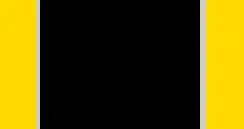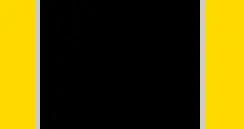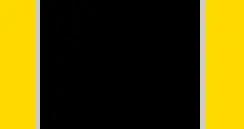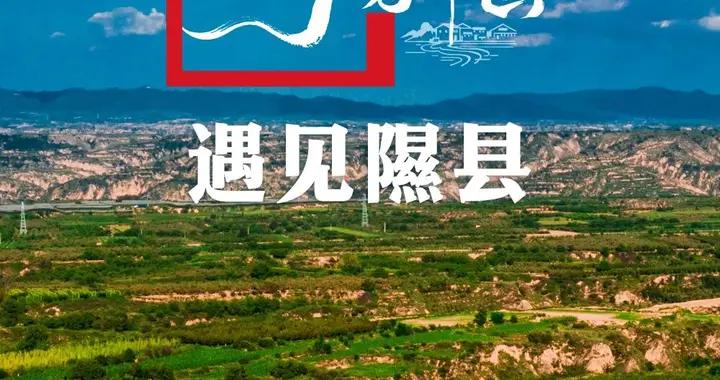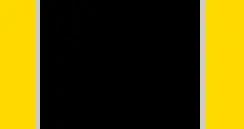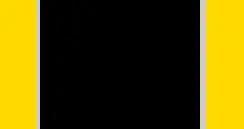1968年地球差點被小行星毀滅?一羣學生用70周,寫了份 “救命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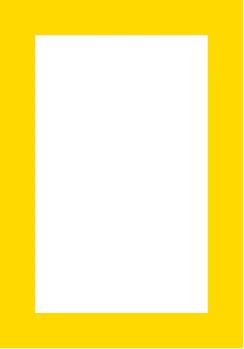
地球是一個奇蹟
歷史|美國

這張壯觀的坦普爾1號彗星(comet Tempel 1)圖像,拍攝於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深度撞擊號” 探測器的撞擊器被其摧毀後的67秒。| 國家地理圖片集

2021年,一項覆蓋全球1萬名16至25歲年輕人的調查顯示,75%的受訪者對未來心懷恐懼,超過半數甚至認爲人類終將走向滅絕。
這樣的悲觀情緒並非空穴來風。如今的大學生成長在一個特殊的時代——人類面臨的風險不僅持續增加,還變得愈發複雜。但並非所有關乎人類生存的風險都在不斷升級,事實上,最致命的風險——足以摧毀世界的彗星或小行星撞擊地球——如今發生的概率已遠低於過去。
這種風險的大幅降低,背後有着諸多原因,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點,是一羣大學生與一位年輕教授主動站了出來,採取了行動。20世紀60年代,當小行星撞擊地球的可能性首次引發美國公衆恐慌時,正是這羣學生起草了一份拯救地球的行動藍圖。
1949年,天文學家沃爾特·巴德(Walter Baade)發現了一顆小行星,後來這顆小行星被命名爲伊卡洛斯(Icarus)。人們很快發現,伊卡洛斯的運行軌道不僅會讓它靠近太陽——這也是它得名“伊卡洛斯”的原因——還會讓它危險地逼近地球。
1965年,曾參與計算伊卡洛斯軌道的天文學家羅伯特·理查森(Robert Richardson)指出,只要這顆小行星的軌道發生一絲微小偏移,到1968年它下次靠近地球時,就可能撞上地球。物理學家斯圖爾特·托馬斯·巴特勒(Stuart Thomas Butler)隨後發出警告:伊卡洛斯“或許能在一瞬間,就把世界上任何一座主要城市夷爲平地”。
20世紀60年代本就是個令人惶惶不安的十年,這樣的警告很容易引發公衆的焦慮。發達國家的生態系統明顯走向崩潰,部分原因是不受管控的污染排放與殺蟲劑濫用。
那是一個處處充斥着生存風險的時代,和我們當下所處的環境頗爲相似。或許正是這種普遍的焦慮,讓很多人認真對待了巴特勒的警告。《紐約時報》的記者沃爾特·沙利文(Walter Sullivan)報道稱,“本報及其他多家報社都接到了大量民衆打來的焦慮電話”。
儘管頗具影響力的天文學家們紛紛站出來安撫公衆,稱1968年小行星撞擊地球的可能性爲零,但他們也無法否認,理論上,隨時可能有另一顆小行星撞上地球。
1967年1月,距離伊卡洛斯預計掠過地球僅剩一年多時間。當時,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工程師、同時也是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的保羅·桑多夫(Paul Sandorff),正準備開設一門名爲“高級空間系統工程”的研究生課程。
他在校園各處的佈告欄上張貼了招生啓事,並承諾,這門課的核心任務,是讓學生們制定出一套防止伊卡洛斯撞擊地球的方案。
不少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對此持懷疑態度。有人回憶,當時校園裏還流傳着玩笑話——“要不造個超大蹦牀把小行星彈走?”——但最終,還是有21名學生報名了這門課。他們後來回憶,第一次上課的時候,大家心裏都“帶着幾分不屑與懷疑”,而當他們見到保羅·桑多夫本人時,這種態度也沒怎麼改變:眼前的教授身材矮小,總是佝僂着背,褲子還往上提得蓋住了肚子。
不過,這種不屑並沒有持續太久。桑多夫給學生們描繪了一個令人心驚的場景:畢竟,天文學家已經確定,伊卡洛斯一定會撞擊地球——時間就在1968年6月19日正午,這顆小行星將墜入大西洋中部,爆炸產生的威力相當於5000億噸TNT炸藥,隨之引發的海嘯會奪走數百萬人的生命。
桑多夫要求學生們必須想出辦法阻止這場災難。而且有明確要求:只能使用當時已有的技術,調動的資源也必須是在70周內,國家和全球範圍內切實能調用的力量。
學生們心裏很清楚,即便伊卡洛斯這次真的不會撞上地球,小行星或彗星撞擊地球的威脅卻是真實存在的——這種威脅讓公衆越來越恐慌,可各國政府卻完全沒有采取應對措施。他們後來在回憶中寫道,沒過多久,大家就抱着“絕不放棄的決心”投入到方案設計中,因爲他們知道,自己肩負的使命有着“最有價值的目標——拯救人類的生命”。
學生們自發分成了多個小組,每個小組負責解決伊卡洛斯逼近地球所帶來的一個具體難題。他們很快發現,“一個小組做出的決定,往往會成爲另一個小組開展工作的基礎規則”,所以,那些複雜的難題,只有通過“小組內部、小組之間的密切協調與合作”才能解決。
這門課,無形中變成了一堂系統管理的速成課。在理解來襲小行星所帶來的挑戰本質上,學生們很快取得了實質性進展。他們意識到,只要能在小行星以較慢速度經過其軌道上離太陽最遠的點時追上它,那麼將它從小行星與地球的相撞軌道上引開,就會相對容易。
這就像推鞦韆的原理:在鞦韆盪到最高點時輕輕推一下,到了最低點,這個推力帶來的影響就會變得很大。
學生們一致認爲,探測是防止小行星撞擊地球的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如果能在一顆有威脅的小行星撞上地球前很多年就發現它,那就可以在它遠離太陽時發射火箭前往。只要給小行星施加一個適度的推力,就能讓它的軌道發生微小偏移——但就是這一點點偏移,足夠讓它避開地球。
不過學生們也明白,用這種方法來改變伊卡洛斯的軌道,已經來不及了。等到航天器能被髮射到伊卡洛斯附近時,這顆小行星早就以每小時超過10萬公里的速度逼近地球了。
當時能想到的另一個辦法,是用氫彈摧毀它。學生們估算,一枚當量爲10億噸TNT的氫彈或許能奏效,但這相當於美國武器庫中最大氫彈威力的50倍——想在短時間內造出這樣一枚氫彈,幾乎是不可能的。
更糟糕的是,即便真的造出了這樣的氫彈,也可能只是把伊卡洛斯炸成碎片,而這些碎片加起來,依然會給全球帶來毀滅性打擊。所以,唯一的選擇只能是在地球附近改變伊卡洛斯的軌道,也就是讓它偏移,但這同樣需要巨大的力量。
到學期結束時,學生們終於制定出了一套完整方案:用六枚土星五號(Saturn V)登月火箭,每枚火箭攜帶一枚當量爲1億噸TNT的氫彈。在雷達的引導下,第一枚氫彈會在距離小行星約100英尺的地方引爆——這個距離能最大限度降低小行星被炸成碎片的風險。
氫彈爆炸產生的輻射會讓小行星表面汽化,汽化產生的力量會推動小行星,讓它偏離原本的軌道。如果小行星依然朝着地球飛來,後續的氫彈就會繼續施加推力,要是小行星已經被炸成碎片,這些氫彈就會摧毀那些朝着地球飛去的碎片。
當然,這個方案並非萬無一失:每一枚火箭都有可能出現故障,而且小行星也可能會分解成細小的碎片,根本無法徹底摧毀。但學生們計算得出,“伊卡洛斯計劃”(Project Icarus)能讓地球避開這場末日災難的概率約爲71%,而且完成這個計劃所需的資金,還不到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
同年5月,學生們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克雷斯吉禮堂展示了他們的完整方案。正如他們後來所說,當時大家都“充滿熱情”,而且方案公佈後,全美“從東海岸到西海岸,至少有30家報紙”都刊登了報道,介紹他們的這個項目。
可到了1968年,當伊卡洛斯安全掠過地球后,公衆對小行星撞擊風險的關注度就大幅下降了。各國政府不僅沒有爲小行星探測項目提供資金支持,更別說投入資源研發未來能攔截、偏移來襲小行星的系統了。
不過,情況後來還是發生了改變。1979年,科學家們提出,一顆大型小行星很可能是導致恐龍滅絕的“元兇”——正是它引發了全球物種大滅絕;1989年,一顆此前從未被觀測到的小行星,危險地逼近了地球;1994年,一顆彗星的碎片與木星相撞,在木星表面留下了明顯痕跡,這一幕讓公衆極爲震驚。
此後,美國國會將“小行星撞擊預防”——也就是後來所說的“行星防禦”——納入了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核心職責。
在桑多夫的學生們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三十年後,他們當初提出的小行星探測項目建議,終於被採納。如今,科學家們已經繪製出了約100萬顆小行星的運行軌道,並且確認這些小行星都不會對地球構成威脅。
此外,通過讓機器人航天器與小行星相撞,科學家們還證實了麻省理工學院計劃中提出的“首選偏移方法”是可行的——也就是在小行星遠離地球時,改變它的運行軌道。因此,和1967年桑多夫的學生們走進他的課堂時相比,現在小行星撞擊地球的風險已經大大降低了。
桑多夫當初設計的這種授課方式,在今天看來,依然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如今的課堂上,當學生們瞭解到核擴散、氣候變化,或是人工智能持續發展所帶來的威脅時,常常會感到無能爲力,甚至陷入絕望。而桑多夫的教學方法,能讓學生們意識到,自己也能爲解決這些現實問題出一份力。
誰又能說得準呢?或許,這羣學生真的能在未來拯救世界。
撰文:Dagomar Degroot
編譯:Arvin
校對:錢思琦
版式設計:錢思琦

點點,謝謝關注。
伸出小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