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引擎淪爲歐洲病夫,朔爾茨的紅綠燈聯盟,如何摧毀第四帝國
閱讀此文前,誠邀您點擊一下“關注”按鈕,方便以後持續爲您推送此類文章,同時也便於您進行討論與分享,您的支持是我們堅持創作的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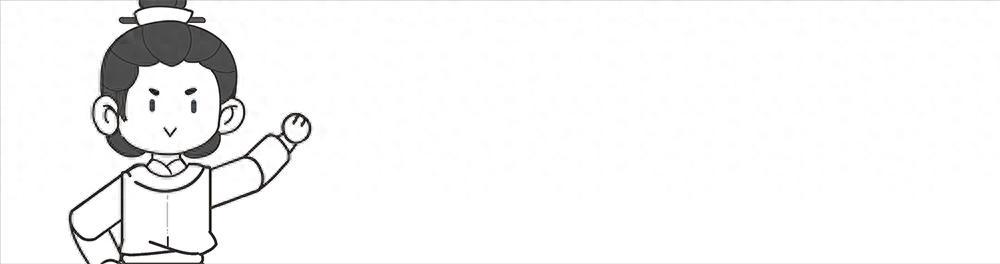
聲明:本文內容均引用權威資料結合個人觀點進行撰寫,文未已標註文獻來源及截圖,請知悉。
“德國又一次成爲歐洲病夫了嗎?”
2023年,英國《經濟學人》上發表了一篇評論德國經濟的文章,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討論。
儘管德國政府一再反駁“歐洲病夫”的說法,但事實卻是德國這個昔日的歐洲引擎在接下來的一年多時間裏,經濟持續負增長,最終甚至導致德國政府垮臺。
德國,這個昔日默克爾治下的歐盟引擎,爲何在默克爾卸任之後如此迅速淪落?

第四帝國
德國,曾經有過一段輝煌的歷史,德意志第三帝國的“奮鬥”讓整個歐洲震顫匍匐。
不過,這場戰爭最後的結果,以反法西斯同盟的勝利而告終,曾經不可一世的德意志第三帝國也被徹底拆解。
雖然由於冷戰的興起,德國作爲兩大陣營在歐洲的交界處,被雙方視作了展示自身優越性的櫥窗。
這使得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分別向西德和東德投注了大量資源,將德國經濟發展水平拉到了陣營前列。
但作爲代價,兩德的政治都深受到陣營領袖的影響甚至控制,而德國二戰發起國、戰敗國的身份,更給這種控制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在主權都稱不上完整的情況下,不管經濟再怎麼發展,自然都談不上什麼國家的輝煌。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德國總算等到了兩大陣營的力量天平失衡,藉着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機會,重新實現了兩德統一。
不過,兩德合併雖然是德國人的夙願,但由於兩德之間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存在巨大的差距,不可避免地給德國造成了融合期陣痛。
此時正是歐美資本主義陣營瓜分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多年發展成果的關鍵時刻,同時,美國還釋放了不少軍事技術進入民用領域,帶動了以互聯網經濟爲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
英、法爲首的一衆歐洲國家,因這千載難逢的機遇取得了飛速發展,唯有德國經濟停滯不前甚至是不進反退,德國也因此首次被《經濟學人》戲稱爲“歐洲病夫”。

但就在英國對德國開嘲諷之後不久,2005年,精通妥協藝術的默克爾上臺,給德國帶來了轉機。
此前,德國政府一直在發福利收買民衆和減稅挽救企業之間來回搖擺。
選擇發福利,就會導致政府負擔過重,不得不增加稅收來維持運轉,進而導致企業因高稅收而缺乏國際競爭力;而選擇減稅,就不得不砍福利,這又會引發民衆的強烈不滿。
但默克爾深知不能一條道走到黑的道理,在企業和工會之間協調,大家各退一步,團結起來搞發展。
在默克爾的協調下,德國的經濟發展總算是迴歸了正軌,2006年,德國創下了21世紀以來的最高經濟增長,經濟發展速度重回歐洲前列。

甚至於,在隨後的2008年經濟危機當中,德國憑藉自身強大的工業實力,成爲了歐洲第一個擺脫危機影響的國家。
趁着其他歐洲國家陷在歐債危機裏出不來的機會,默克爾利用德國在歐洲央行的影響力,逼着其他歐洲國家改革。
依靠着一套類似於債務陷阱的手段,德國一邊打垮了其他歐洲國家的工業,一邊還混到了個“歐洲拯救者”的好名聲。
同時,默克爾還藉着“拯救歐洲”的威望,在歐盟各國之間居中調停,充分發揮妥協藝術,爲各國找到利益均衡點。
這極大地促進了歐洲團結,進而帶動了歐洲的發展,絕大多數的歐洲國家都認爲,在默克爾時期,歐盟在德國的帶領下正在變得越來越好。

德國也憑藉自己的經濟實力,和默克爾的調停之功,成爲了歐盟的領袖,並借歐盟的聲勢,進一步提高了德國的國際地位,甚至達到了德國曆史上都不曾有過的高度。
在默克爾任內,德國當真是風光無限,以尚未完全擺脫雅爾塔體系限制的身份,成爲了世界多極化的重要一環,默克爾治下的德國,也因此被戲稱爲“第四帝國”。

羣龍無首
2021年,默克爾按照她2018年的承諾,在她的第4個總理任期結束之後未再追求連任,德國從此迎來了“後默克爾時代”。
當時,任誰都沒想到,在失去了默克爾這個強勢領袖之後,德國政壇竟會陷入混亂,而這種混亂,居然迅速地摧毀了默克爾苦心打造的“第四帝國”。
原本,由於默克爾治下的德國形勢一片大好,她所在的聯盟黨備受德國民衆歡迎,聯盟黨新黨首拉舍特只要不犯錯,就能夠平穩接班。
結果任誰也不會想到,拉舍特居然能如此拉垮,在大選期間去視察洪水災區卻不合時宜地發出大笑,引發民衆的強烈反感,聯盟黨的支持率從此開始跌跌不休。

最終大選結果出爐,聯盟黨的支持率僅爲24.1%。
反倒是長期與聯盟黨聯合執政的小夥伴社民黨,在候選人朔爾茨給自己打出“默克爾繼承人”的旗號後,支持率達到25.7%,成爲議會第一大黨。
然而,在德國的政治體制下,大選只是政府換屆的第一步,後面的組閣纔是真正的重頭戲。
由於在之前與聯盟黨的聯合中,社民黨長期被壓制,對聯盟黨早有不滿,且在本次選舉中兩黨差距極小,社民黨沒法確保兩黨聯合後牢牢把握內閣主導權。
也因爲這次選舉的結果實在平均,即使社民黨與聯盟黨聯合,也沒法達到組閣門檻,註定要拉第三方加入。
朔爾茨乾脆選擇拋開聯盟黨,拉上綠黨和自民黨組了個交通燈聯盟。

在這個聯盟中,綠黨和自民黨彼此政見差距極大,反倒都與社民黨的主張有一定接近之處,且兩黨都是小黨,支持率遠不及社民黨,看起來應該比較容易拿捏。
結果沒想到,即便看起來條件如此有利,等到真正開始聯合執政之後,朔爾茨依舊是被拿捏的那一個。
綠黨和自民黨仗着社民黨不敢散夥,在政見上決不妥協,政府整日磋商,也討論不出一個共同的政見。
更加糟糕的是,在實際的政策實施中,各黨派爭相“搶跑”,仗着自己在有關部門的之位,不管政府意見,先把自己的政見推行下去再說。
其中綠黨尤爲典型,2022年,朔爾茨帶隊訪華,準備與中國建立全方位戰略伙伴關係,結果綠黨在國內卻搞出了《對華戰略》草案,對中國所謂人權問題指手畫腳。

德國政府政出多頭,互相扯後腿,結果就是什麼事都幹不成。
更加糟糕的是,德國的外部環境,也在這時發生了嚴峻的變化。
朔爾茨政府剛上臺,就遇上了中美矛盾激化和俄烏開打,原本德國能在中美俄三家之間左右逢源,現在不行了,美國正按着德國要他制裁俄羅斯,與中國脫鉤。
如果德國政府能擰成一股繩,或許還能夠周旋一二。
偏偏此時的德國政府正忙着內部拉扯,尤其政府內部還有綠黨這個也嚷着和中俄脫鉤的“內鬼”,面對美國的施壓根本毫無抵抗之力。
原本德國的經濟強勢,靠的是製造業相對發達,而俄羅斯的廉價能源和中國的龐大市場,加上東歐的廉價勞動力,正是德國製造業發達的三大基礎。

現在德國因爲政治原因,自己動手去拆掉了兩根支柱,經濟衰退也就成了情理之中。
2023年,德國經濟增長率爲-0.3%,是歐盟主要經濟體中唯一一個呈現負增長的國家,《經濟學人》也是在這個時候又開始嘲諷德國是“歐洲病夫”。
德國政府對此一再反駁,稱德國雖然因爲地緣政治問題面臨一些結構性挑戰,但這絕不是病態,只要調整過來,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然而事實勝於雄辯,第二年,德國經濟繼續負增長,企業破產數量創下數年來的新高,就連那些享譽世界的大企業,也開始在德國本部大規模裁員。
在經濟上的表現如此糟糕,在政治上,朔爾茨政府更是成爲了世界笑柄。

俄烏衝突爆發不符合歐洲利益,德國和法國一開始是想要勸阻的,結果一點也勸不住;
衝突爆發之後,德國給烏克蘭出的錢僅次於歐美,結果卻因爲在援烏過程中不肯率先升級援烏武器規格,還要被烏克蘭指責爲軟弱,連個好名聲都沒撈到;
在俄烏衝突和中美戰略競爭中,半主動半被迫地上了美國的船,結果連討好美國都做不到,在美國大選中站隊民主黨沒少得罪特朗普,結果特朗普上臺,德國頓時傻了眼。
內憂外患之下,德國政府支持率連連下跌,政府內三黨的爭執也不斷加劇,最終在2024年11月徹底宣佈散夥。
隨後,朔爾茨政府沒能通過議會信任投票,德國政府正式宣告垮臺。

昔日強盛的“第四帝國”,短短3年就淪落到這個地步,確實令人唏噓。
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德國的衰落,似乎又是德國所謂“民主政體”導致的碎片化政治下的必然。
在德國的政治模式下,幾乎沒有哪個政黨有可能獨立執政,必然要組建執政聯盟,但聯合執政就意味着政府內部分歧。
即使是默克爾這樣難得的強勢人才,在她的最後一個任期中,也是舉步維艱,差點沒能順利組閣,當總理個人能力不足時,德國政治體制的問題更是會無限凸顯。
而政治的失能,必然給極度依賴社會環境和政府支持的經濟發展造成反噬,今天在德國發生的一切,即使換一個政府,也未必不會上演。

參考資料
罕見連續兩年負增長,“火車頭”變“病夫”的德國何去何從 新浪財經

德國統一後經濟發展的困境與成功歷程分析 王湧 西部學刊

德國大選罕見結果:一個沒全贏,一個沒輸透 澎湃新聞

地球局|德國“紅綠燈聯盟”散夥,朔爾茨能挺過信任投票嗎 齊魯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