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精粹】回憶未必可靠 | 李傳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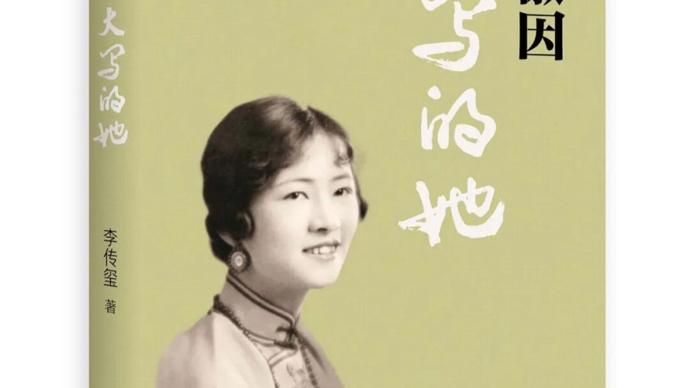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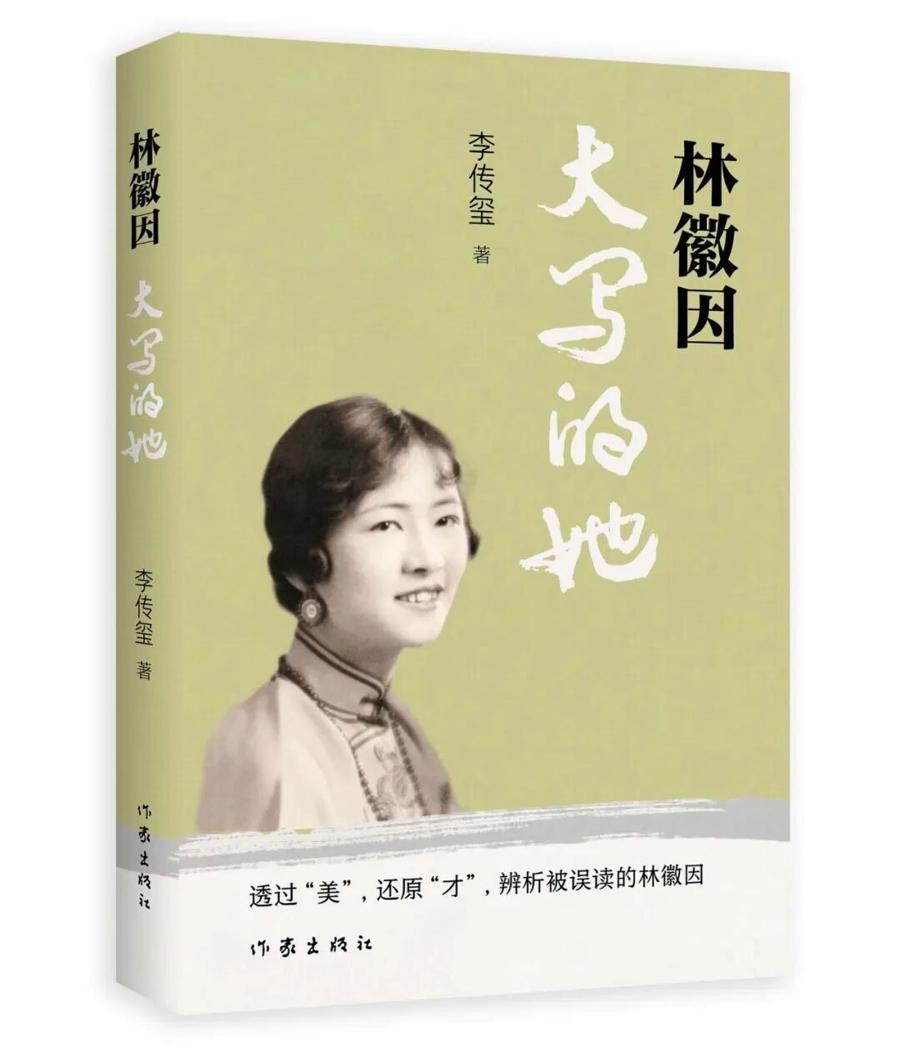
本文爲作家出版社即將出版的《林徽因:大寫的她》代序
標題是我這兩年研究梁思成、林徽因所產生的感慨。
何以會有這個感慨?
讀有關人民英雄紀念碑史料時,看到20世紀80年代初出版的一本小冊子,談到參與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人員時,竟然把林徽因寫成了“凌徽因”。這本書還是當年參與者回憶性質的書,那時出版無論編輯還是作者都是很嚴謹的,出這個錯,當我一看到,真是大大一愣。爲什麼會有此錯呢?只能是一個原因:林徽因先生逝世較早,距此時已經有快三十年了,這三十年又是中國知識分子遭受衝擊最頻繁的艱難歲月,林先生在人們的記憶中已經淡化。
“科學的春天”到來後,林徽因逐漸以中國現代文化人最閃亮的形象迴歸人們的視野。對她的回憶和紀念文章開始大量出現。又正是這種時間流逝以及由此帶來的記憶的淡化,使得此類文章同樣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此類失誤。
再舉一個例子。
1950年6月2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國徽審查小組召開會議,議題就是選定國徽圖案。梁思成先生因爲那幾天太勞累病倒了,林徽因先生本來就病着。由於朱暢中先生兼任清華大學營建系祕書,同時參與了國徽圖案設計,梁先生就請他“做代表去會上聽取意見”,朱暢中先生跟隨張奚若先生前往參加。在紀念梁思成先生誕辰八十五週年之時,他寫了篇回憶文章,重點談了國徽設計以及參加此次重要會議所見到的討論國徽圖案的情景:“會議室中間白牆上掛着兩個國徽圖案:左爲清華方案,右爲美院方案”,“參加會議的委員們,或坐或站,一邊觀看國徽圖案,一邊議論紛紛。他們各有所好,各有看法,各持己見,莫衷一是。當時我站在旁邊,心中忐忑不安地等待着這捉摸不定的評選結果”,“大家正在紛紛議論之中,周恩來總理親臨會場。周總理走到兩個圖案前細細觀看一下後,就問大家意見如何。田漢先生首先對總理說,他認爲中央美院的方案好,還說了些優點。有的委員也贊同田漢的意見”。(《梁思成先生誕辰八十五週年紀念文集》,此書編輯委員會編,清華大學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126頁)
別小看這麼幾句話,這可是重大歷史事件,事關參會人員對國徽圖案的態度與選擇意見。看此次會議記錄影印件,列席者就朱暢中一人。他的這回憶應該很重要,故而後來說到此次會議,朱先生的回憶都是關鍵參考資料,基本上都予以引用。
我初次看到這段,不僅準備引用,心中還產生聯想:討論國歌時,馬敘倫先生提議用《義勇軍進行曲》做國歌,他的話首先得到梁先生的贊同,並提出詞曲都保留。當時田漢先生就在場,他自己還謙虛說詞有時間侷限性。此番討論國徽圖案,沒想到首先是田漢先生否定由梁思成、林徽因掛帥的清華圖案,看來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討論國旗國歌國徽方案時,大家都是一本公心,沒有存情面之私的。
但當我再對照影印記錄時,發現不是這麼回事。缺席人名字寫着(我按原記錄照抄):剪(作者按:應作“翦”)伯贊、錢三強、張瀾、馬寅初、梁思成、葉劍英、郭沫若、田漢、李立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國歌檔案》下卷,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417頁)梁思成先生沒去,田漢先生也沒去。沒去的田漢何來此番不同意見?
還看一個例子。費慰梅作爲梁思成林徽因最好的朋友,20世紀90年代出版了《梁思成與林徽因——一對探索中國建築史的伴侶》一書,以紀念他們之間的深厚友誼。在說到梁思成與林徽因因抗戰全面爆發離開北平時間時,她這樣寫道:“1937年9月5日,梁家離開北京去天津,走上逃亡路上的第一站。”(曲瑩璞、關超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年9月第1版,第124頁)可根據新版《林徽因全集》“英文書信卷”(1935—1940)林徽因致費慰梅1937年9月19日信記載:“親愛的人們:發生了太多的事情,不知從何說起。我們總還算是平安,一週前抵達天津,正乘船離開,準備前往青島轉濟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7月第1版,第272頁)此信一直由費慰梅保留着,明確地說明了梁林一家離開北平的時間是9月12日,和從天津繼續逃亡的時間是9月19日。此信寫得很短,一反她給費慰梅信總是長篇大論,正是由於乘船離開時間緊張。看來費慰梅在寫作時是僅憑記憶來寫的。她並沒有去看看當時的信件。
由此我想說,即使是事件親歷者,時間一久,回憶未必可靠,在寫作時必須注意與原始資料或檔案相印證。
這本書裏很多文章是對林徽因先生的“辨析”,在在證明回憶未必可靠。這兩年印行的一些關於林徽因先生早期的史料(這些史料由於年代久遠,也存在着一些時間編排上的錯誤),爲這些辨析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這些辨析不是對回憶者和紀念者所作出的貢獻的貶低,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都是爲了給關心梁、林的讀者“留下真實的註腳”(於葵語)。這些辨析更不是對林徽因先生包括梁思成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地位的否定,相反,會讓他們的形象更清晰更鮮明更真實,讓林徽因那大寫的“人”更“風神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