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鹽商視角下的微觀中國近代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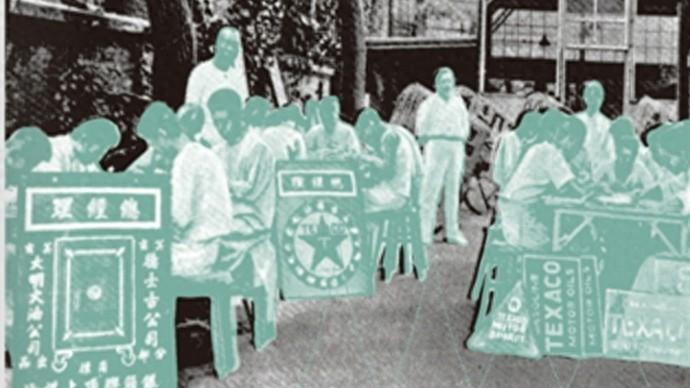

《亦官亦商:明清時期天津的鹽商與社會》是一部講述天津鹽商羣體與城市發展的社會史著作,通過鹽商的視角,揭示了明清國家、社會與經濟的複雜互動。全書以鹽商爲核心,立體剖析其在經濟發展、家族治理、社會文化網絡構建中“亦官亦商”的矛盾性:一方面努力經營社會網絡,向朝廷捐輸,與士人交遊,通過聯姻等方式與其他家族互通有無;另一方面服務桑梓,用心於地方慈善事業,積極參與地方自治、教育改革等事業。書中,作者考索了天津大鹽商家族的命運沉浮,系統梳理其從興起、鼎盛到衰落,從積極參與政治到退步抽身的數百年曆史,還原清代鹽稅徵收、引岸制度運作、民商糾紛等細節,呈現了一段別樣的天津明清社會生活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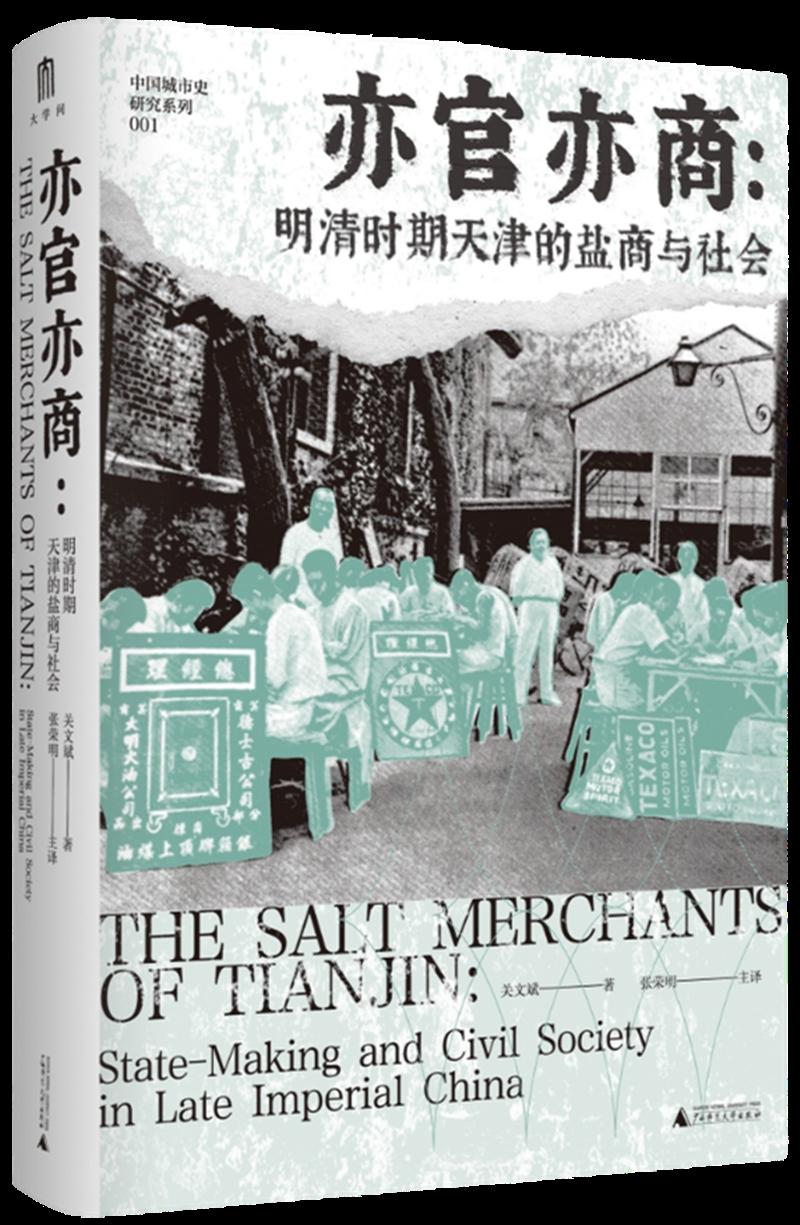
《亦官亦商:明清時期天津的鹽商與社會》,關文斌 著,張榮明 主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內文選讀:
查氏家族:盛極一時的水西莊
張氏和安氏敗落之後,查氏繼起,成爲天津鹽商社會文化網絡的領袖。查氏在天津的兩個主要支派可追溯至江西臨川。1590年,以查聿和查秀爲首的一支遷徙到今天的北京郊區宛平。這個家族經歷了明清之際的改朝換代,以“義不可辱身於賊”,一門“七烈女”自殺,被文人稱頌。查秀的孫子查如鑑曾任揚州府江都典史,他去世時,其子查天行(1667—1747)才3歲。自此以後,這個家庭儘管陷入了貧困之地,卻擁有相當多的社會關係。查天行由其任儀徵知縣的姐夫撫養成人,在他父親諸多朋友的幫助下,事業迅速發展。他定居天津,先供職於工部關。這是一個雖地位低但有油水的世襲職位,缺份可以隨意買賣。
但是,在查天行看來,長蘆似乎更有誘惑力。於是,他成爲張霖的合作者之一,牽涉入案,亦被查參,只有125081兩銀的資產,卻向內務府稱貸21萬兩。他被投入了監獄,並被判死罪。但是,查天行不像張霖,他與親家金大中清償了所欠的117500兩銀。察察爲明的康熙甚至批評辦理此案的官僚,因爲貸款時議定分八年本利清還,而查、張案發時並未滿八年,戶部本利一併全追,康熙認爲這樣做“於理不合”,命令戶部解釋。大學士馬齊爲戶部辯護,“恩出皇上,部中何敢議免”。這復奏讓康熙闡釋他對法律的看法:“雖朕之恩,亦據理斷之而已。若無理,豈可斷乎?”查獲得了赦免,1709年被釋放。
可是,此次教訓似乎並沒有抑制查天行的野心。三年後,他再次身陷囹圄,罪名更爲嚴重:爲他的兒子在科舉考試中串通作弊。據趙申喬的奏摺:“本生(查爲仁)卷面大興與冊內開宛平不符,榜發十日本生尚未赴順天府聲明籍貫,有無情弊,難以懸定,據實題明,乞敕部查究。”《清實錄·康熙朝》1711年10月31日。後來查明查天行僱舉人邵坡冒名爲他的長子查爲仁(1694?—1749),參加1711年順天府鄉試。這一舞弊行爲的暴露,原因倒不是槍手失敗,而恰恰相反,是槍手考了第一名。在市井傳言中,作爲解元的查爲仁目不識丁,因而輿論譁然。朝廷準備再次調查,父子二人倉皇逃往南方,躲在浙江紹興一個親戚家裏。1713年,兩人被捕受審並被判處死刑。但是,蔣良騏驚異地發現,查氏父子最終竟得到赦免,不像其他的鹽商,也不像1711年江南和福建的相同科場案犯——他們都被立即處死。
關於查氏父子是如何化險爲夷的,現存史料只有零星的載錄。查爲仁在刑部西曹的難友張照爲查爲仁的詩集《花影庵集》(花影庵是查給自己的監牢取的齋號)所作的序言裏提供了一條線索。張照的同年進士趙熊詔告訴他,他的父親趙申喬作爲1711年順天府鄉試的主考官,自感對查氏的處境負有責任。步軍統領陶和氣(託合齊)也介入了此案,目的是報復趙申喬建議參革銅商金、王兩姓。陶(託)氏四處散佈言論,說這科榜首與取中者多是富人子,是因爲他們有行賄勾當,藉以打擊趙申喬。趙跟託是否有其他過節、趙對查的赦免是否真的起了作用還不清楚,但是,銀子能使他們化險爲夷。據說,查天行的妻子用2萬兩銀子贖罪,查氏父子分別於1718年和1720年被釋放。
無論如何,查爲仁成爲一位傳奇人物,被載入史冊和鄉土教材。文人雅士們視他爲天才,爲他能在惡劣的環境下,從目不識丁成長爲詩人中的翹楚,爲天津文學增光而感到自豪。這些傳奇式的說法,自然真假混雜。假如查爲仁1713年入獄時目不識丁的話,那麼他在創作《花影庵集》(集中最早的詩作於1714年)之前,僅有一年的時間學習詩作的格律與技巧。這是一件有可能卻令人難以置信的事。當然,這亦不排除槍手代筆的可能。
不論是否目不識丁,查天行父子繼承張氏和安氏餘緒,成爲天津鹽商文化網絡的領袖。他們在城西三里購買了一百多畝地,建成“水西莊”,這裏便成了查氏網絡的大本營。水西莊位於運河南岸,莊裏綠樹成蔭,假山奇石遍佈,歌臺舞榭等大小建築掩映其間,房中羅列書籍、畫卷、古玩。陳元龍與查昇是總角之交,二人曾同在南書房共事,陳還在各部及內閣擔任過要職,如文淵閣大學士兼管禮部,致仕後旅次水西莊作《坐攬翠軒與天行述舊》一文,回憶兩人總角之時,又作《水西莊記》,稱“斯園乃塵世之丹邱”。陳的侄子、當時任戶部侍郎的陳世倌稱查天行爲叔叔,在查氏七十壽辰的時候,敬獻祝壽詞一篇。另一位高官、湖南人陳鵬年,經查慎行和查浦的引介,亦作客水西莊,爲查爲仁的詩集題寫序言。
地方官也是查氏網絡的成員。首任天津直隸州(設於1725年)知州宋晶,1725年到任的長蘆鹽運使張璨,都常到水西莊酬唱。1726年任長蘆鹽運使的陳時夏撰文讚頌查天行的繼室,言及他與查之間近二十年的友誼。英廉在擔任天津河防同知時,曾頻繁與查氏交往,與這裏的詩人唱和。水利專家陳儀(第一章已述及)不無驕傲地宣稱,沒有人比他更瞭解查天行了。陳宏謀任職天津河道期間,亦與查氏論交,爲查日乾側室王氏撰寫八十壽序。查爲義(爲仁弟)故後,陳宏謀應查禮(爲仁三弟)的請求,作《集堂府君小傳》爲紀念,“以俟後世之採風者”。
來到水西莊的更多是文人騷客。查氏海寧支系(南查)的查慎行(曾任職南書房,前已述及)視查爲仁如同親子,教他作詩。慎行的弟弟查浦在1700年成進士之後的兩年時間中旅食水西莊,與查天行以兄弟相稱,視水西莊爲“隱逸之所”。厲鶚、杭世駿、萬光泰、汪沆和符曾等來到水西莊時無不感到賓至如歸。由查爲仁命名的水西莊詩集《沽上題襟集》刻印後,一紙風行。查爲仁箋註《絕妙好詞》,厲鶚將查的箋註與他的箋註相比較,認爲查氏堪稱第一。這樣,查作爲詩人和學者日益聲名遠揚。
然而,當乾隆皇帝駕幸水西莊時,所有這些達官貴人和文人雅士都黯然失色。乾隆皇帝於1748年首次到水西莊,他認爲這是一個愜意之所。隨後他幾次來到天津,也都下榻水西莊。只是這一特殊的榮耀,也使查氏付出一定的代價。既然皇帝如此厚愛此園,查氏便深感責任重大,於是將莊園的一部分修繕一新,專門奉獻給皇帝。1771年,乾隆皇帝將此園御筆命名爲“芥園”,從此這裏成爲皇帝親臨的聖地,其他人無論擁有多大權勢、多少財富,也不能僭越了。
然而,這樣的代價並不算大,查氏因此實現了他們追求的夢想——獲得社會的尊重。儘管地方誌編纂者對查氏是“流寓”抑或“鄉賢”持有爭議,但查氏宣稱他們自參加科舉考試起就入籍天津。他們的姓名甚至進入了本地方言,“闊查”成爲富有的同義詞。查爲仁的二弟查爲義曾任安徽太平府通判,致仕返回天津後成爲一名鹽商、詩人和業餘畫家。查爲仁三弟查禮,1748年在戶部任職,外放後領兵參與大小金川之役,最終於1782年任湖南巡撫(未到任)。查禮之子查淳,官至湖北布政使。確實,自查天行之後的查氏五代人,代代至少有一人中舉人或成爲進士。他們與海寧陳氏(本姓高)源遠流長的關係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查爲仁次子查善和是陳邦彥的女婿。陳邦彥進士出身,是一位造詣頗深的書法家,曾入值南書房,官至禮部侍郎。但是北查到了善和這一代,家道已經開始衰落。科場無論得意還是失意,候補或捐官,都耗資鉅萬。加上族人“花時載酒,累月流連”,不事生產,所託非人,連年涉訟,“遺貲幾蕩然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