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年輕女作家決定去荒野尋馬



“生活是曠野,不是軌道”這句話風靡網絡,折射出當代生活中的精神困境:在功績社會和內卷競爭包圍下,究竟該從何處突圍?在理性與科技雙重控制的當代生活中,該如何實現自己的自由?然而,大多數人跟風喊出這句口號時,並不理解曠野究竟意味着什麼。人們嚮往曠野,僅僅是因爲對遠方生活的美好想象可以作爲從當下生活逃離的出口,或是想當然地認爲,只要做出另一種選擇,就能過上幸福生活。
當拿起依蔓的《荒野尋馬》這本書時,我原以爲這也會是一種對“遠方生活”的詩性再現:美景,美食,還有對陌生事物的驚歎。但完全不是。依蔓的寫作極度坦誠,她對遠方的幻想、荒野的濾鏡心存警惕。可以說,依蔓的旅程是一趟驗證之旅。她帶着一個明確的動機:在動盪的荒野生活中,能找到某種確定性的東西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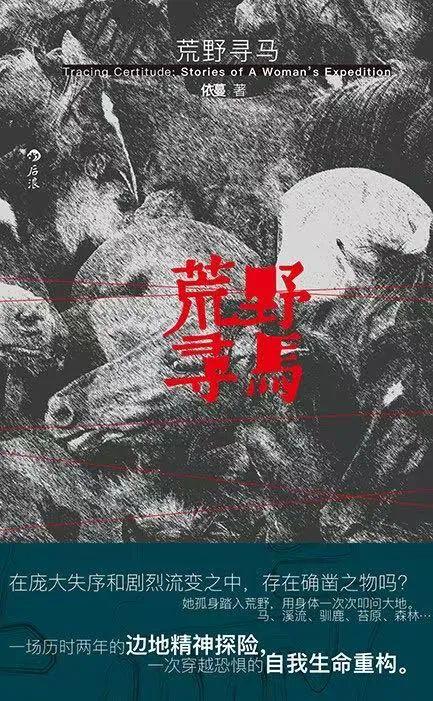
爲什麼要去荒野尋找確定性?她說:“在看似自由,也意味着極度動盪的生活之中——如果真的存在所謂確鑿不移的東西,真正可以仰仗相信,真正抓得牢靠得住的東西——在這樣的地方也可以存在的確鑿的東西,纔是真實的,經得起沖刷的吧。”她要尋找的是某種普遍恆定的確定性,不受外在環境的制約和束縛。大都市的生活經歷讓她對現代城市所代表的精確和控制產生懷疑。龐大失序的事物讓她感嘆:“現代都市系統極致繁盛但無時無刻不處於極致控制之下的確鑿看似堅固,實則無比脆弱,它是虛空、唬人的假物。”
城市代表着人類文明和現代性的發展,強調規則、秩序、效率、可控性,同樣也強調確定性。有了確定性的前提,人類理性才能在此基礎上不斷髮展。啓蒙運動之後,人的價值和理性主義被無限放大,人的主體性在此基礎上不斷膨脹。人們警惕混沌之物和未被命名之物,因爲這意味着自我受到威脅,不受控制;推崇確定的有邏輯的事物,因爲這是可被理性解釋的,可被人們理解和選擇的。但這勢必帶來一個問題:人類中心主義。
人類中心主義認爲人是萬物的靈長,人可以從自身理性出發去丈量世界,人的理性優於其他生物,人的行動具有某種社會意義,並天然預設了權力等級(人類顯然位於最高級)。但是來到荒野,人類中心主義的視角不管用了。在這裏,人類自以爲的現代工具抵抗不了零下30度的嚴寒,GPS不能一勞永逸定位到馬的位置,沼澤充滿未知。
依蔓說:“秩序是現代的神,草原是這一切的反面。”她主動從人類理性世界中逃逸。書名“荒野尋馬”耐人尋味。荒野,未被人類理性規訓過的空間。馬,漂亮動物,不是人造的東西。想要尋找從人出發的確鑿,在荒野中是不存在的。荒野中的確鑿,就是馬身上所具備的和人類理性相反的自然性、動物性、偶然性。在馬看來,動盪纔是恆常不變。在書的最後,她寫:“真正確鑿的就是我所懼憚的動盪本身。”

《荒野尋馬》作者依蔓
其實,哲學專業出身的依蔓怎會不明白?但從理性上知道是一回事,從身體上知道又是另一回事。人不能說出未經經驗的事物。依蔓在書中非常明確地說道:“只能自己用身體去真正地經驗它,而不是想象它,在那之前,我絕不可能真正說出它。”
依蔓自述從小患有焦慮症。原生家庭帶給她強烈的不安全感,她需要證明自己比別人強,讓拋棄家庭的父親後悔。“如果真的成爲一個不夠優秀的女兒,那麼父親的離開就是正確的。”她驚恐時母親給她塗清涼油,意圖讓她清醒。“可是母親,我就是過於警惕清醒。”依蔓的自述讓人心疼。這樣的成長背景下,依蔓是優績主義道路上的成功者。她需要確定性,這樣才能控制自己的人生,這樣才能不斷完善自己,朝着目標前進。比如人生病了,只要知道病名,按照治療手冊去治病就行。比如工作通勤,依蔓會精確算好時間坐高鐵和地鐵:“一切行動必須嚴絲合縫纔不會出錯。只要遵照這個流程,一整天就可以安全、高效、有序地鋪展開去。”甚至,她在旅程中會時不時責怪自己不懂牧民的生存經驗。
可是,有些病是現代醫學手段無法確診的。高鐵地鐵的精確控制也讓我們的時間碎片化,生活日漸疏離疲憊。沒在草原生活過的她必然也是不知道那些經驗的。
責怪自己的依蔓可能認爲,只要改正錯誤,精進自己,就可以繼續沿着優績主義這條路走下去。也許最初,想在荒野中找到普遍性的確鑿,也是一種“做題家”思維,想找到最優的解法。在當代社會成爲系統控制型社會後,一個問題是:人,也能掌控一切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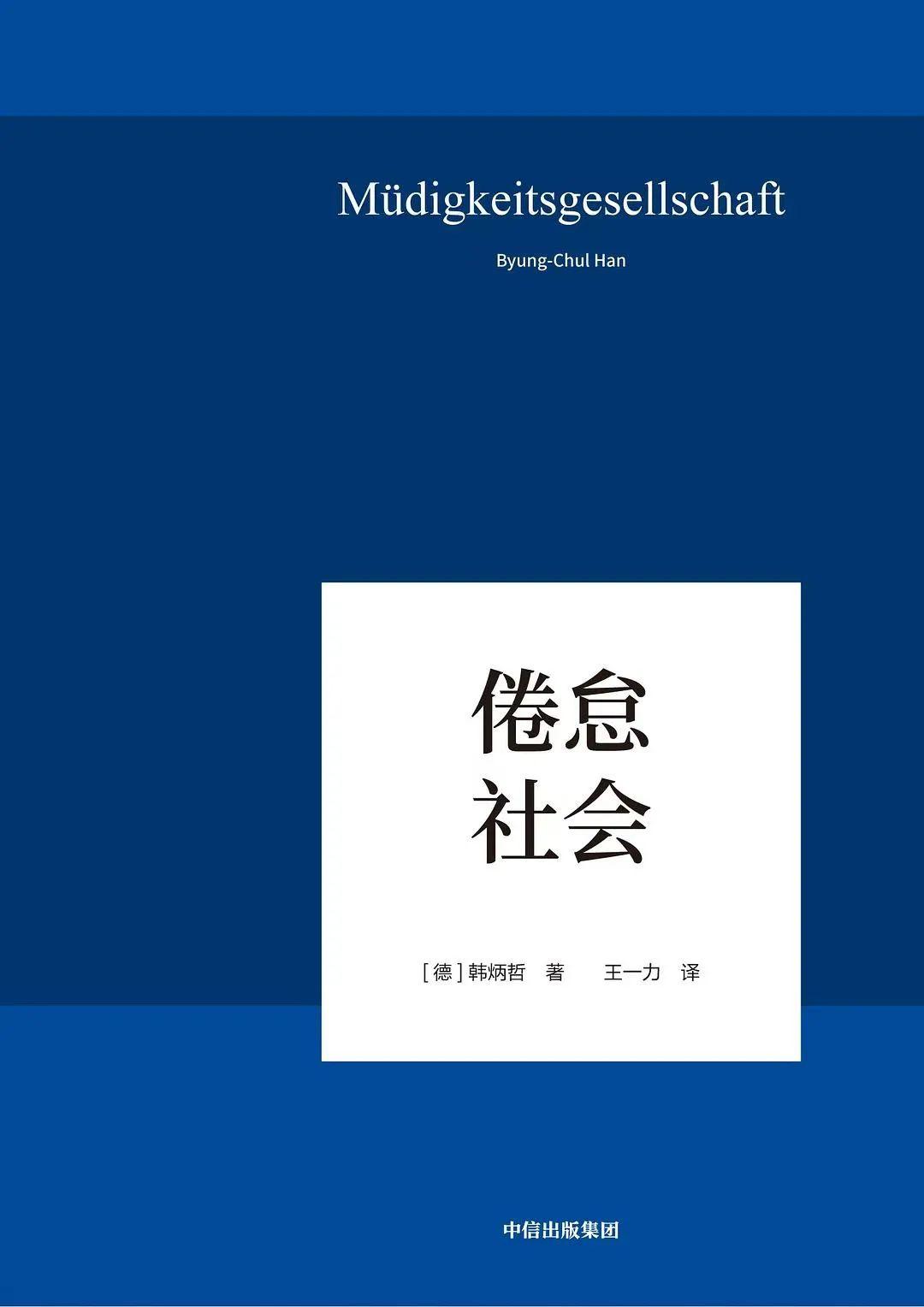
韓炳哲在《倦怠社會》中認爲:“現代功績社會,也是一種積極社會。”積極社會中的自我認爲,發展自我,成就自我,是在實現自己的價值。每個人都有義務和責任讓自己變得更好。這種“好”被簡化爲“強”。人們慕強恐弱,系統性暴力滋生,並把他者工具化,而可被工具測量和利用的世界必然導致無限內卷和崩塌。人們以爲自己在自由地進步,其實這種自由是一種虛假的自由。韓炳哲說:“一旦積極性加劇爲過度活躍,它將轉變爲一種過度消極,在這種狀態下,人類將毫無防禦地回應一切衝動和刺激。由此導致了新的束縛,而非自由。如果一個人信奉越積極便越自由,那麼這只是他的幻想和錯覺。”
而要打破這種功績主體的桎梏,就要破除對確定性的迷信。因爲積極社會的前提就是可控性和確定性。依蔓在《荒野尋馬》中告訴我們:世界本沒有確定唯一的東西。只有承認這一點,原來堅固守舊的價值觀才能逐漸瓦解,才能讓流動取代固定,多元取代唯一,開放取代封閉,遊蕩取代穩定,被遮蔽的層次才能浮出水面,廣闊的空間才能向我們敞開,我們也才能創造新的連接的可能。
讀《荒野尋馬》,跟隨依蔓一路從恩和到埃平森林、薩布賽多,彷彿也能看到那些山,那些馬,能夠一路感受她的焦慮、痛苦和頓悟。荒野的旅程不僅讓她回顧和剖白自己的過去,重新生成對世界的理解,更讓她身體力行,跨越自身理性與生命經驗的侷限,激盪起對當代生活的反思。
在書的最後一節,依蔓那段穿越荒原的經歷堪稱神奇,讓人感動得幾乎落淚。她在克服恐懼,在沒有確定性前提下的未知經驗下探索,達成與自然萬物相連接的境界。所謂以萬物爲芻狗,就是荒野在平等地看待一切,也要求我們平等看待所有。“我變得透明,變成了別的什麼,變成我不熟悉的東西。更赤裸的東西。沒有姓名的什麼東西……與荒原邊界模糊,我們消融彼此。我自願被荒原吞沒。失去我。消弭我。”一路走來,逃脫功績社會的轄制,打消對確定性的迷信,破除內心的魔障,她與自己和解,以新的眼光去看荒原,那便是原初,廣博,寬闊,生動,元氣十足。山就是山,河流就是河流,沒被人類的語言污染,未被形而上學所命名。語言的音、形只能固定我們對於世界的理解,它是一道牆,是邊界本身。“言說只捕捉異常有限的確鑿。我們遠在詞語出現之前就識得山。”她在消除感知的邊界,以有限抵達無限,由此洞開一個新的生命空間。這個空間彷彿天地初開,一切都是新的,於是,便有了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