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香格里拉——西方社會持久出現西藏熱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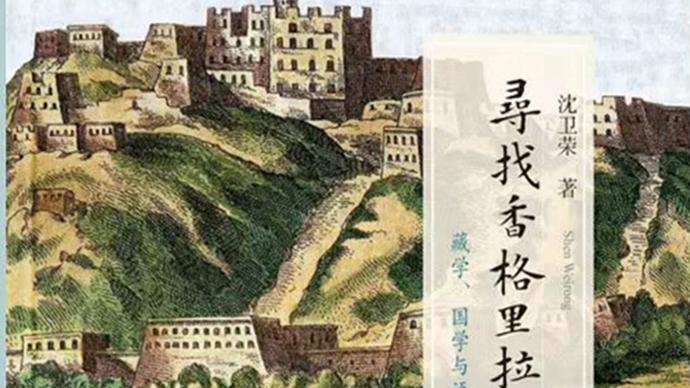

《尋找香格里拉——藏學、國學與語文學論集(一)》系作者對國學、“西藏問題”和學術方法等熱點問題的思考,發表以來深受學界和文化界好評。作者的“大國學”理念別具一格,對“語文學”的闡釋和倡導發人深思。長達16年的海外遊學經歷,結合紮實的專業知識背景,使作者對國際視野中的“西藏問題”有非常透徹和獨到的見解。通過對一個西方後現代的烏托邦神話——“虛擬的西藏”(即香格里拉)的解構,作者爲世人理解西藏、西藏文化和所謂“西藏問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本書初版於中國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本次再版已隔15年。原書剛問世時,曾引發了討論西藏問題的熱潮,許多讀者並被其中廣闊的全球學術眼界、豐富而生動的學術史闡述,以及旁徵博引、信手拈來的文風所深深打動。作者對於西方世界想象中的西藏、東方主義的批判,解答了許多當代人——不論東方還是西方——對於西藏傳統、藏族生活、藏傳信仰的疑惑,糾正了許多常識性的誤解。面對那些先入爲主的書寫和概念,倡導以“文本學”“語文學”的方法,打破慣性,還原西藏的本來面目。而今天,不論是我們從中華文明史的視野對於西藏史地的重新審視,還是對於語文學、古典學的深入瞭解和運用,本書都仍然具有重要的啓發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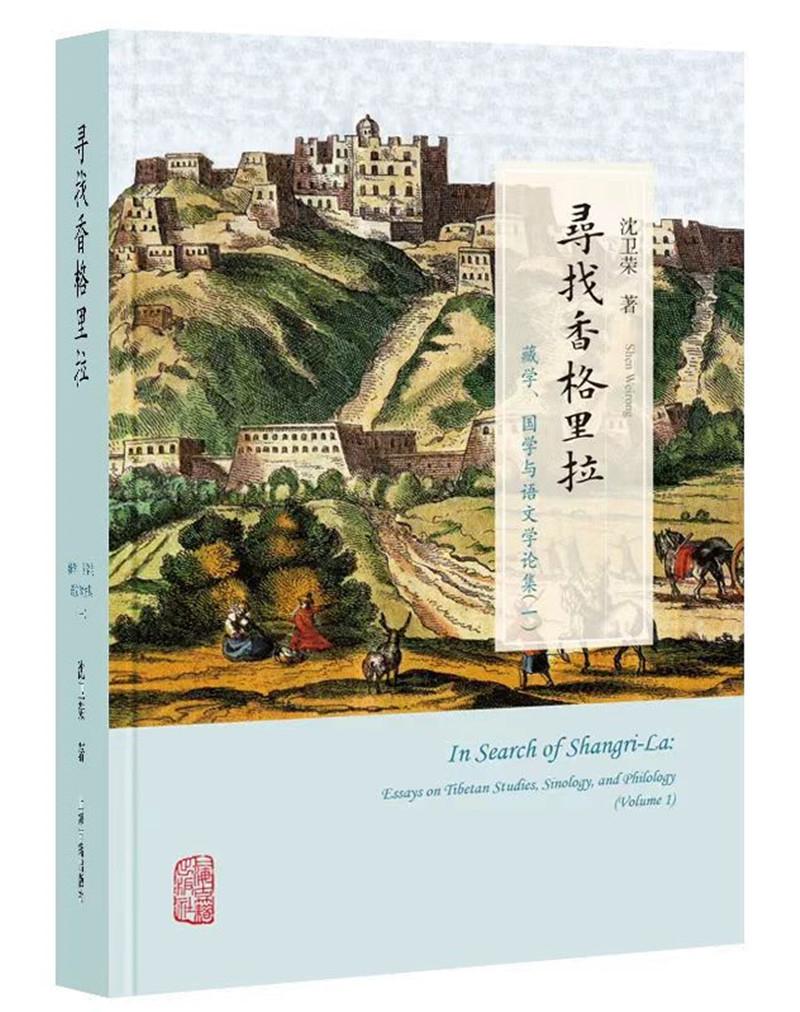
《尋找香格里拉——藏學、國學與語文學論集(一)》,沈衛榮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出版
>>內文選讀:
尋找香格里拉——妖魔化與神話化西藏的背後
1933年,一位名叫James Hilton的人發表了一部題爲《消失的地平線》的小說,一路暢銷至今,被後人稱爲遁世主義小說之母。這部小說講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一個世外桃源的故事。
1931年5月,外國人正慌亂地從印度某城巴斯庫撤離,一架英國使館派出的飛機從該城飛往中亞的白沙瓦,結果被劫持到了一個叫香格里拉的地方。當時飛機上有四個人,一個是英國的公使,名叫Robert Conway,還有他的一名副手、一名女傳教士和一位正遭通緝的美國金融騙子。當這四個人坐的飛機中途被劫持、迫降在雪山叢中時,他們發現這個名爲香格里拉的地方竟是一個難得的世外桃源。
雪山叢中,有一個“藍月谷”,一座巨大的宮殿聳立於中央,最上面住着香格里拉的主宰“高喇嘛”(High Lama),香格里拉會集世界各路精英,管家是一位文雅、世故的漢人,還有一位漂亮的滿族小姐。香格里拉有中央供暖、俄亥俄的阿克倫浴缸、大圖書館、三角鋼琴、羽管鍵琴,還有從山下肥沃的谷地運來的食物。
香格里拉的圖書館裏面充滿了西方文學的經典,收藏的藝術品裏面有宋代的瓷器,演奏的音樂中竟有肖邦未曾來得及於世間公佈的傑作,可以說世界文明的精華鹹集於此。香格里拉的居民人人享受着現代、富足的生活,所有的西藏人卻住在宮殿的腳下,他們都是伺候那些喇嘛及其他居民的僕人。除了西藏人以外,這裏的人都長生不老。他們的“高喇嘛”已經活了250多歲。那位看上去很年輕的滿族小姐實際上亦已經接近百歲了。
1919年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美年輕人成了“迷惘的一代”,特別是英國的很多精英知識分子和年輕人,他們滿懷着對人類社會幸福美好的嚮往,積極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但是戰爭粉碎了他們對世界的希望和夢想,使他們無法再走上傳統的生活道路,於是開始尋找心中的香格里拉。
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是一場世界性的經濟衰退,可能比近幾年我們所面對的金融危機還要嚴重,是近代以來規模最大、後果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可想而知,在戰爭把自己的理想粉碎的時候,又遭受嚴重的經濟危機,當時的人們是怎樣一種精神狀態。接下來各個國家出現瘋狂的民族主義,最典型的就是德國的納粹開始猖獗。第二次世界大戰山雨欲來,百姓恐懼戰爭陰霾,飽受摧殘的心靈需要在香格里拉這個寧靜美好的伊甸園中得到撫慰。
可以看出,香格里拉是西方世界想要尋找的一個美好的伊甸園。
《消失的地平線》反映的是時代的思想,帶有很深的帝國主義的烙印,在純潔美好的烏托邦理想下掩蓋了許多隱藏的暴行。香格里拉只是西方白人的伊甸園,而不是東方人的桃花源,更不是世界人民的幸福樂園。香格里拉居民的地理分佈充分體現了這種平和的神權統治下徹頭徹尾的種族等級體系,住得越高,地位就越高,像“高喇嘛”住在最頂層,是一個平和的神權政治的最高統治者。外族的喇嘛們生活在屹立於宏偉巍峨的雪山上的喇嘛寺,而種植糧食的大量土著居民生活在下面的山谷中,這些就是西藏人,他們除了會喫飯、微笑以及伺候他人外,就不會再做什麼了。在香格里拉,他們是沒有地位的,只是僕人。
西方人公開地聲稱:“我們認爲西藏人由於他們所生活的海拔高度等原因,不如外界的民族那麼敏銳,他們是非常迷人的民族,而且我們已經接納了很多藏族人,但是我們懷疑他們其中能否有人活過百年。漢族人相對而言好一些,但是他們中很多人也只活了一般意義上的高壽而已。我們最好的選擇毫無疑問是歐洲的拉丁人和北歐人,美國人也同樣受歡迎。”從這些可以看出種族的劃分是非常明顯的,有很典型的帝國主義的氣息。
總而言之,香格里拉是一座西方文明的博物館,是18世紀歐洲人對於東方和東方傳統文化的幻想。香格里拉是一個充滿了帝國主義腐臭的地方,它是西方人創造的一個精神家園,而不是西藏人的精神家園。在《消失的地平線》中經常提到:東方人難以進行精神交流,西方人的精神苦悶和終極追求是東方人不能理解的。所以,這個保存了世界文化成果的香格里拉是西方文明的博物館,東方文化只是裝點。
1937年,著名導演Frank Capra將《消失的地平線》拍成電影,這部同名電影使得香格里拉的故事在西方深入人心。香格里拉本身的來歷可能是作者靈機一動創造出來的,也可能是與藏傳佛教裏的香巴拉有些關係。但是現在沒有證據可以說作者知道藏傳佛教裏有香巴拉這個傳統。總之,在地圖裏,香格里拉是一個找不到的地方,沒有辦法確定。從前美國的導彈發射基地就被稱爲香格里拉。美國總統休假的地方,現在叫戴維營,以前也叫香格里拉。20世紀70年代開始,香格里拉大酒店遍佈東亞,但在西方是沒有的。這是帝國主義的流風餘緒,目的在於重溫帝國主義的舊夢。
非常遺憾的是,幾年前中國雲南的中甸宣佈這個地方就是香格里拉。還有很多人出書證明這個地方就是香格里拉。其實,香格里拉就是一個莫須有的地方。如果把對香格里拉的這種認同作爲發展民族經濟的商業行爲,無可厚非。但是從政治上講,這是很不正確的。把雲南中甸裝扮、濃縮成西藏文化的一個縮影,我認爲是一個不恰當的做法,這是在賤賣自己的傳統文化。這是內部的東方主義,Internal Orientalism,是取悅於西方,按照西方的設想製造一個東方的形象。這種傾向在近代和當代,包括電影、書畫、文學作品裏,都出現過。
將香格里拉等同於西藏是西方出現的一種非常典型的傾向,香格里拉變成了後現代西方人的精神家園。這幾年,西藏包括藏族文化在西方非常的喫香流行,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西藏被西方人當成了香格里拉,被整個西方世界當成了他們所期待的一個精神家園。這也是西方社會如此持久的出現西藏熱的原因。實際上,大部分西方人對現實的西藏並不瞭解,也不關心。他們只是關心他們心靈中的西藏,或者是他們虛擬的西藏,而這個西藏,就是香格里拉的一個變種和發展。
西方人對西藏的熱愛是西方“東方主義”的一個經典例證。西方人視野中的西藏與現實、物質的西藏沒有什麼關係,它是一個精神化了的虛擬空間,擁有西方文明中已經失去了的、令人渴望的一切美好的東西。它是一個充滿智慧、慈悲的地方,沒有暴力,沒有爾虞我詐;藏族是一個綠色、和平的民族,人不分貴賤、男女,一律平等,沒有剝削,沒有壓迫。這樣的一個西藏過去沒有在歷史上存在過,在很近的將來也不可能出現。說穿了,西藏是西方人心中一個不可或缺的“他者”,是他們觀照自己的鏡子,是他們用來確定自我認同的座標,是經歷了工業化之後的西方人的精神超市,寄託了他們所有的夢想和懷舊之情。在這裏他們的精神可以縱橫馳騁,得到無窮的享受和滿足。與其說他們熱愛西藏,不如說他們熱愛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