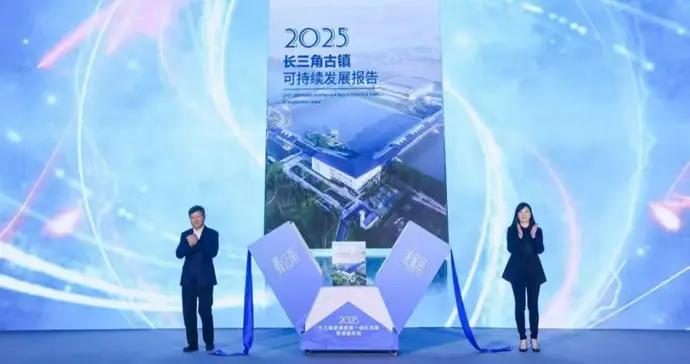活下去,需要的不只是勇氣



人類對長壽的追逐像一臺永動機,從未停歇。不過你是否想過,“活得長”與“活得好”不一定結伴而行,當長壽伴隨着身體朽壞、尊嚴喪失,閣下又該如何應對?說到底,如何有尊嚴地走向生命終點,纔是我們要直面的命題。王一方《醫生不曾告訴你的生命哲學課》,從醫學人文視角剖析長壽與尊嚴的矛盾;吉安·波拉西奧的《生命的最後一公里》,以冷靜筆觸探討生命終點的醫療選擇與自然法則;歐文·亞隆夫婦的《生命的禮物:關於愛、死亡及存在的意義》,則以親身經歷展現臨終時光的溫度與存在的意義。三本書從不同維度打開思考的窗口,指引我們直面生死,探尋向死而生的可能。
人生苦短
古人用“千古艱難惟一死”來形容人類面對死亡的極度恐懼。的確,螻蟻尚且惜命,何況具有主體意識的人呢?一部人類發展史,也是一場人類不斷與時間拉鋸、爲自己續命的超長馬拉松。
史前時代,人類的平均壽命僅20歲上下,今天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放到遠古社會,已接近人生終點了。進入農業文明,平均壽命逐漸拉高,達到35歲,刨去奇高的嬰幼兒夭折率,一個成年人大概率能活到四五十歲。60歲是道坎,孔子談人生,講到六旬之年打住,恐怕是因爲再往後他也沒把握,故存而不論。70歲是又一道坎,人生七十古來稀,非常稀罕。

圖源:視覺中國
古代人的平均壽命爲什麼很難提上去?原因很多。生產力水平低下,多數人長期喫不飽肚子,營養不良,加上科技落後、醫療匱乏,是折壽的普遍因素。要是再遇上天災人禍,老百姓就更難覓活路了。
翻開《古詩十九首》,多有對生命易逝的悲嘆:“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人生如寄,多憂何爲”……對亂世中人來說,“命不久矣”是懸於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於是一再發出“人生苦短”的浩嘆。
直到18世紀工業革命爆發,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衛生的興起,人類平均壽命從古代的35歲上升至1950年的46歲,足足提高了11歲。時至今日,全球平均預期壽命增加至73.3歲,並且還在往上走。投入上億美元研發長壽科技的俄羅斯富豪謝爾蓋·揚甚至聲稱,未來人類有望活到200歲,“永生”也並非遙不可及。
壽則多辱
但事情恐怕沒謝爾蓋·揚所聲稱的那麼簡單。要知道,活得長不等於過得好,長壽和幸福並不必然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把長壽這面翻過來,迎接你的或許是幸福的反義詞。
這道理其實古人都講透了。莊子就認爲“壽則多辱”,意思是與年齒漸長相伴隨的是軀體的朽壞、疾病的困擾及尊嚴的喪失。這樣的“活着”,有何質量可言?18世紀英國作家斯威夫特在《格列佛遊記》中,記敘自己去過一座小島拜訪神奇人種斯特魯格布魯德,他們可以活到1000歲,然而活到90歲,斯特魯格布魯德已陷入耳目失聰、腿腳不便、反應遲鈍的境地,往後900多年的漫長餘生,只能痛苦地苟活着。
你或許覺得這只是小說家言,但現實裏,壽則多辱的情況經常發生。《醫生不曾告訴你的生命哲學課》作者王一方就見過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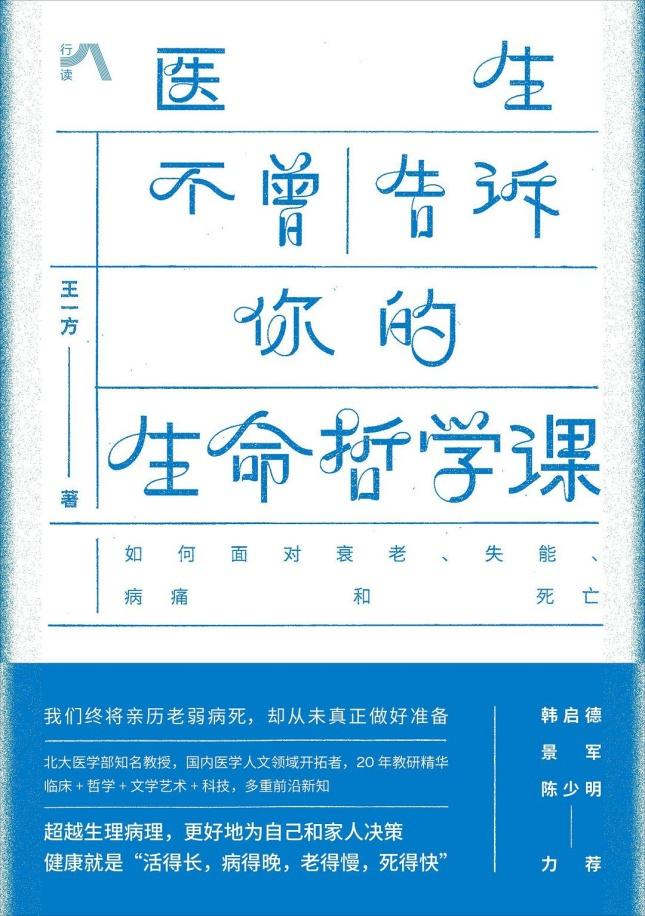
《醫生不曾告訴你的生命哲學課》,王一方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王一方是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教授,有過長期的臨牀經驗,後轉向醫學人文,致力於研究生死哲學、醫學思想史、醫學哲學和敘事醫學。轉向的驅動力,就和他在臨牀實踐中見多了老人受“辱”的景象有關。
屈辱首先源於身體機能的衰退。王一方指出,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表現,很多老人因此患上肌少症。“肌肉量太少會破壞平衡和支撐,導致失能,還可能造成大腦灰質的澱粉樣變,導致大腦退化,也就是失智。”一個行動不便、腦筋糊塗的人,會產生強烈的挫敗感。
拐點往往出現在開車上。不少老人就是在發現失去自由駕駛的能力後一蹶不振的。隨着年紀增長,失能失智的程度會日益加深,老人將越來越多地失去對事物的掌控能力,最終不可逆地滑向精神崩塌。
人工智能或許能彌補這一缺失。“比如,高齡老人能在AI技術幫助下開車上路,這有助於減少他的挫敗感。”王一方說。但人工智能無法破解人類喪失主體性後任人擺佈的困境,而這纔是人之所以受“辱”的關鍵。
王一方觀察到,現在的情形是,很多老人思想開明,早已看淡生死,只求臨終時走得不痛苦、有尊嚴。偏偏是子女放不下所謂的孝道,違背老人明確表示過不進重症監護室、不插管、不鼻飼的意願,堅持要醫生盡全力搶救。老人無力抗拒,只能默默承受,其結果反而是徒增屈辱和痛苦。
如何面對死亡,有尊嚴、有質量地走完生命最後階段,不只是老人關心的事情。無論是爲了親人還是爲了自己,我們都有必要深入思考。
與病共存
首先我們需要明白,人不是生來就長壽的。事實上,前現代社會成年人的平均壽命,可能纔是符合生物學規律的。
《生命的最後一公里》開篇,波拉西奧就用冷靜的筆觸揭示了生物爲何要死的真相:“每一個生物體在儘可能多地產出後代、讓後代存活下來並照顧到後代進入育齡期之後,該生物體在生物演化意義上的作用就已經窮盡。從此以後,該生物體只會是自身後代在獲取食物上的競爭者,對於基因擴散沒有可見的益處。因此,爲有利於自身的物種,該生物體應該儘快終結個體的存在。”照此邏輯,假設一個人20多歲生兒育女,待後代長到相仿年紀,他也就到該離開的時候了,否則隨着勞動能力喪失,他將從價值的創造者變成純粹的消耗者,與後代爭搶生存資源。這違背了自然法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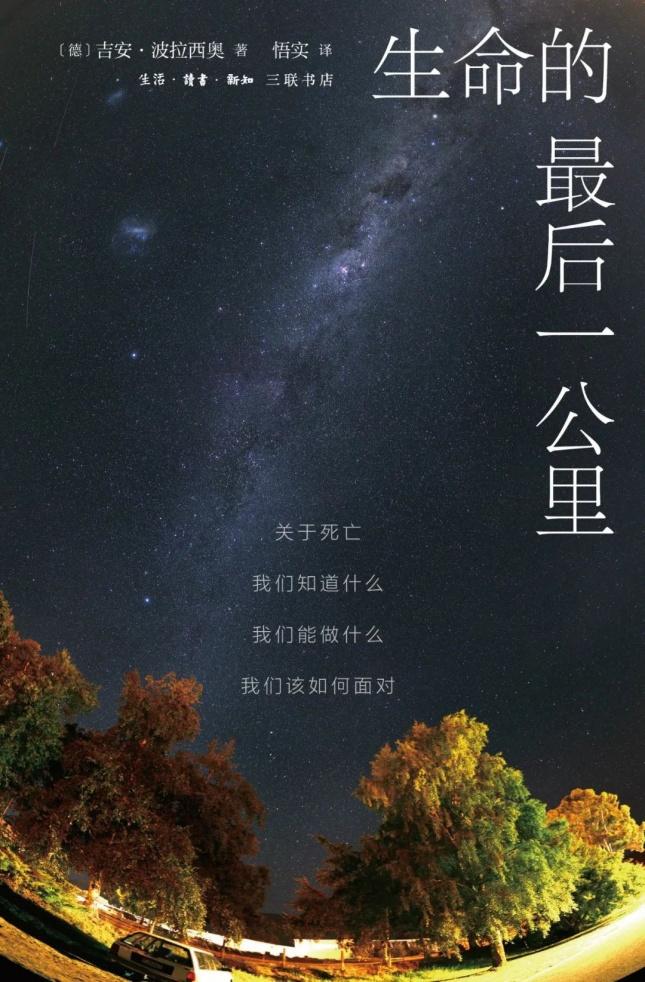
《生命的最後一公里》,[德]吉安·波拉西奧 著,悟 實 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出版
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從兩個維度破解了這一難題。一方面,生產力大幅提高,能供養更多的剩餘人口了;另一方面,通過加強營養、改善衛生、發展醫療等手段將壽命活生生拉長,上演了“逆天改命”的戲碼。
但這是有代價的。現代人患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病等疾病的幾率遠遠高於古人,原因之一就是活得太長。古人較少得這些病,是因爲還沒到得病的年紀就已經往生。因此,現代人要享有更長的生命長度,就必須學會與衰老和疾病共存。問題在於如何共存、共存到什麼程度?
這並不好回答。如果答案是竭盡所能,共存到不能共存爲止,就意味着我們應當忍受屈辱和痛苦,醫院的重症監護室(ICU)將是最好歸宿。然而,只要親眼見過ICU裏那些常年臥牀、全靠營養液和藥物維繫的病人,你會捫心自問:這種毫無生趣和尊嚴可言的“共存”,果真值得嚮往嗎?難道就沒有更好的選項了?
在《醫生不曾告訴你的生命哲學課》中,王一方舉了兩個案例:一位癌症晚期的高齡老人,被家人送進ICU,戴着呼吸機,身上插滿管子,強撐了31天。在這31天裏,子女只能在規定時間探視,都沒來得及和老人見上最後一面;另一位患癌老人,在安寧病房住了11天,期間召集子女,回顧自己的一生,並對每個子女提出忠告,最後在親人的陪伴下平靜離世。
從延緩生命的角度說,無疑是前一位老人勝出。但換作你或你的家人,會傾向於哪一種離去方式,覺得哪一種更人性化、更能慰藉死者和家屬的心魂呢?我想,每個人心中自有答案。
當然,像關乎生死這樣的終極問題沒有非此即彼的答案。我們不是要確立排他性標準,而是嘗試在“延續生命”和“有尊嚴地活”之間取得某種平衡,爲人生走向終點探尋更多可能性。這就將我們的目光引向了安寧療護。
拒絕“拔河”
安寧療護,亦作臨終關懷,始於英國醫護工作者西西里·桑德斯夫人。長期護理絕症患者的經驗使桑德斯夫人深刻認識到,病人的痛苦不僅來自生理疾病,還源自精神、心理以及社交等各個層面。因此單純地緩解肉體上的痛苦遠遠不夠,他們需要全面、細緻的關懷。1967年,桑德斯夫人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家安寧療護機構——聖克里斯托弗安寧醫院,致力於改善臨終者的生存狀況,盡一切努力減輕他們的痛苦。

圖源:視覺中國
波拉西奧指出,正是這一點將安寧醫院和常規醫院區分開來。20世紀中葉以來,由於在手術和重症監護方面取得了驚人成就,醫學界瀰漫着一種“無所不能的感覺”,彷彿沒什麼病是治不好的,就算治不了,也要千方百計地延長患者的生命。結果,醫生把死亡當作敵人,出現死亡便是對敵鬥爭失敗。在這種思維主導下,“治癒”和“續命”成爲醫生的至高準則。
王一方用“和死神拔河”形容這種心態:患者如同一根繩子,醫生與死神各執一端,拼命拉拽。“真正遭罪的是這根繩子,可誰都沒有爲它考慮過。”換言之,患者在治療過程中遭受的痛苦,很少被認真對待。
安寧療護要做的,是在確認患者進入臨終階段後,將“繩子”的一頭放鬆,減輕其痛苦。波拉西奧據此主張,把非必要的、可能引起過多痛苦和副作用的措施減少到最低限度,從而走好“生命的最後一公里”。因此,安寧醫院不會像常規醫院那樣,使用鼻飼、輸氧、化療等手段爲臨終者續命。
進一步思索,這或許是對醫學倫理的迴歸。醫學歸根結底是爲人服務的,而不是拿臨終者和死神拉鋸。桑德斯夫人有一句廣爲流傳的名言:“你重要,因爲你是你;你重要,即使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如何體現這種重要性呢?那就是要以臨終者爲中心,充分尊重其主體性。
向死而生
據王一方估算,我國每年的死亡人口約1000萬,其中癌症患者約佔三分之一、340萬人左右,而能夠進入安寧療護通道的僅30萬人。供給不足是一方面。當前,中國設有安寧療護科的醫療衛生機構約4000家,主要集中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且專業醫護人員缺口較大。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觀念問題。據陸傑華、戚政燁的《直面臨終時刻:醫院安寧療護中的妥協與調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一書披露,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死亡仍然是犯忌諱的話題,哪怕醫護人員也往往對死亡諱莫如深,以至於在安寧療護病牀總供給量不足的情況下,出現了病牀利用率偏低的尷尬景象。
應該承認,竭力挽救親人的生命乃是人之常情,不獨中國人如此,波拉西奧筆下的德國人同樣如此。簡單判定哪一方錯了,試圖去“糾偏”,是輕率的,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探尋更多的可能性。這方面,亞隆夫婦的經驗值得參考。
美國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師歐文·亞隆和妻子、歷史學家瑪麗蓮·亞隆都是享有世界級聲望的學者。2019年,瑪麗蓮患多發性脊髓癌,化療時一度中風。醒來後,她請亞隆放下手頭工作,合寫一本書。接下來六個月,兩人各自書寫,並彼此交換閱讀。直到有一天,瑪麗蓮決定停止化療,選擇安寧療護,在亞隆和四名子女的環繞下告別人世。妻子去世後,亞隆繼續寫書,直至完成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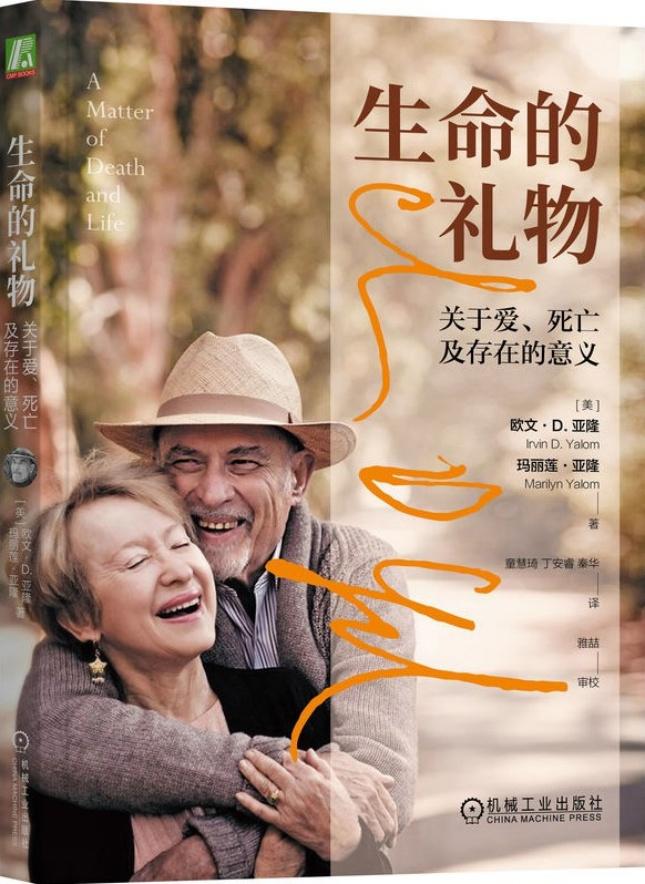
《生命的禮物:關於愛、死亡及存在的意義》,[美]歐文·亞隆、瑪麗蓮·亞隆 著,童慧琦 等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23年出版
於是有了這本感人至深的《生命的禮物:關於愛、死亡及存在的意義》。在書中,亞隆夫婦以誠摯的文筆回顧了兩人相濡以沫、相愛相知的風雨人生路,又以深邃的思考探討了生命、死亡、愛與存在的意義,特別是當至愛至親之人走向終點時,我們應以何種姿態相伴左右。書中最令我觸動的是這句話:“我們寫作是爲了理解我們的存在,即便它把我們掃進了身體衰退和死亡的最黑暗區域。這本書的首要意義是幫助我們度過生命的盡頭。”在我看來,這本書的寫作既是對瑪麗蓮的一種安寧療護,也是亞隆自我療愈的過程。
亞隆夫婦面對死亡的態度啓示我們,死亡是人類的宿命,與其在恐懼和迴避中被死亡的陰影所籠罩,不如主動面對,言說甚至與之對話。所謂“向死而生”,就是將生命的最後階段也視爲一個有意義的、可參與的過程,通過反思、告別與愛的表達,賦予人生終點以獨特的重量,最終實現對生命整體的理解和接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