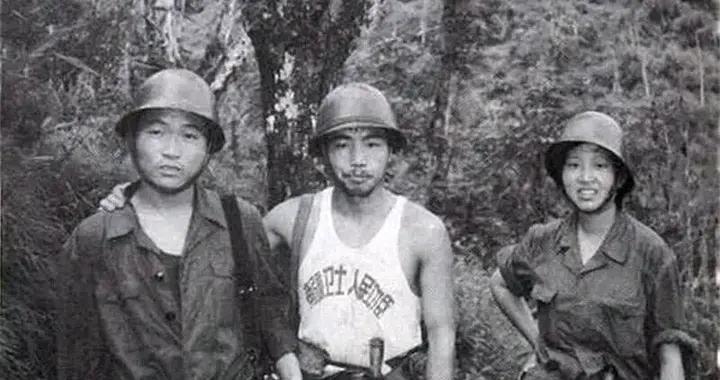鄭天挺:他是西南聯大的“大管家”,也是中國史學界的當家人物
談到民國,你能想到什麼呢?
是十里洋場的燈紅酒綠?
是軍閥混戰,強敵環伺?
還是林徽因的詩?
徐悲鴻的畫?
穿旗袍的畫報女郎?
亦或是五四青年的一聲聲吶喊?
革命先烈的慷慨激昂?
民國,就像狄更斯在《雙城記》中開頭說的: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
那個時代炮火連天,民不聊生,但也人才輩出,百家爭鳴。
而西南聯大,則是那個時代重要的人才搖籃。
那時的西南聯大,飛機在頭上轟炸,學生在洞裏上課,但就是這樣艱苦的環境,孕育出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171位兩院院士以及100多位人文大師。
學生出俊傑,教授更是不遑多讓。
擔任常委的有清華校長梅貽琦、北大校長蔣夢麟、南開校長張伯苓,中文系有朱自清、聞一多;
外文系則有葉公超、柳無忌,哲學心理系有馮友蘭、金嶽霖,算學系有華羅庚,社會學系有費孝通……
而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則是當時西南聯大的歷史系教授、著名歷史學家鄭天挺。
鄭天挺是西南聯大的“大管家”,他在抗戰期間擔任西南聯大的總務長,爲學校的運營保駕護航。
他也是史學界的“當家”人物,爲北京大學、南開大學歷史學科建設恪盡職守。
他畢生致力於史學研究,被譽爲20世紀後期少有的宗師級史學家。
接下來,我們就一起走進鄭天挺的傳奇人生。

出身名門,幼年失怙
鄭天挺,1899年8月9日出生,祖籍福建長樂。
長樂設縣始於唐武德六年(623年),取長安久樂之義。
長樂歷史文化底蘊深厚,自古就有“海濱鄒魯、文獻名邦”的美譽。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良好的文化氛圍,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
古有“朱子理學第一傳人”黃榦,明代數學家、珠算學家柯尚遷,清代著名中醫理論家、醫學教育家陳修園;
近現代則有作家鄭振鐸、詩人冰心等人物。
而鄭天挺也是長樂這片土地培育出的一顆璀璨明星。
鄭天挺出生於書香世家,他的曾祖父鄭廷珪,是清代道光年間進士,之後先後到安吉、象山、金華等地當知縣。
鄭天挺父親鄭叔忱,繼承了曾祖父的才學,在光緒十六年也就是1890年,也考中了進士,之後到翰林院任庶吉士。
庶吉士是明清兩朝翰林院內的短期職位,爲皇帝近臣,是明朝內閣輔臣的重要來源之一,一般在進士當中選擇最有潛質的人擔任。
後來,鄭叔忱於光緒二十八年後任奉天府丞、奉天學政、京師大學堂教務提調等職務。
鄭天挺母親陸嘉坤,也是一位知識女性,她“善作詩,操古琴”,有遺著《初日芙蓉樓吟稿》。
家學淵源爲鄭天挺今後的路鋪就了基礎,但其父母先後早逝。
父母託孤於親戚梁濟,之後鄭天挺和弟弟就被寄養在姨父家,由梁濟監護。
雖然雙親離世,又寄人籬下,但是鄭天挺沒有自怨自艾,他在學習上一直非常優秀,即使後來帶着弟弟單獨生活,也從來沒有耽誤學業。
他18歲的時候,從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考入了北京大學國文系。
在北大,除了學習國文課程外,鄭天挺還旁及其他專業的知識,在圖書館系統閱讀了《史記》《資治通鑑》等史籍,培養出了對史學的濃厚興趣。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鄭天挺也參加了北大學生會組織的活動,還代表北大到天津與南開中學聯絡,也曾參與街頭宣傳活動。
他還與朱謙之、許地山等十四名在北京的福建籍學生成立了社會改革學會。
此時的鄭天挺既是一個求知若渴的有志學子,也是一個充滿社會責任感的熱血青年。
他儘自己的力量發光發熱,探索屬於自己的人生道路。
亂世立身,勵圖治史
1920年夏天,21歲的鄭天挺從北京大學畢業後,先後在北洋政府經濟調查局、廈門大學有過短暫的任職經歷。
一年後,鄭天挺再次返回北京大學攻讀研究生,師從錢玄同。
在讀研期間,鄭天挺參與了北京大學主持的清代內閣大庫檔案整理工作,這項工作也爲他日後研究明清史奠定了基礎。
研究生畢業後,鄭天挺留校擔任北京大學講師,負責教授人文地理等課程。
在教學之餘,他對於史學的興趣愈加濃厚,併產生了“史宜立圖”、纂集《史籍考》的願望。
鄭天挺擔任北京大學講師兩年後。
他開始兼任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員,以及外國語專門學校的教員。
但是好景不長,1926年3月,北洋政府衛隊製造了318慘案。
北京大學和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數名學生在慘案中死亡,加上北洋政府欠薪嚴重,一年後,鄭天挺離開北大,轉去浙江省民政廳和浙江大學任職。
直到1930年底,鄭天挺才重回北大。
這次他出任北大祕書長,還兼任了中國文學系的教授,講授古地理學和校勘學等課程,並且主持編輯了《古地理學講義》,校勘《世說新語》。
三年後,他開始專注於明清史的研究。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北大師生紛紛離校南下。
在這種危急關頭,鄭天挺挑起料理校產和照顧未能脫身的教授們的重擔,並組織學生安全撤退。
而他自己則臨危不懼,照常辦公,在日本憲兵隊搜查北大辦公室時,依然堅守崗位。
8月底,“漢奸維持會”派人接收北大,鄭天挺纔不得不離開校園,準備南下。
在南下的時候,他成了大家的領頭羊。
他負責安排所有人的行程、管理圖書、實驗儀器的運輸、經費籌措及使用等事項。
1937年11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長沙組建成立了長沙臨時大學。
但沒過多久,由於長沙接連遭到敵機轟炸,長沙臨時大學決定西遷昆明,並在昆明改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到昆明後,由於校舍緊張,鄭天挺代表北大赴蒙自,籌備在當地分設文學院、法學院的相關事宜。
在蒙自的半年期間,鄭天挺除了教授隋唐五代史外,研究範圍還涉及了西南邊疆史和西藏史,先後寫作了《發羌之地望與對音》等文章。
1938年下半年起,鄭天挺開始在西南聯大教授明清史。
1939年5月,北京大學恢復文科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由鄭天挺主持。
1940年初,西南聯大總務長沈履離職,清華校長梅貽琦等人均推薦鄭天挺繼任。
就職後,鄭天挺開始忙於行政工作,負責處理聯大各種複雜繁重的校務。
爲了給西南聯大籌措經費,他還經常奔波於興文、富滇、勸業、礦業等銀行。
可以說,西南聯大能夠在戰火紛飛的時局下堅持辦學,鄭天挺厥功至偉。
鄭天挺也因此被稱爲西南聯大的“大管家”。
抗戰結束後,1945年8月底,北大開始計劃覆校事宜,決定組織遷移委員會,鄭天挺又受命返回北平接收校產。
可以說,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他始終爲學校事務鞠躬盡瘁,盡職盡責。
鄭天挺不是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弱書生,每逢危難之時,他總是挺身而出,義不容辭地擔起重任,爲其他師生保駕護航。
他身上體現了老一輩學者的使命感、責任感。
建設史學,著作等身
1952年9月,在北大教學7年後,鄭天挺被調去南開大學任歷史系主任、中國史教研組主任,開始了其後半生長達三十年的南開生活。
當時南開大學在教學方面有諸多不完善之處,鄭天挺到南開後,馬不停蹄展開了改革,並親自指定新的教學計劃,親自授課爲其他教師做示範。
他還在南開大學創建了明清史研究室,主持了校點《明史》等重要學術工作,並培養了大批史學學子,壯大了歷史學科的學術隊伍。
不僅如此,懷着強烈社會責任感的鄭天挺還積極參與全國性的史學建設活動。
比如擔任歷史學科評議組的召集人,帶領全國史學界編纂《中國歷史大辭典》,推動明清史領域的國際學術交流等,極大地推動了新中國歷史學科的建設。
雖然行政工作繁忙,但鄭天挺從未脫離史學的教學和研究。
即使是在抗戰期間,戰火紛飛,他又忙於西南聯大校務工作時,鄭天挺也一直有史學報告、研究出世。
鄭天挺在明清史、隋唐史、魏晉南北朝史、音韻學、歷史地理等方面均有學術論著發表;
且著作形式多樣,目前已出版的有學術專著1部,序跋文1篇,日記輯錄1部。
學術論文集3部,演講記錄5部,學術論文11篇。
他的主要論著,包括《列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志要》《清史探微》《探微集》《清史簡述》等,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學術價值。
1981年,由於積勞成疾,鄭天挺因病逝世於天津。
鄭天挺的一生,是與時代同行、與學術共進的一生。
他既是民國時期學術精神的縮影,也是中國近現代史學發展的見證。
他以深厚的學術造詣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學子,更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堅定的學術追求,成爲了中國史學界的一面旗幟。
他對於歷史學的深刻研究和獨到見解,亦爲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學術遺產和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