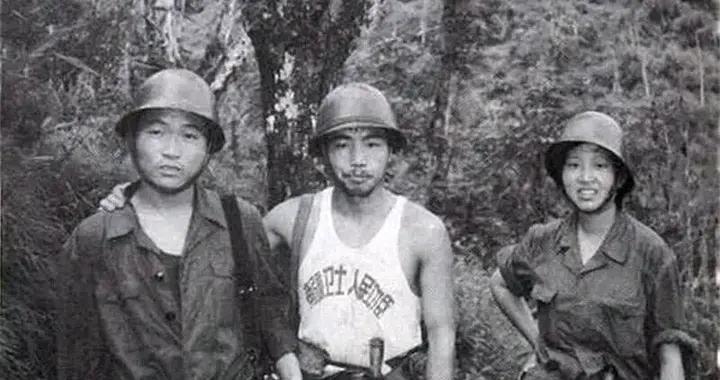漆身吞炭只爲報恩,用生命詮釋“士爲知己者死”
春秋戰國五大刺客中,曹沫以勇著稱,專諸以智取勝,聶政彰顯情義無雙,荊軻則用生命詮釋信諾之重。
而豫讓則以其極致的忠義,獨樹一幟,成了忠之典範。
我們熟知的“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便出自豫讓之口。
今天讓我們一起走進這位著名刺客豫讓的一生,去探尋那份超越生死、矢志不渝的忠義之心。

知遇之恩,情深意重
春秋戰國是一個禮崩樂壞、諸侯爭霸的混亂時代,也是一個是英雄輩出、百家爭鳴的黃金時期。
隨着傳統統治秩序的衰落,原本依附於王室、貴族的士人階層紛紛開始尋找新的出路。
他們憑藉自身的才學與智慧,遊走於各國之間,成爲諸侯競相爭奪的寶貴資源。
這些士人,有的擅長治國理政,有的精通兵法謀略,還有的擅長外交辭令。
他們的出現,極大地豐富了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生態,也爲後來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奠定了基礎。
豫讓就是其中一員。
他是當時的晉國人。
晉國是春秋第一強國,但是晉國國君早已大權旁落,權力都集中在智氏、趙氏、魏氏、韓氏、範氏、中行氏六個大家族手中,他們世代爲卿,史稱“晉國六卿”。
豫讓先後投效在範氏、中行氏門下,但是範氏、中行氏都不看重他,他感到懷才不遇,鬱郁不得志,便投效到晉國最強大的家族——智氏門下。
智氏,特別是智氏少主智瑤對他青睞有加,給予他很高的地位和優厚的待遇。
後來,智氏聯合趙、魏、韓三家,攻滅了範氏、中行氏,奪取了他們的土地。
再後來,智氏老家主去世,智瑤成爲新的智氏家主,隨後又成爲晉國的執政卿。
在這過程中,豫讓跟着智瑤,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地爲智氏衝鋒陷陣,立下了汗馬功勞。
然而,世事無常,風雲突變,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正在悄然醞釀。
智伯掌權後,心懷壯志,意圖將趙、魏、韓三家一併吞併,以成就霸業。
他首先向晉國公室獻地,以此爲藉口,強迫趙、魏、韓三家效仿。
趙、魏、韓三家明白,名義上是向公室獻地,但由於智瑤是執政卿,此舉其實就是變相地向智氏家族獻地。
面對智氏的強大壓力,魏、韓兩家因自身實力相對薄弱,權衡利弊之下,不得不忍痛選擇妥協退讓。
趙氏力量與智氏不相上下,便決定反抗。
智瑤見狀,率領魏、韓兩家圍攻趙氏。
然而,趙氏暗中與魏、韓兩家勾結,裏應外合,最終逆轉戰局,將智氏一舉擊潰。
公元前453年,智氏被韓、趙、魏三家攻滅,智氏領土被瓜分。
尤爲殘忍的是,對智瑤恨之入骨的趙氏家主趙襄子,竟將智瑤頭骨製成漆器盛酒,以示報復。
在這場浩劫中,深受智瑤信賴與器重的豫讓,不幸淪爲通緝對象。
他被迫遁入深山,心中卻時刻銘記智瑤的知遇之恩。
“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
他立誓要爲智氏報仇雪恨。
立志復仇,漆身吞炭
之後,豫讓更名改姓,僞裝成一名受過刑的人,偷偷潛入趙襄子的府邸中。
爲了方便行刺,他主動請纓,承擔起清理廁所這種旁人避之不及的髒活累活。
昔日,他是智氏的座上貴賓,享受着錦衣玉食、尊貴非凡的生活;
而今,他卻甘願化身爲低賤的僕役,只爲那一線復仇的渺茫希望。
在豫讓的貼身衣物深處,藏着一把鋒利的匕首,那是他精心準備的致命武器,計劃在趙襄子如廁之時,給予其致命一擊。
然而,命運似乎總愛與人開玩笑,就在那決定性的一刻,趙襄子步入廁所,目光不經意間掠過豫讓的身影,一絲熟悉感油然而生。
或許是豫讓初次行刺的緊張與不安,讓他不經意間露出了破綻。
趙襄子心下一沉,即刻下令讓人將豫讓帶至面前詢問。
當豫讓的身影逐漸靠近,趙襄子定睛一看,不禁大喫一驚——竟是豫讓!
他迅速示意衛士將其擒獲。
趙襄子親自審問豫讓,豫讓則毫無懼色,他的聲音堅定而有力:
“你殺害了我的主公智瑤,此仇不報,我誓不爲人!”
趙襄子身邊的侍衛們很生氣,打算殺掉他。
沒想到趙襄子卻搖了搖頭:
“智瑤死後,他以前的門客沒有一個站出來爲他報仇,豫讓卻能夠如此忠義。
此等賢士,實屬難得。
更何況,豫讓既然已經被識破,我也會提高警惕,他以後再沒機會接近我了。”
言罷,趙襄子放走了豫讓。
儘管豫讓重獲自由,但復仇的火焰仍在他心中熊熊燃燒,未曾有絲毫熄滅。
但趙襄子說的很有道理,他已經暴露身份,趙襄子又提高了警惕,成功的可能性已經不大了。
怎麼辦?
豫讓拿起鏡子,凝視着鏡子中的自己,狠下心來。
他找來生漆,塗在身上,沒幾天,他的皮膚開始潰爛,就像得了癩瘡一樣。
爲防聲音泄露身份,他拿起熾熱的炭火直接吞下,燒傷了自己的喉嚨,使自己聲音嘶啞。
即便如此,豫讓仍覺不夠,他狠心剃去鬍鬚與眉毛,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外貌。
爲了驗證他人是否能夠認出自己,他喬裝改扮成乞丐。
當他敲開自己家的大門時,連最親近的妻子也沒有認出他。
一天,一位故友偶遇這位形銷骨立的乞丐,感覺其身形氣質似曾相識。
他仔細端詳,小心地問:
“你難道是豫讓?”
豫讓回答道:
“是我。”
這位朋友目睹豫讓的慘烈轉變,心如刀絞,淚水不禁奪眶而出。
他哽咽着勸道:
“你何苦如此執拗,將自己逼至絕境?
我倒是有一個辦法,或許能夠助你輕鬆達成心願。
你僞裝投效趙襄子,以你的才智與勇氣,他定會視你爲心腹,屆時再尋機下手,豈不比現在這番自殘要容易得多?
你又何必將自己折磨至此,面目全非呢?”
豫讓聞言,眼神更加堅定,他緩緩搖頭,聲音雖嘶啞卻充滿力量:
“以臣子之身,行弒主之事,此等行徑,實乃亂臣賊子所爲,我豫讓豈能踏上這條不義之路?
我雖卑微,卻也知‘忠’之一字重如泰山,即便粉身碎骨,亦要堅守心中的道義與信念!”
說完,豫讓毅然決然離開了,踏上了他悲壯的復仇終章。
赤橋伏擊,悲壯落幕
豫讓用乞丐的身份作掩護,一直蹲守在趙襄子府邸附近,每天都觀察趙襄子的日常行蹤與出行規律。
豫讓發現,趙襄子每次出門都有一個必經之地——赤橋。
橋面上的空間比較狹小,下面就是湍急的水流,非常利於刺殺——空間狹小,趙襄子便不好躲閃,下面是河,如果一擊不中有將趙襄子推進河中淹死的可能。
於是,豫讓在趙襄子要外出的前夜,埋伏於赤橋下,靜靜等待趙襄子的到來。
這一夜,豫讓一夜無眠,他已經料到,這是他最後一次刺殺。無論成功與否,他都將無愧於心,因爲他已傾盡所有。
不久後,天亮了。
遠處,趙襄子的出行隊伍漸漸映入眼簾。
那熟悉的身影騎於高頭大馬之上,即將踏入他精心佈置的死亡之橋。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馬匹似乎預感到了即將到來的危險,突然嘶鳴起來,打破了清晨的寧靜。
趙襄子敏銳地覺察到了異樣,立刻下令隊伍停止前進,並展開嚴密的搜查。
僞裝成乞丐的豫讓終究未能逃脫搜查,他手中的匕首,在晨曦的照耀下閃爍着凜冽的光芒,卻也映射出他內心深處的無奈與不屈的悲壯。
趙襄子凝視着眼前的身影,經過一番仔細辨認,終於確認了這位不速之客竟是豫讓。
趙襄子既憤怒又震撼,也非常不解。
憤怒,是因爲他曾對豫讓展現過寬容,未曾料到對方竟會再次舉起屠刀。
震撼,是因爲豫讓爲了完成復仇,竟不惜如此自殘。
不解,是因爲豫讓之前不也是範氏、中行氏的家臣嗎,爲何偏偏對智瑤如此忠心?
於是,趙襄子以一種近乎質問的語氣對豫讓說道:
“您曾爲範氏、中行氏的家臣,智氏把他們都消滅了,你不替他們報仇,反而轉投智氏麾下。
如今智氏已亡,你又爲何獨獨執着於爲智瑤復仇?”
豫讓聞言,緩緩答道:
“我在範氏、中行氏那裏,不過一尋常家臣,他們都把我當作一般人看待,所以我像一般人那樣報答他們。
而智瑤則不同,他視我爲國士,以非凡之禮相待,此等知遇之恩,我豫讓自當以國士相報。”
趙襄子聽了豫讓的話,很受感動,但是他明白,這一次絕不可再心慈手軟。
兩次僥倖逃脫已讓他深知,再給予豫讓任何機會,都將是對自己生命的極大威脅。
於是,趙襄子下令讓士兵包圍豫讓,準備處死豫讓。
豫讓深知自己已經復仇無望,他想了想,向趙襄子請求道:
“我知道自己必死無疑,復仇無望。
但求能讓我以衣代首,象徵性地完成刺殺之舉,以此慰藉智瑤的在天之靈,報答他昔日的知遇之恩。”
趙襄子沉默片刻,緩緩脫下自己的外衣,遞給豫讓。
豫讓接過衣服,雙手顫抖,淚水在眼眶中打轉。
他猛地抽出寶劍,用盡全身力氣,一下又一下地砍向那件衣物,彷彿要將自己所有的憤怒、悲傷與遺憾都傾注其中。
直到筋疲力盡,衣物被砍得支離破碎,豫讓才停下手中的動作。
他仰天長嘯,聲音中既有解脫也有不甘:
“智伯啊,我豫讓雖未能親手取你仇人性命,但今日以衣代首,總算不負你對我的知遇之恩!”
言罷,他無力地拋下手中的衣物,任由其散落一地。
趙襄子見狀,心中五味雜陳,他轉過身去,輕輕擺了擺手,示意士兵們執行命令。
於是,在一片寂靜中,一代義士豫讓被無情的刀劍所吞噬。
“壯士死知己,青史留華章。”
豫讓雖然失敗了,但是其大義凜然,以身報恩的故事,卻跨越時空,代代流傳。
他的故事不僅是一段關於復仇與忠誠的傳奇,更是一曲人性光輝與悲劇交織的讚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