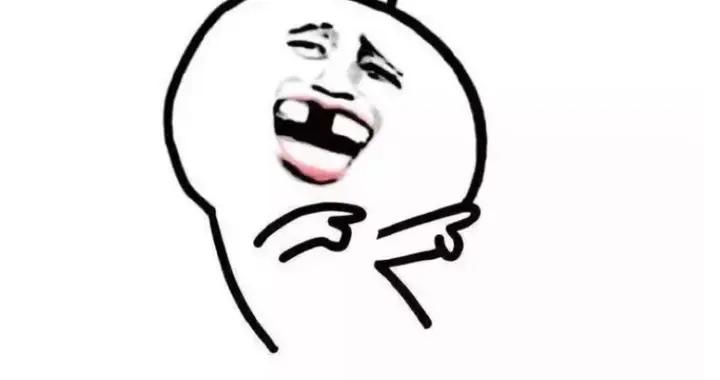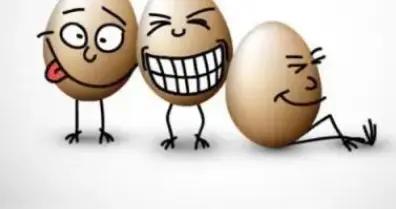《以美之名》將女性苦難熬成雞湯

《以美之名》以“首部醫美行業正劇”的姿態高調登場時,它試圖用手術刀剖開社會對“美”的執念,卻在縫合傷口時悄然注入了一劑甜膩的雞湯。劇中先天畸形患者“換臉”的生死抉擇、家暴受害者修復疤痕反遭網暴的荒誕敘事,看似直面女性苦難,實則將血肉模糊的現實創傷熬煮成“勵志奇觀”。這場以“生命尊嚴”爲名的縫合術,究竟是療愈還是二次傷害?

劇中,家暴受害者林小月的故事線極具代表性:她被丈夫毀容後求助整形醫生,卻在術後因“疤痕修復不徹底”遭受網絡暴力。這一情節本應揭露社會對受害者的結構性壓迫,但劇集的處理卻將矛盾簡化爲“技術不精”與“輿論偏見”的二元對立。當林小月最終通過二次手術“完美修復”疤痕,並在鏡頭前發表“疤痕是勳章”的宣言時,個體的苦難被置換爲“自我和解”的符號,而真正的施暴者——性別暴力與社會規訓——則悄然隱身。

更值得警惕的是“恐龍女”患者的敘事邏輯。這位因先天面部腫瘤被歧視的少女,必須在“保命”與“換臉”間抉擇。劇集以大量特寫鏡頭渲染她腫脹變形的五官,卻在手術成功後迅速轉入“重獲新生”的蒙太奇:陽光下飛揚的裙襬、社交媒體的點贊狂潮、職場逆襲的爽文式結局。這種將生理殘缺與人生價值直接掛鉤的敘事,本質上仍在強化“顏值即正義”的規訓,只不過披上了“醫學救贖”的外衣。

《以美之名》最弔詭之處,在於它一邊揭露黑醫美的“美容貸”陷阱,一邊將正規醫美塑造爲無所不能的救世主。劇中,姚晨飾演的喬楊反覆強調“醫者不能改命,但能帶來好運”,這句充滿宿命感的臺詞,實則是將系統性壓迫轉化爲個體命運議題。當先天畸形患者必須通過“換臉”才能獲得社會接納時,劇集並未追問“爲何社會無法包容差異”,反而將手術刀奉爲解決一切困境的終極答案。

這種“技術至上”的敘事邏輯,在雙女主從“宿敵”到“戰友”的轉變中達到頂峯。兩位頂尖整形醫生通過一場高難度手術修復家暴受害者的面容,鏡頭在無影燈下不斷切換她們默契配合的特寫,彷彿在宣告“女性互助”足以消解結構性暴力。然而,當受害者走出手術室後,她仍需獨自面對就業歧視、親子關係破裂等現實困境——這些真正刺破“美麗新世界”幻象的尖刺,卻被劇集刻意迴避。

主創團隊標榜的“七年調研百例真實案件”,恰恰暴露了創傷美學消費的核心矛盾:當現實苦難被提煉爲戲劇衝突時,其殘酷性必然被情節劇的敘事節奏稀釋。例如劇中“美容貸”受害者的故事線,本應揭露資本與黑醫美合謀的產業鏈,卻最終收束於一場“警方破案”的潦草結局。這種將複雜社會問題簡化爲“正義戰勝邪惡”的套路,本質上是用戲劇性快感替代了對制度性腐敗的深層叩問。

更值得玩味的是劇集對“美”的重新定義。當角色們高呼“整形整的不是臉,而是心”時,看似在批判容貌焦慮,實則將責任轉嫁給個體心理建設。這種“心靈雞湯”式的解決方案,掩蓋了審美霸權背後的權力運作:爲何女性必須通過“與自己和解”來適應扭曲的審美標準?爲何不能質疑標準本身?

現實題材劇集擅長用精緻的鏡頭語言縫合社會傷口,卻拒絕展示傷口潰爛的真相。當“女性力量”“自我覺醒”成爲消費苦難的新話術時,我們或許更需警惕這種溫柔化的暴力。 真正的現實主義不應是創傷的祛痛劑,而應是撕裂僞善的手術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