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未建交的錫蘭用橡膠換中國大米,全球南方今天怎樣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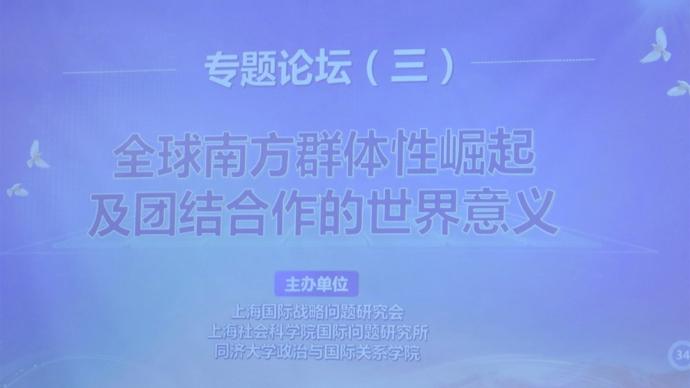

在不久前的中國-東盟外長會議上,王毅表示雙方要構建更爲緊密的命運共同體,在全球南方卓然壯大的歷史大勢中加快亞洲的振興;
剛閉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中國倡議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西班牙媒體稱此舉回應了全球南方的需求,有助於縮小數字鴻溝;而同期的“共贏金磚”論壇上,啓動了金磚國家人工智能產業合作網絡等多個平臺和項目,助力實現普惠化發展。
當全球南方成爲羣體性崛起力量時,如何合作成爲各界聚焦重點。
日前,在上海市國際關係學會等九家上海市社聯所屬學術團體聯合主辦的“世界和平發展與多邊主義國際秩序的未來”學術研討會上,以“全球南方羣體性崛起及團結合作的世界意義”爲題的分論壇討論尤爲熱烈,如何合作成爲焦點。

上海社聯2025年度重點合作項目·會長論壇“世界和平發展與多邊主義國際秩序的未來”學術研討會由開幕式和五個分論壇組成,雲集了滬上國際關係界核心話題和研究學者。分論壇爲“戰後大國關係的演變與地緣政治格局的重塑”“戰後東亞地區合作與亞太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全球南方羣體性崛起及團結合作的世界意義”“聯合國成立80週年與多邊主義國際秩序的未來”“中國式現代化助力世界和平與發展” 李念拍攝
兩種新理解:集體性與全球化
合作肇始於觀念的統一,對“南方”理解是觀念統一的源頭。如何界定“南方”?1980年,勃蘭特領導的南北委員會繪製了著名的“勃蘭特線”,依據地理位置和發展水平區分南方和北方,時至今日依然是全球南方這一概念最直觀、最爲人所知的定義方式。除此之外,全球南方也被視爲國際政治格局中的中間力量的集合體,是大國爭奪的空間。不同於這兩種解釋,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助理教授阮功松分享了一種新的理解路徑:全球南方的集體性源於共同經歷的殖民壓迫歷史所形成的跨越地域的集體情感紐帶。
1966年越戰期間,胡志明在一次對美國民衆的呼籲中說道:“爲什麼一個通過革命從殖民統治中獲得獨立的民族(美國),現在卻要鎮壓另一個爭取獨立自由的民族(越南)?”他的質問巧妙地喚起了被殖民民族的共同記憶,從這個角度看,全球南方認同是流動的、無處不在的,所謂“人人皆可南方”。

“勃蘭特線”代表全球南方的經濟維度,萬隆會議則彰顯反殖民色彩
對全球南方集體性的不同理解帶給我們新啓示。阮功松指出,儘管全球南方不是一個精確的地理位置,其內部的經濟水平和權力大小參差不齊,但是地理視角、發展視角和國際政治視角卻成功地喚起了全球南方人民的區域共同體想象,喚起了人們對於共同面對的貧困、債務、技術依賴等困境的重視,也喚起了人們追求獨立自主、反對西方干涉的願望。
“‘全球南方’,需要探討的不僅有‘南方’一詞,也有‘全球’。”上海國際關係學會副祕書長湯偉認爲,應當從“全球性”的視角來理解全球南方的羣體性崛起。
“全球性”首先體現在南方國家之間更爲密切的跨國交流。如今全球南方成員間的交流已不僅僅限於不結盟運動等政治運動,更擴展至經濟、文化、科技等多個層面,產業也相互交織。
“全球性”與全球化密切相關,在湯偉看來,過去的全球化具有強烈的“垂直等級特徵”。北方國家主導下,南方國家被動地融入全球價值鏈,並大多處於價值鏈下游,南方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往往依賴北方國家作爲中介,南方國家對外交往的空間受到侷限。然而,隨着南方國家的羣體性崛起,尤其是新興經濟體逐步成爲新的樞紐,南北垂直結構被打破,南方國家得以面向全球。

2025年裏約金磚峯會,圍繞新興經濟體全球南方國家彼此合作
米膠協定精神:跨越制度、大小
全球南方合作並非全新的事物,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些新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間就已經建立了寶貴的夥伴友誼。1952年,當時尚未建交的中國和斯里蘭卡(時稱錫蘭)簽訂了《米膠協定》。冷戰初期,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陣營實施嚴格封鎖、戰略禁運,而新中國正百廢待興,急需橡膠等物資進行建設。爲了緩解燃眉之急,新中國向錫蘭提供其需要的大米,以換取橡膠,“獨立自強、團結互助”的米膠協定精神自此寫入中斯關係史和第三世界合作史之中。
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王震眼中,全球南方合作興起的當下,這一協定有着更深層的歷史借鑑意義。錫蘭頂住西方壓力與中國簽約,表明小國同樣能夠維護自身利益、保持戰略自主。同時,協定也成爲大國與小國基於平等交往的範例,平等相待、患難與共、團結互助、自強不息的精神恰恰是廣大全球南方國家構建命運共同體的參照。“雙方的合作不僅是簡單的市場行爲、利益交換,也暗含着南方國家之間跨越制度差異的身份認同。”王震說道。

1952年,中國與斯里蘭卡在北京簽署《米膠協定》 圖源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
傳統援助退潮,撬動投貿成爲主力
當前,全球正面臨嚴重的治理赤字和發展赤字,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姚樂指出,許多全球南方國家所依賴的發達國家提供發展援助的模式正在衰落。2024年,全球前十大捐助國中,除意大利外,其餘九國的官方發展援助都出現了明顯的負增長。相較之下,發展援助正在成爲地緣政治競爭的工具,特朗普上任後美國大幅削減了對外援助預算,同時強調援助需服務於其外交戰略和國家利益。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資金缺口已從每年2.5萬億美元膨脹至約4.2萬億美元。”而全球南方國家正面臨着數字經濟轉型的壓力。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丁迪指出南方國家的普遍性問題:網絡帶寬有限、數據中心缺乏、算力嚴重落後。隨着發達國家憑藉技術優勢,通過出口管制和投資審查限制南方國家獲取先進數字技術產品,南北的數字鴻溝可能進一步加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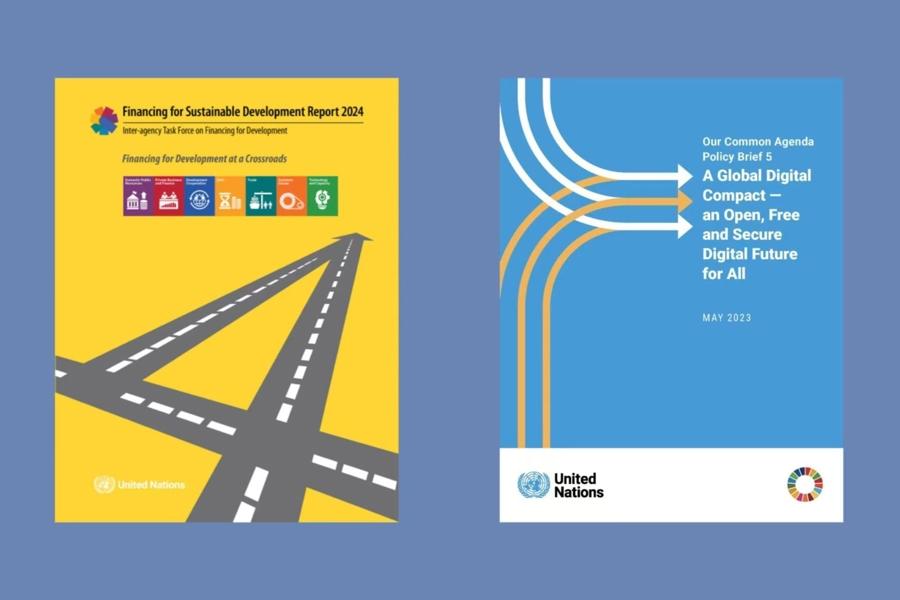
聯合國關注到,可持續發展資金缺口與全球數字鴻溝都在擴大
面對挑戰,以中國爲代表的新興國家爲全球南方發展合作注入了新動能。數據表明,2010至2019年間,13個主要新興經濟體國家向多邊機構提供的發展資金從1.3億美元躍升至63億美元。其中,中國是最大的貢獻者,佔比達34%。除了中國,印度、巴西、沙特、土耳其也貢獻巨大。姚樂分析,中國的援助不同於側重贈款的傳統援助,其更注重“以援助撬動投資貿易”,整合多元化資金促進投資驅動型增長。
在綠色轉型、數字轉型的浪潮中,全球南方探索創新合作模式至關重要。丁迪提出,可以借鑑中國參與設立亞投行、新開發銀行的成功經驗,探索設立支持全球發展與南南合作的專門基金,並進一步發揮中非合作論壇、中阿合作論壇等成熟平臺的作用。另外在全媒體時代,積極傳播自身發展理念與數字治理主張,倡導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也是全球南方不能忽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