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古史寫作新範式之誕生



一本面世於近百年前的書,今天還有重新出版的價值嗎?就在將近50年前,作者借用莎士比亞“無事生非”一語表明心跡,希望大家忘卻此書;今天,又一個50年快到了,作者已不能笑迎或冷拒,那麼讀者或編者又該如何思考呢?
《中國之誕生:中國文明的形成期》寫作於顧立雅即將結束1932—1936年在華研學生涯,返回芝加哥大學開創東亞研究和漢學傳統之際,既是剛過而立之年的作者的成名之作,也是西方漢學的奠基作品之一。與其它同時期乃至更爲晚近的漢學著述顯著不同的是,《中國之誕生》中,“中國”與其說是寫作的對象和範疇,不如說是方法和情境。顧立雅在華五年,正是中國新史學即將瓜熟蒂落之際。由於在哈佛求學期間導師梅光迪的熱心引介,顧立雅成功地進入北平學術羣體,他的記憶中宛如“重要的研討會”的晚餐的參與者正是中國新史學的代表性學者們。無論是他隨後的研究,還是《中國之誕生》的寫作,都極大地受惠於接下來的數年中騎車穿行於學者們家中的問學。因此,《中國之誕生》其實是中國新史學的成果,而不是從外部視角探索中國的產物。
顧立雅通過致謝和引用表明了自身和《中國之誕生》的知識譜系。在《自序》中,顧立雅特別向勞費爾和畢安祺兩人表達了謝意。雖然兩人都與初生的中國考古學或者藝術史有關聯,但勞費爾的推薦使顧立雅有機會求學於哈佛,畢安祺提供了《中國之誕生》的序言,勞費爾關於中國文明的基本觀點也被頻頻引用,但是他們的德奧歷史語言學傳統和基於博物館收藏的藝術史學術傳統都沒有對顧立雅形成實質性影響。對於顧立雅的中國關聯而言,梅光迪是更加重要的中介。彼時執教於中央大學的梅光迪爲顧立雅介紹了遊走於北平知識界的飯局、客廳和書房的契機。顧立雅恰當地總結了《中國之誕生》的三類基礎。首先是甲骨學的成熟。雖然甲骨早在1899年就出現在古物市場上,但直到20世紀20年代才最終誕生文字學和歷史學意義上的成果。其次是古史辨運動。最早於1926年集結的古史辨運動到20世紀30年代超越了單純的疑經辨古,開啓全新的以考古學、民俗學和歷史地理學新材料重寫中國史的新階段。其三,也是最爲重要的,是考古學。20世紀20年代,中國出現嚴格意義上的考古學,尤其是自1928年開始,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安陽殷墟連續地展開發掘,以安陽爲中心、以復原古史爲目的的中國考古學已經形成一定積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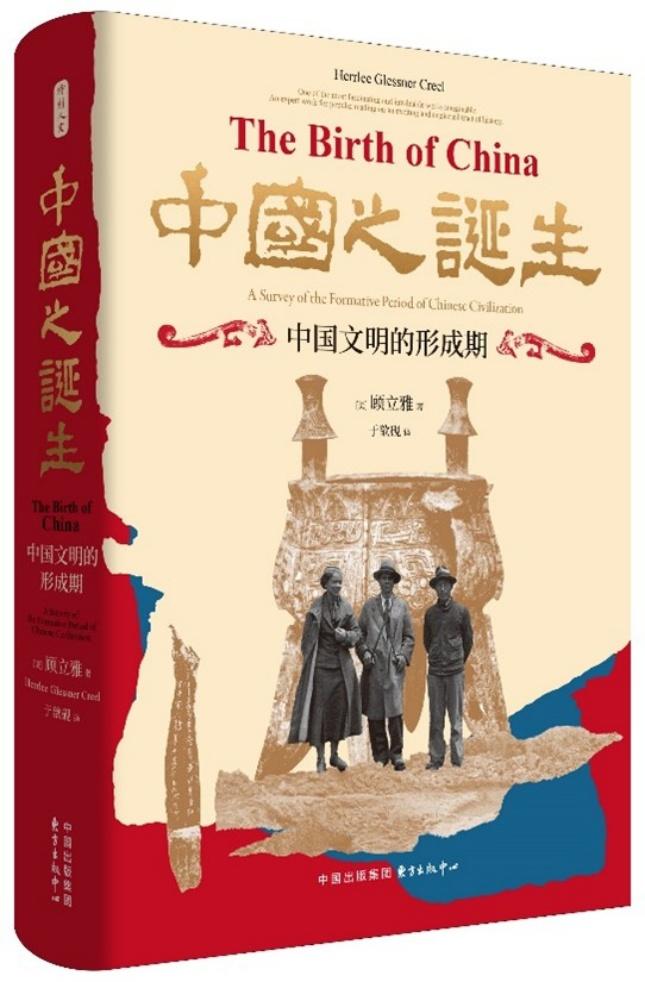
《中國之誕生:中國文明的形成期》,[美]顧立雅 著,於歆硯 譯,東方出版中心2025年出版
更具體而言,《中國之誕生》的內容顯示出顧立雅的早期中國知識來源的三條脈絡,分別是文字學、古物學和考古學。在文字和文獻一端,顧立雅主要受到北平圖書館劉節、同時受聘於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唐蘭的影響;而在甲骨文上,顧立雅則特別依賴於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董作賓。和早期西方漢學作者一樣,顧立雅也深受洋莊引導下的全球範圍早期中國藝術收藏的影響,除了以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卡爾伯克和堪薩斯柔克義納爾遜美術館史克門爲代表的西方博物館學者之外,顧立雅特別提及北京尊古齋黃伯川。後者與劉節、容庚、商承祚等皆很熟絡,也可能就是由他們介紹,並且爲顧立雅的寫作提供了諸多材料。《中國之誕生》中,方斝、觚、戈等器物都來自尊古齋收藏,也多出現在《鄴中片羽》中。
更爲得天獨厚的知識來源是新生的中國考古學。顧立雅主要得到李濟、梁思永、郭寶鈞、董作賓的幫助,得以進入到正在發掘之中的安陽殷墟現場,發掘者們也毫無保留地提供了他們的見解。1934—1935年,在李濟的安排下,顧立雅觀摩了安陽第九季和第十季發掘,這是安陽考古學在小屯經歷多年磨練之後,轉向西北岡王陵區的時刻,表明前八季的考古發掘已經積累起對晚商社會和歷史的基本認識。除顧立雅外,西方世界尚有伯希和、韓思復、卡爾伯克等人觀摩過安陽殷墟考古,不過,此時安陽考古資料尚未及時整理,中國田野考古報告的編輯也還在計劃之中,顧立雅成爲使安陽舉世皆知的最早的學者之一。由於他的信息來源審慎可靠,他對安陽的解釋基本都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更爲有趣的是,安陽並不是當時的中國考古學的全部,在殷墟之外,20世紀30年代初期同樣重要的考古工作是由郭寶鈞主持,與河南古蹟研究會聯合開展的豫北地區一系列年代在兩週時期的遺址的發掘。此時,浚縣辛村已被揭露和發掘,而汲縣山彪鎮和輝縣琉璃閣即將開始調查。顧立雅已經關注到前者,除了前往開封觀摩出土器物之外,還得到與郭寶鈞深入探討的機會。辛村成爲《中國之誕生》西周史寫作的主要素材。

圖源:視覺中國
《中國之誕生》的另一種新史學特質體現在以“歷史學”而非“漢學”的方式寫作中國上古史上。顧立雅熟知中國傳統文獻,但是有意規避了《殷本紀》確立的敘事體系,而更多地依靠《詩經》等非正史文獻、新見甲骨和金文文獻以及考古發掘材料。商代部分以核心遺址大邑商破題,漸次展開生產、生活、社會、權力、戰爭、書寫、信仰等內容。西周部分則按照政治、文學、社會、婚姻、家庭、生計、娛樂、宗教、法律等部分描述。在商史上,直到30餘年之後,殷墟發掘的領導者李濟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講學時才形成類似作品,以考古開始,繼而分門別類討論經濟、裝飾藝術、譜系和親屬關係、祭祀及體質人類學。而西周史的新史學範式寫作出現得更晚。顧立雅可能面臨材料不足的問題,也會夾雜學術草創時期常見的錯漏,但即使在李濟《安陽》或者許倬雲《西周史》中也不可避免,而《中國之誕生》的開創之功不可否認。在顧立雅的筆下,“中國”不是特殊而孤立的文明形態,而是世界上重要的文明類型之一,是西方世界需要理解而且可以理解的。這在全書終章“天命”中表現得尤其淋漓盡致。這也使得《中國之誕生》頻頻被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興起的全球史寫作,以及晚至崔格爾的《理解早期文明》等比較研究徵引。
《中國之誕生》能讓今天的讀者讀起來仍然甘之若飴,得益於作者的寫法。這是作者投入到更學術的《中國早期文明研究》的寫作中的副產品,卻具有超越漢學的影響力。寫作《中國之誕生》時,以及在隨後的學術生涯中,顧立雅對思想史和治理史更感興趣,在《孔子:其人與神話》《中國治國之術的起源:西周》和《申不害:中國公元前4世紀的政治哲學家》中,可以看到梅光迪對他的更多影響;而在《中國之誕生》裏,他則更受與學衡派針鋒相對的學者羣體的影響和幫助,甚至可以說,這就是新史學最好的作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