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裴麗珠到魯迅:近代中國城市的三種生活切片



晚清至民國的中國經歷了劇烈的時代變遷,北京的城牆、天津的租界、上海的里弄都見證了東西方文化的碰撞與交融。這當然是從大處着眼。如果從具體生活這一角度切入,則微觀層面的細節會帶給我們理解歷史的更豐盈的感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裴麗珠的《北京紀勝》、李來福的《晚清中國城市的水與電》及上海魯迅紀念館編的《魯迅上海生活志》,穿透了表面的互不相關、各有主題,於內在肌理上有了交疊的意義。
裴麗珠的北京情緣
裴麗珠何許人也?聽說過她名字的讀者恐怕不多,但提到另一個名字羅伯特·赫德,知道的人可就多了。這個出生在北愛爾蘭的英國人,曾任晚清海關總稅務司半個世紀之久,將中國的關稅大權操弄於股掌之間。裴麗珠和赫德有關聯嗎?還真有,裴麗珠的父親裴式楷(Robert Edward Berdon)是赫德的妻弟。東方式人情講究“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其實西方也一樣。赫德擔任總稅務司期間任用親友,培植私人勢力,將裴式楷從英國召至中國,進入大清海關,步步高昇,做到副總稅務司的高位。
裴麗珠是裴式楷的獨生女,1881年生於中國,幼年和父母在漢口生活,1897年隨父親搬到北京,在這裏一住40年,成了一名地道的“老北京”。
1920年,裴麗珠出版過一本書《北京紀勝》,此後多次再版,享有盛譽,林語堂盛讚其爲“關於北京的最全面的著作”。從內容看,《北京紀勝》將北京的城牆、城門、宮苑、園林、寺廟、自然風景乃至生活景觀一一道來,相當於一本遊記。但它又不同於一般的遊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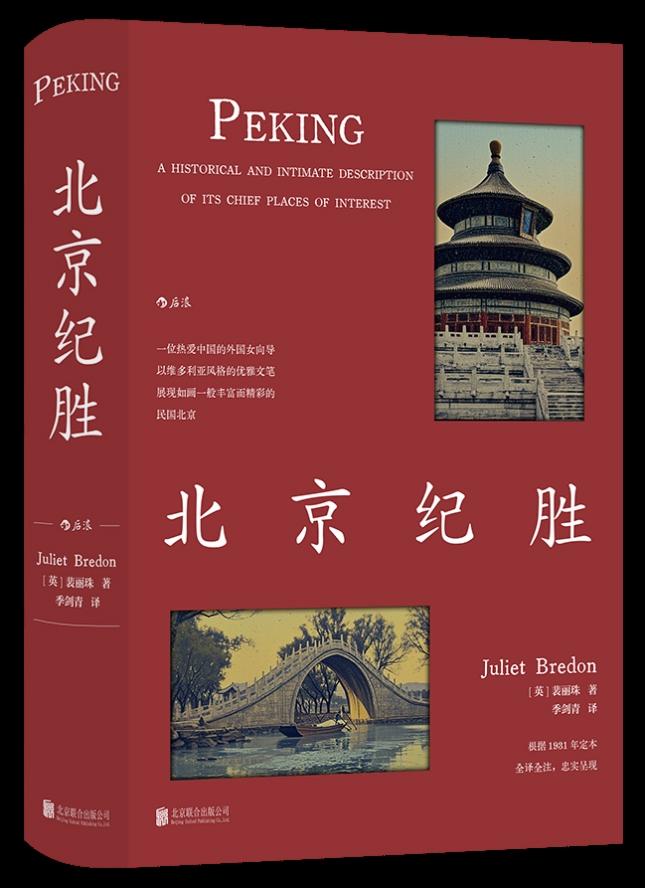
《北京紀勝》,[英]裴麗珠 著,季劍青 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5年出版
首先是文筆很出色。裴麗珠在序言裏說,讀者翻閱這本書,會產生一種作者“挽着你胳膊”逛遍北京及其郊區的感覺。可見她十分注重閱讀體驗,想爲讀者營造身臨其境的體驗感。更重要的,是姿態和視角。
本書譯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季劍青指出,當時的西方人普遍將北京視作典型的“東方奇觀”,他們建構的北京形象充斥着經過西方濾鏡裝扮的異域風情,目的在於凸顯前現代的中國與現代歐洲之間的巨大差距。這樣的北京看起來獨特,其實很大程度上出自西方遊客的想象與投射。
裴麗珠不一樣。她的文字很少帶有獵奇色彩,相反,她試圖發掘北京和歐洲城市的共性。她寫北京街頭小販的叫賣聲,說“如同倫敦的魚販子和巴黎的四季商人那般悅耳”;寫清朝官員坐轎子出行的陣仗,用“倫敦的市長巡遊”作對比;記錄趕大車的風趣俚語,說他們有着“拉伯雷式的滑稽幽默”。這一方面可以理解成寫作策略,有助於讓對東方一無所知的西方遊客藉助自己熟悉的文化背景快速瞭解北京;另一方面,也是源於她對北京的真愛。
晚清民國時期北京(1928年更名爲北平)的外國人,以外交官及其家屬、傳教士、教師爲主,他們大多住在東交民巷的使館區,同本地的人和事沒有太深的勾連。裴麗珠則是真心熱愛北京。她熟悉古都的風土人情,還習得了一口流利的北京話,能和普通市民深入交流。因爲經常在家裏招待客人,她也是北京社交圈著名的沙龍女主人。凡此種種,使北京對裴麗珠來說不構成奇觀或異域,而是生活和精神上皆有緊密連接的第二故鄉。作家寫故鄉,筆下自會流淌出細膩的愛和貼近的體會。這並不是說裴麗珠看不見東西文化之間的明顯差異,她當然看得見,但不會居高臨下地評判。而且面對美好事物,她會遵從人類的愛美天性,由衷地發出讚美。此種真誠的態度,難能可貴。
1937年夏初,裴麗珠和丈夫去日本度假,期間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中國軍民奮起反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突燃的戰火阻斷了歸途,裴麗珠只得輾轉前往美國。是年底,她因心臟病突發在舊金山辭世,享年56歲。
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翌年將北京更名爲北平,此舉極大削弱了北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使其變成了一座普通城市。同時隨着政府機關南遷,衆多官員、社會名流離開,經濟也遭受打擊。在失去政治和經濟中心地位後,官方重新界定北京的身份,藉助“帝都遺存”,將其定位爲“文化城”。這與《北京紀勝》的內容高度匹配。裴麗珠介紹了中南海、景山、天壇、國子監等人文景觀,她對街頭巷尾的描摹,更顯示北平還擁有豐富的市井文化和濃郁的煙火氣。這也是爲什麼100多年過去了,《北京紀勝》作爲遊記的指南功能已消退,卻仍有閱讀價值——它留存了舊日北京的樣貌與氣息,從而成爲一份珍貴的歷史人類學記錄。
丹麥工程師和近代天津
如果說晚清民國的北京/北平還是一座非常傳統的中國城市,那麼距離其120公里的天津則是另一番景象。
天津是近代中國較早被闢爲通商口岸的城市。1860年英國率先在天津設立租界,頂峯時天津共有九國租界,總面積超過15平方公里。這固然是一段屈辱的歷史,但租界當局也給傳統中國吹入新風,比如開展市政建設,創辦銀行、企業、教堂、學校、醫院等,將天津帶入現代化進程。至19世紀末,天津已經是當之無愧的北方金融中心及中國第二大工商業城市了。
關於外國人在近代天津的活動,學界更多注意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另一個小衆羣體丹麥人則被忽視。這也不難理解,比起英法德等列強,國小民寡、在天津又沒有租界的丹麥確實沒什麼存在感。但這不代表丹麥人缺席了。丹麥漢學家、哥本哈根大學歷史學教授李來福翻遍丹麥國家檔案館、天津檔案館,撰寫了《晚清中國城市的水與電:生活在天津的丹麥人,1860-1912》一書,聚焦晚清時期天津丹麥人的工作與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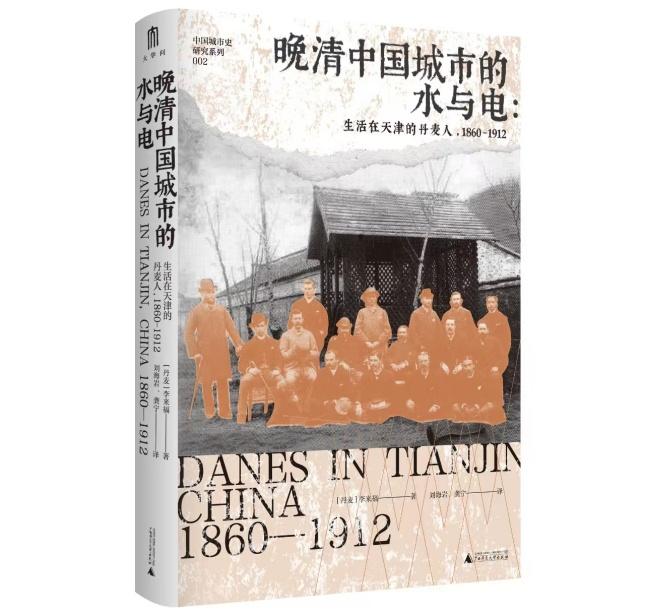
《晚清中國城市的水與電》,[丹]李來福 著,劉海巖 龔 寧 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5年出版
從1860年到1912年的半個多世紀裏,有大約150名丹麥人定居天津,他們受僱於租界當局或商業機構,充當工程師、商人、水手等。李來福重點觀照工程師的作爲。據他研究,這些丹麥工程師對天津乃至中國的現代市政建設發揮了重大作用。1871年來華的卡爾·璞爾生,曾爲大清電報總局下轄的電報學堂編寫教材,幫清政府培養通信人才;爲盛宣懷主管的天津電報局安裝電話線,推動中國電話事業發展。另一位工程師勞裏茨·安德森參與過海河治理工程,還設計了天津最早的現代化下水道系統。
除了工作,李來福還勾勒出一幅生活圖景。例如,在璞爾生的建議下,他的弟弟也來到中國發展,在海關任職。兄弟倆後來娶了當地歐洲僑民家庭的女子爲妻,住在英租界的一棟西式洋房裏。他們用歐式傢俱,過歐式生活,但餐桌上也會出現中式菜餚。兄弟倆的孩子在華洋雜處的環境里長大,既會說丹麥語和英語,也能用天津話作簡單交流。
遺憾的是,因資料有限,《晚清中國城市的水與電》整體寫得比較簡單,人物故事按粗線條展開,缺少細節的豐盈。這當然是求全責備。畢竟,書中人都是凡夫俗子,能在檔案裏留下痕跡就不錯了,豈能奢望?十多年前有過一本《租界生活:一個英國人在天津的童年》,作者布萊恩·鮑爾是在天津出生並長大的英國僑民,所述的租界風貌頗可一觀,可與本書相互映照。
魯迅的煙火上海
事實上,近年來這類從生活史角度觀察和書寫中國城市的著作出過不少。例如,三峽大學教授胡俊修的《民國武漢日常生活與大衆娛樂》,聚焦民國武漢的都市社會和大衆娛樂。澳門大學歷史學教授王笛那本備受讚譽的《茶館: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與復興》,透過茶館這一“微觀世界”,描繪了成都幾十年間的變遷。至於上海,更是憑藉豐富的史料成爲研究富礦,甚至發展出了“上海學”。
有關近現代上海生活的書已是俯拾即是,這裏我推薦一本比較特別的——《魯迅上海生活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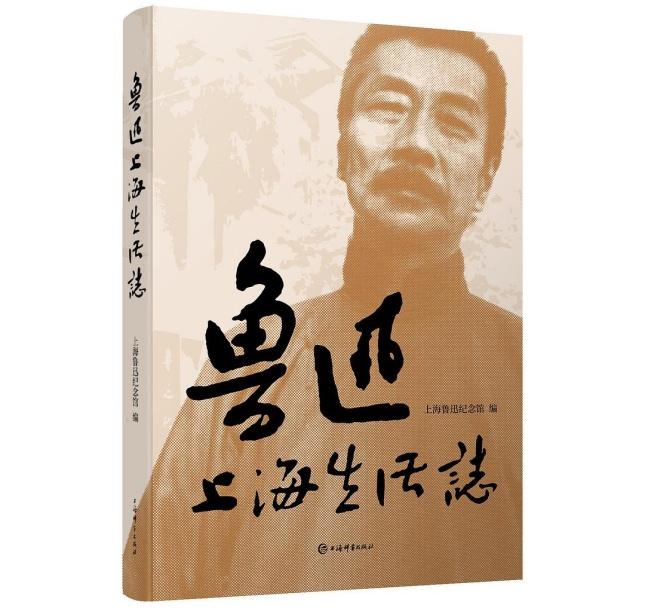
《魯迅上海生活志》,上海魯迅紀念館 編,上海辭書出版社2024年出版
作爲現代中國文壇“天王巨星”級別的人物,魯迅研究自成一門顯學,其生平、作品、思想早就被翻來覆去解讀了個遍。不過,或許由於星光耀眼,反而遮蔽了日常性的一面。魯迅的最後十年是在上海度過的,他住在哪兒?喫什麼?穿什麼?玩什麼?和這座城市的關係如何?這些都是值得研究並呈現給公衆的。
這方面,上海魯迅紀念館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建館至今70多年,其收集了大量與魯迅有關的物質材料,足以爲魯迅及其家人勾勒出一部上海生活史。匯聚衆多研究者編寫的《魯迅上海生活志》,正是這樣一部書。
該書以紀念館保存的魯迅生活遺物爲研究對象,分爲“書房一隅”“尋常煙火”“休憩時刻”“此中甘苦”“居於滬上”等五部分。涉及的物品可謂琳琅滿目,除了一般文化人都有的印章、信箋、藏書、墨硯、書櫥等,還有冰箱、衣物、家庭常備藥等。從諸多細節可以推斷出,無論魯迅對“海派”持何種態度,他和家人已深度嵌入海派生活之中。
魯迅喜歡看好萊塢電影已是衆所周知,讀了這本書,我還有新發現。例如,從前我只知道魯迅愛喝家鄉紹興的黃酒,讀了邢魁的文章,才發現他也常喝啤酒,甚至喝葡萄酒、威士忌;吳仲凱則描繪了一個愛喫糖的魯迅,既愛柿霜糖、核桃糖等中式糖食,也愛水果糖、檸檬糖、朱古力等外國糖食;鄭亞聚焦館藏的11件花瓶,告訴我們魯迅有很高的審美品位,這和蕭紅筆下那個對色彩敏感、對穿搭頗有心得的魯迅恰可互相印證。
在這個意義上,《魯迅上海生活志》將魯迅還原成爲周樹人——他不再晦澀難懂,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曾行走於世間的人。
如果說裴麗珠筆下的北京,是挽着胳膊帶你感知日常的溫度與人性,丹麥工程師在天津的足跡,是現代化浪潮中異國工匠嵌入城市血脈的無聲鑿痕,那麼魯迅遺物構築的上海生活志,讓我們得以窺見文化巨擘在都市煙火中的真實側影。這些散落的歷史碎片,如同穿越時空的棱鏡,折射出近代中國城市多元、複雜而充滿張力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