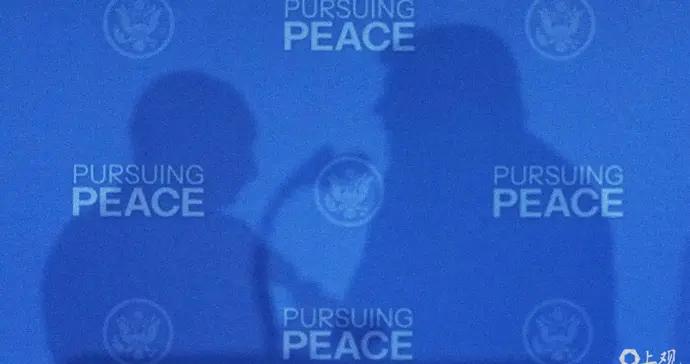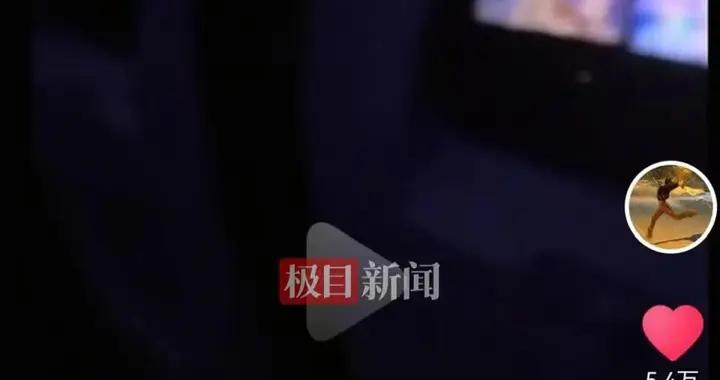讓張軍圓夢的“重逢《牡丹亭》”,是老少皆宜的“崑曲文創”


新編崑曲“重逢《牡丹亭》”和剛在紐約首秀成功的原創舞劇《白蛇》,同屬上海大劇院的“東方舞臺美學”系列。“重逢《牡丹亭》於2022年在上海首演引發熱議,時隔三年,“重逢《牡丹亭》”迎來和觀衆重逢——8月16-17日,這部“亦新亦舊”的《牡丹亭》將在YOUNG劇場演出。
最近的一場主創分享會前,在劇場後臺,YOUNG劇場的節目總監包含和導演馬俊豐探討:“遵守崑曲表演程式的前提下,這個經典文本能不能以更激進、更先鋒的形式重構?”與此同時,主演張軍斟酌着和導演商量:“一些生旦對手戲的調度是不是改回傳統的路子?”新和舊,先鋒和傳統,這些看起來矛盾的特質平行地存在於“重逢《牡丹亭》”,造成它很難被定義和概括的表演氣質。它在“新”和“舊”的兩個方向做到極致?還是作出折衷的調和?這是“重逢《牡丹亭》”歸來時,留給觀衆來解開的謎題。

羅周的劇本讓張軍覺得“圓夢”
《牡丹亭》的演出版本衆多,主演張軍在1998年演過長達六晚、21小時的《牡丹亭》,也在朱家角課植園演了很多場75分鐘園林實景版《牡丹亭》。在過去的幾個月,上海崑劇團的55折全本《牡丹亭》四月在武漢連演三夜,北方崑曲劇院標榜的“宮廷風格崑曲”《遊園·驚夢》七月在上海大劇院演出。通常由經典摺子戲《遊園》《驚夢》《尋夢》《拾畫叫畫》組成的“串折版《牡丹亭》”,則是全國各家崑劇院團的“喫飯戲”。
編劇羅周改編的“重逢《牡丹亭》”與諸多常見演出版本的不同在於,她改寫了原作的時間線和敘事結構,青春少女杜麗娘不曾活過,出場就是遊魂女鬼。原作開篇有《言懷》一折,遠在嶺南的柳姓書生自述夢到美人立在梅樹邊,他醒後改名柳夢梅。他夢中的女子即貴族少女杜麗娘,之後,湯顯祖的筆觸轉向杜麗娘的閨閣生活。“重逢《牡丹亭》”由《言懷》起興,略過杜麗娘,直接快進到柳夢梅的《拾畫》,其後上演人鬼情未了的《幽媾》《冥誓》,結束於《回生》。張軍形容,這個劇本讓他感覺“圓了一個夢”。
導演馬俊豐回憶,劇組兩年前赴中國臺灣演出時,他擔心這個劇本“是不是改太多,太先鋒了,觀衆接受不了”,結果劇院滿場,白先勇去了都差點沒座。扮演“石道姑”的李鴻良則盛讚,這麼“新”的《牡丹亭》只會出現在上海的演出環境裏,註定由馬俊豐和羅周這些敢破敢立的“新人”來實現。
其實,把《牡丹亭》的表演重心傾向小生柳夢梅,這是有前例可循的。李鴻良是江蘇省崑劇院的“舊人”,省昆早在1986年創排由石曉梅主演的《還魂記》,據記載,當時擔任劇本整理改編的丁修詢“以柳夢梅爲主線的摺子戲捏合五場戲,分別是《序幕》《拾畫》《幽媾》《冥誓》和《回生》。”就文本的取捨而言,羅周的選擇沒有打破早年的改編思路。

擔心被柳夢梅帶跑偏的杜麗娘
儘管女主角單雯現在的身份是南京藝術學院的老師,離開了省昆,不再像過往那樣頻繁地出現在崑劇舞臺上,她仍然強調,杜麗娘這個角色是她作爲閨門旦的起點,也是她追求的終極目標。杜麗娘是她演得最多、也最深入人心的角色,“重逢《牡丹亭》”對她來說卻是一部“新戲”。儘管,“這一版的每一句都是湯顯祖筆下原汁原味的經典”,但是,她常常忍不住笑說:“排練和演出的時候,唱詞會‘混’,總擔心不要被張軍哥哥帶‘跑偏’了。”
羅周的劇本略過杜麗娘的“生前”,從柳夢梅的《言懷》直接《拾畫》,這不僅摺疊了時間,還把劇情摺疊了。杜麗娘雖以鬼魂登場,但《遊園》《驚夢》沒有被省略,《遊園》被拼貼進《拾畫》,《驚夢》進入《回生》。當柳夢梅進入頹敗的花園時,杜麗娘在魂遊故地,原作的一雙少女遊春,被改寫成人鬼殊途的“生旦雙遊園”,旦角唱“雨絲風片,煙波畫船”,小生和“蒼苔滑擦,寒花繞砌”。“重逢《牡丹亭》”三年前首演時,當時有觀衆評價:“讓原作的名場面如蒙太奇穿插上演。”
張軍在一次講座裏,用一則花哨的標題概括“重逢《牡丹亭》”:“在我的夢裏看到你的夢”。說是“重逢”,行動的主動權和主體性從杜麗娘轉向柳夢梅。湯顯祖塑造了一個在文學史中不多見的作爲客體的男主角,是少女杜麗娘做了一個勇敢的夢,她死後在地府的審判中勇敢地面對那個夢,也是化作遊魂的她主動地重返人間尋找夢中人,甚至,當她重生醒來,是她主動地對柳夢梅言說舊夢。到了“重逢《牡丹亭》”,羅周再三強調“雙向奔赴”,她把《驚夢》安插在《回生》的位置,要讓柳夢梅發現杜麗娘就是夢中人,他的意志和行動決定了這段“人鬼戀”終得圓滿。張軍欣賞羅周的改編,尤其,“在《冥誓》中有一段原創唸白,非常重要,這段唸白有些燒腦,經過導演的雕琢,這成爲這個作品當代性的代表——《驚夢》是總結,開始和結果是重合的。”少女做夢的權利讓渡給書生,儘管如此,馬俊豐還是堅持:“怎麼改都行,只要審美精神和湯顯祖是一致的。”
“重逢《牡丹亭》”重組了《牡丹亭》里耳熟能詳的曲牌和表演段落,開創生旦唱和的“支聲復調”,伴以大量西洋樂器的加入,以及舞臺美術中引入版畫和鏡面,遊園驚夢演成“遊園鏡夢”……如此種種,讓古老的《牡丹亭》煥然一新。上海戲劇學院教授郭晨子感慨,如果作爲“非遺”的崑曲是文物,那麼“破圈”之後和觀衆雙向奔赴的“重逢《牡丹亭》”,大致相當於“崑曲文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