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爲這紛至沓來而輕輕碰杯——2025年,一些書,一些思緒



“謊言般衆多的星辰,抬頭一看,明光耀眼”
冬至已過,冬天彷彿沒有如期而至,不見呼嘯的寒風,更談不上白雪皚皚,鄰家爬牆的月季還在妖嬈盛開。不過,世界並不一律,比如,我的家鄉昨天就下雪了。我把雪落大地的圖片發到微信朋友圈,很多人問:你去哪裏了?哪兒也沒有去,躺在家裏的沙發上,拿了一個手機,數字技術幫了忙,從監控中截圖。當然,如果我手持一個小小的閱讀器,等於掌握了一座小型圖書館。
這是2025年,這就是我們的生活。不知不覺中,21世紀過去了四分之一。
我坐在書房裏,用古老的方式也可以穿越古今,遍覽千山萬水,那就是閱讀。在上海20℃的冬日,我體驗冬夜裏一個人面對星空的感覺:
嚴酷的夜景。沒有月。謊言般衆多的星辰,抬頭一看,明光耀眼,閃閃飄浮,似乎皆以虛幻的速度繼續沉落下去。羣星漸次接近眼眉,天空漸漸高遠,夜色更加幽邃。國境的山巒重重疊疊,模糊難辨,厚重的黑暗沉沉垂掛於星空的四圍。一切都達到了一種清雅和靜謐的調和。([日]川端康成《雪國》第40頁,陳德文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7月版)

中信版“無界文庫”
人同此心,川端康成筆下的此情此景,我在東北老家的小曲屯多次體驗過。這次重讀的機緣是《雪國》收入“人文經典文庫”出了文庫本。這是一個規模不小的出版計劃,書目涵蓋古今中外。2025年4月,中信出版集團的文庫本“無界文庫”上市,同樣古今中外,兩家打擂臺。於是,我手裏有了兩本《雪國》,譯者不同,譯法也不一樣。“星空”的那幾句,後者譯作:“抬頭望去,繁星多得出奇,燦然懸在天際,好似正以一種不着痕跡的快速紛紛地墜落。”([日]川端康成《雪國》第51頁,高慧勤譯,中信出版集團2025年4月版)
2025,是文庫本出版年嗎?儘管不是今年始,但是今年這股浪潮特別洶湧。後浪諮詢出版(北京)有限公司、江蘇文藝出版社合作的“後浪插圖經典口袋本”因有插圖,十分討人喜歡。巴金故居與作家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巴金小說系列》(十種,作家出版社2025年11月版)選擇文庫本,考慮的也是方便閱讀,期望書走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圖書版本多元化,是出版社放下身段積極向讀者需求靠攏的一種表現。2025年,是中國紙質出版的轉折年,危機也許帶來轉機。比如,從“背心”到“包袱”,文創儼然是出版社轟轟烈烈開闢的第二戰場。

《巴金小說系列》,作家出版社2025年出版
“你有多少天沒笑了”
2025年,是文學與“聲名狼藉”親密接觸的一年。青年作家要愛護,卻不必嬌寵,更不能拔苗助長。在寫作態度上,那些寶刀不老的作家仍舊是榜樣:這兩年,王安憶有《兒女風雲錄》,葉兆言有《璩家花園》,張煒有《去老萬玉家》,蘇童有《好天氣》,賈平凹有《消息》,陳建功有《請在我髒的時候愛我們》,餘華有《盧克明的偷偷一笑》,劉震雲有《鹹的玩笑》等長篇小說。韓少功出了荒誕故事集《張三李四》,高唱“青春萬歲”的王蒙90歲了,《霞滿天》《薔薇薔薇處處開》《奇葩奇葩處處哀》朵朵開放……哪怕你可以說餘華老師那本《盧克明的偷偷一笑》,怎麼看你都不笑,但是,作家只要不是活在段子裏、短視頻上,而是在寫作中,或成或敗,我都豎起大拇指。現在是文學不熱鬧,文學活動太熱鬧。“我想到米蘭(昆德拉)一再重複的話。他說傳記就是一劑毒藥。他說作家應該儘量不要(暴露)生活。或者說,他應該隱身於作品之後”。([法]弗洛朗斯·努瓦維爾《寫作,多麼古怪的想法!》第205頁,袁筱一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5年6月版)

《寫作,多麼古怪的想法!》,[法]弗洛朗斯·努瓦維爾 著,袁筱一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5年出版
作品纔是作家第一面孔,也彰顯作家的心。初讀劉震雲《鹹的玩笑》(人民文學出版社2026年1月版),感覺劉老師是在爲家鄉縣城做文旅代言人,是在給大家上人生哲學課還有唐詩複習課,看着看着才發覺他在爲那些倒黴蛋、那些根本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人代言。這些人有美好時光嗎?有,可能也見不得陽光,比如跟按摩女偷情。杜太白曾對麻煩重重中的前同事申時行發出這樣一句靈魂拷問:“老申,你有多少天沒笑了?”這個問題,讓我也愣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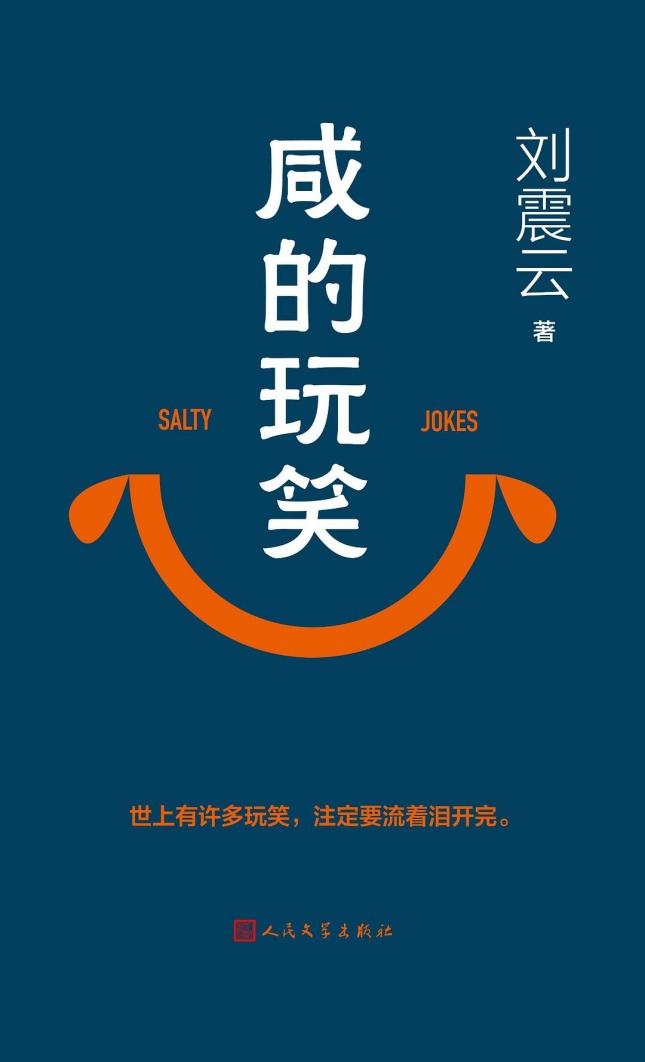
《鹹的玩笑》,劉震雲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6年出版
“世界好複雜,我應付不了。”(第427頁)杜太白哭訴他“動輒得咎”,曹五車在城牆上罵得清醒:“對一個人的不公,就是對所有人的威脅,包括你們自己,懂嗎?”對於相互戕害的底層他又質問:“把杜太白殺了,能改變你們受欺負的命運嗎?”原來劉震雲老師是個哲學家。
“接受我們的平庸”
與職業作家寫作處在不同狀態的是另外一羣人,有人稱之爲“素人寫作”。於是,便有了礦工詩人陳年喜、快遞詩人王計兵、《我在北京送快遞》的胡安焉、“菜場作家”陳慧……我不大喜歡用某種身份標籤來稱呼作家,作家跟作品有關,靠作品說話,跟寫作者的身份關係不大。
這一羣寫作者倒是給被職業作家弄得乾枯、圓滑、套路的文學圈吹進了一股清新的風。他們不用吆吆喝喝地去體驗生活,他們就在熱氣騰騰或冷似寒冰的生活中。陳慧這樣描述:“2006年的初夏,我常常是這樣度過的:凌晨三點多,我將尚在睡夢中的九個月的兒子抱給隔壁房間的婆婆,然後騎上自行車,順着黑咕隆咚的弄堂趕去距菜市場不遠的我小姨娘家,把寄存在她家的一大堆小百貨用三輪車拉去菜市場擺地攤。”(《在菜場,在人間》第245頁,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12月版)她穿過黎明前的黑暗,迎來清晨的忙亂,還有無言的生活負擔。寫作,不是無病呻吟,而是生命的表達。他們可能還不習慣思想,卻也不知道粉飾;他們的寫作技術可能不夠成熟,只會忠實地記錄。然而,對於當代中國文學,記錄也是神聖的職責,真實則是它的防腐劑。張賽在《在工廠夢不到工廠》(上海譯文出版社2025年8月版)序言中說:“直面生活纔是重要的。”瑤族女作家扎十一惹在《我是寨子里長大的女孩》(上海譯文出版社2025年8月版)中轉述她朋友的一段話:“我又老、又醜、又笨地在活着。”她的感慨是:“接受我們的平庸,接受自己又老、又醜、又笨,接受人類虛弱的本質,但又堅持着生活下去。”接受也許是一種無奈,正視“醜陋”的、不完美的自我,則是一種成熟的心態。

《我是寨子里長大的女孩》,扎十一惹 著,上海譯文出版社2025年出版
當然,他們的文字的價值絕不僅僅是原料新鮮,它們也漸成風格正顯個性,我這裏指的是陳慧的作品。我讀過她的《在菜場,在人間》和《她鄉》(天津人民出版社2025年7月版)兩本集子,書中那些來自底層的人物形象,讓我聯想到魯迅的《吶喊》和《彷徨》,它們都畫出了中國社會中生存和掙扎着的面影,且一掃頹靡的寫作之風。
“盡我所能地活着”
陳慧“每天的日子”是這樣過的:上午,賣菜五小時,午間美美地睡上一覺。下午,“和狗玩一會兒,立在村路上望望遠山,翻翻自己想看的書,寫點兒隨心所欲的文字……天一黑,關好大門,坐在牀上看會兒書,早早捲進被窩”。太佛繫了,朋友認爲過於“冷清”,她則認爲:“在菜市場擺攤不低級,著書立說不高級,都是爲了有聲有色地活着。”(《她鄉》第232頁)我想她不是沒有負擔、壓力、焦慮,只不過找到了卸下它們的方式。人活得真實就不會爲各種身份綁架,活出了自信,才能“有聲有色”。

《她鄉》,陳 慧 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翻文庫本《瓦爾登湖》(徐遲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7月版),我讀到梭羅的話:“當我享受着四季的友愛時,我相信,任什麼也不能使生活成爲我沉重的負擔。”這也是一種自信,站在背後給他力量的是“四季”,是大自然。一個人只有是獨立的、自信的、精神飽滿的,才能充分地享受“寂寞”,纔不致因此驚惶失措。“大部分時間內,我覺得寂寞是有益於健康的……我愛孤獨。我沒有碰到比寂寞更好的同伴了。”和陳慧的想法差不多,梭羅也認爲:“社交往往廉價。”經常聽到年輕人有“牛馬”的感嘆,牛馬不思考,我們會呀,想過是什麼讓我們變成這樣嗎?也許,現在的狀態就是自我的選擇,或者是自我放棄了選擇。
鄧恩在一首詩中寫道:“我們的心,/除了爲這紛至沓來而輕輕碰杯。”([美]斯蒂芬·鄧恩《紛至沓來》,《怎樣做一個幸福的人》第91頁,唐小兵編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5年12月版)我想探究這“紛至沓來”的是什麼?整日奔忙,我自己有時候偶爾望一下高樓夾縫中的天,此時“我學會了不抱任何希望/盡我所能地活着,幾乎很幸福,/在被掠奪也光芒四射的現在。”(同上,第94頁)或者我們都不安於普通日子,卻又不會保衛普通日子,我們的生命就像骨頭裏的鈣質在那些漫長的日子裏悄然不覺地流失了。

《怎樣做一個幸福的人:鄧恩詩選》,[美]斯蒂芬·鄧恩 著,唐小兵 編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5年出版
“你還是需要不斷閱讀,不斷重讀”
米蘭·昆德拉是一位執着的懷疑論者,但他卻相信文學,提倡“小說的智慧”,不是因爲確定性,而是因爲“不確定性的智慧”:“人們的愚蠢在於爲一切都提供一個答案,小說的智慧在於對一切都提出一個問題……小說家教育讀者把世界當成一個問題來看。這種態度中包含着智慧和寬容。在一個建立於極度神聖的肯定之上的世界裏,小說就無法存在。”(《寫作,多麼古怪的想法!》第296頁)
當今之世,還有多少人相信文學的力量?
2025歲末,我收到不少版權頁上署着“2026年1月出版”的書,這正合辭舊迎新的本義?一本厚厚的《生命的燦爛之書:布魯姆文學之旅》([美]哈羅德·布魯姆著,黃遠帆譯,商務印書館2026年1月版)帶我從文學泥淖中走出來,走進文學的聖殿。這本書與一年多前的《記憶縈迴:布魯姆文學回憶錄》(李小均譯,中信出版社2024年8月版)正好銜接,都是這位傑出學者在生命的最後的告別之書,其中所談都是作者一輩子不斷閱讀的作品。布魯姆毫不懷疑地說:“不管你是誰,哪怕你已進入望九之年,你還是需要不斷閱讀,不斷重讀,除非你是具有原創性的哲人,或者擅長過一種沉思性的生活。”他感恩從荷馬到普魯斯特、喬伊斯這些人的作品得來的“世俗的神恩”,“文學成爲我們生命獲得更多神恩的重要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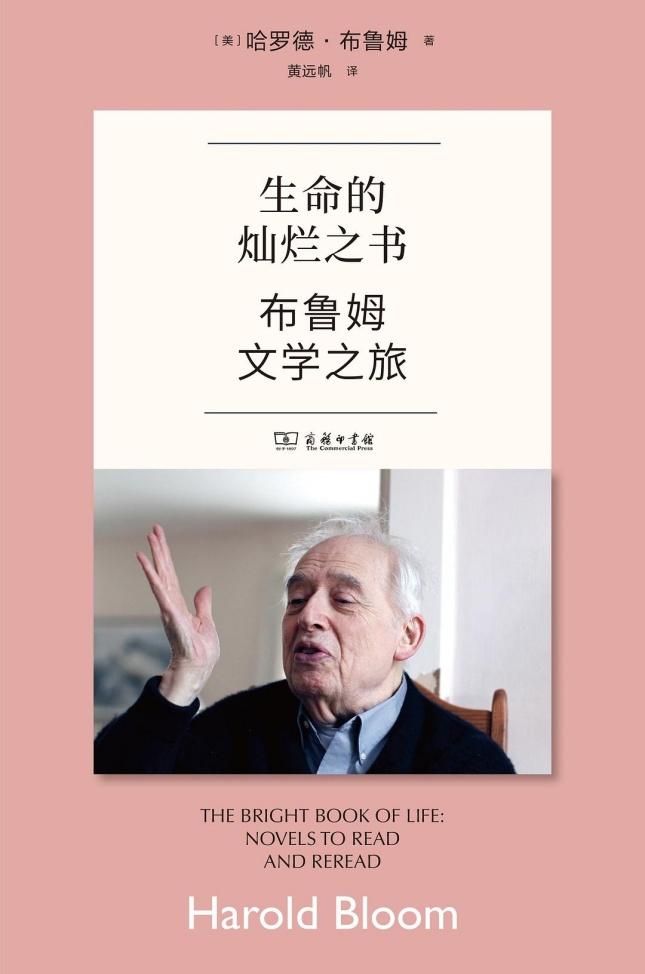
《生命的燦爛之書:布魯姆文學之旅》,[美]哈羅德·布魯姆 著,黃遠帆 譯,商務印書館2026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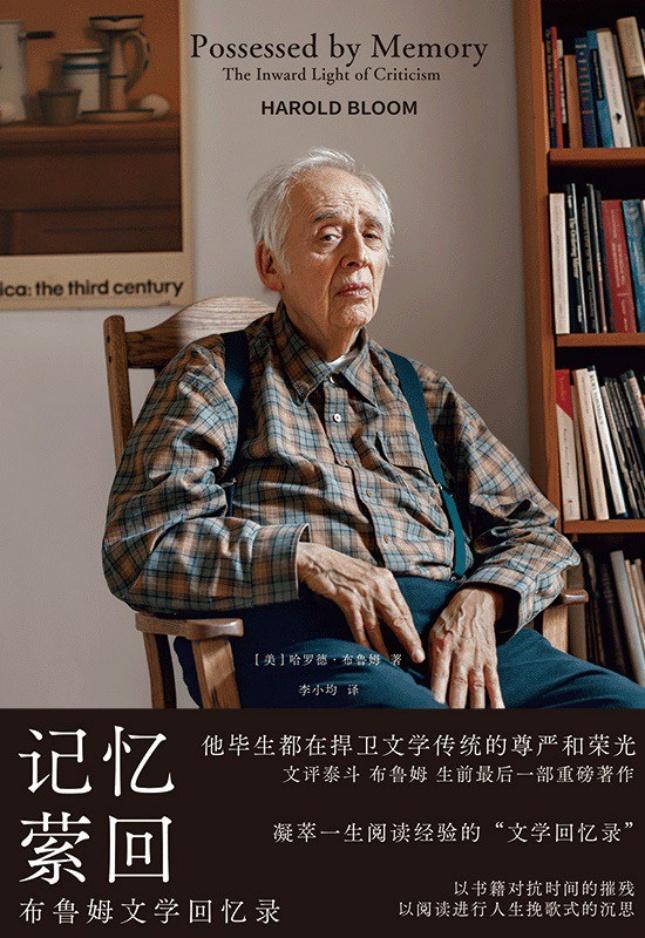
《記憶縈迴:布魯姆文學回憶錄》,[美]哈羅德·布魯姆 著,李小均 譯,中信出版社2024年出版
他得到了什麼,又堅信什麼呢?重讀《包法利夫人》,他看到了“一副人性的面孔”。他也確信:“一個人若無個性,巨量的財富、世俗的成就、當世的名聲,所有這些終將黯淡。”走入21世紀,種種恐怖、戰爭、宗教紛爭爆發時,他“強調生命高於一切”……昆德拉也罷,布魯姆也好,我們不難看出,他們背後都有一個強大的精神傳統,憑依它們,渺小的個人才能挺起腰桿,變得堅強。
在隨遇而安中,等待春風
葛兆光“至今還記得2000年在比利時魯汶的寓所裏,寫完第二卷最後一個字的情形:那是秋冬之際的一個黃昏,關上電腦,站起來看看窗外,滿天颯颯而落的黃葉鋪滿了整個庭院”。“那時候,我剛到知天命之年。沒想到時間過得那麼快,居然二十多年一下子就過去了。”(《〈中國思想史〉修訂本》,商務印書館2025年9月版)二十餘年如一夢,這是陳簡齋的詞句:“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 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閒登小閣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武玉成、顧叢龍注《宋詞三百首》第17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7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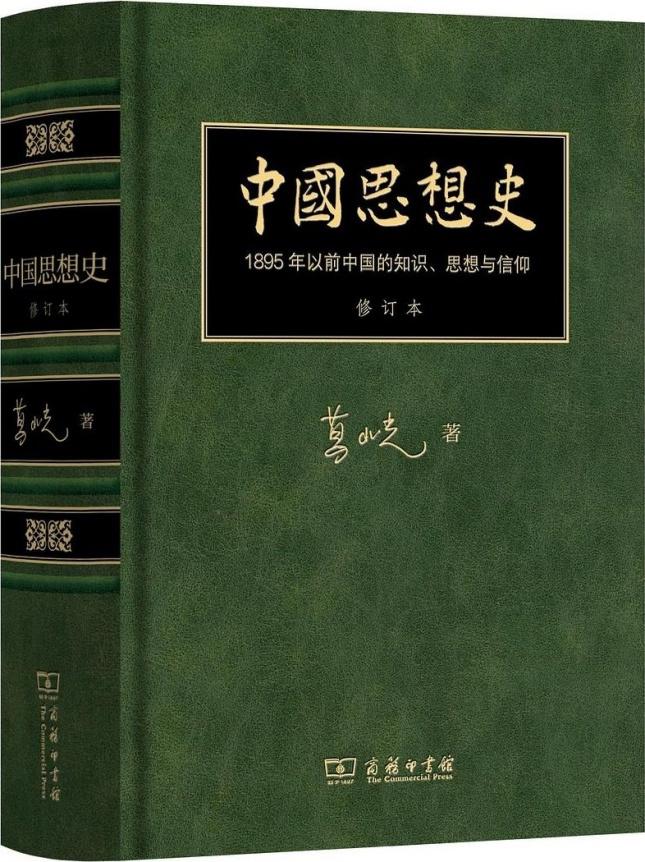
《〈中國思想史〉修訂本》,葛兆光 著,商務印書館2025年出版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歲末之際,讀這樣的話,難免隨之有時光流逝之嘆。哪怕沒有肅殺的寒風,冬天給人的荒涼還是抹不掉的。年少時感受不到生命的沉重,不太喜歡老杜,隨着心上的老繭越長越多,才體會到他道出了很多我們不能言說的苦衷。“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這樣的相逢,是該哭,還是笑呢?生命,比嚴冬還要殘酷。
布魯姆在多病的垂暮之年分外渴望“春草重生”的春天。“我記得,耶路撒冷的春天始於杏花開,但如今,春草重生,卻得不到我生機的回應,因爲我在悲悼正在凋零的同輩。”(《記憶縈迴:布魯姆文學回憶錄》第109頁)傷感,源自消逝的。切莫問“春草重生”的春天究竟還有多遠,沈三白在“客中”哪怕“典衣”也能遊山玩水,買鑼鼓敲出歡快來。樂趣,不是生活的賜予,而是自我製造出來的:“是年大除,雪後極寒,獻歲發春,無賀年之擾,日惟燃紙炮、放紙鳶、扎紙燈以爲樂。”(沈復《浮生六記》第18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7月第2版)像這樣隨遇而安,不卷,值得我們學習。那麼,就讓我們在隨遇而安中,等待春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