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對話馬伯庸:有一種英雄主義來自“平庸的善”



對話人:
馬伯庸(華東師範大學創意寫作駐校作家)
孫 璐(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

在當代中國文學版圖上,馬伯庸是一個現象級的存在。大衆視他爲“腦洞大開”的歷史懸疑小說家,視其作品爲數字邏輯下的智力遊戲。然而,站在文學批評的角度,馬伯庸的獨特性遠不止於此。憑藉曾在跨國企業歷練過的“技術員”思維,他打破了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壁壘,用極具現代體感的話語重構古人的生存困境,開闢了一條通往“新人民史觀”的微觀史學寫作路徑。機緣巧合,我和馬伯庸做了將近一個月的“同學”,於是有了無數次漫無邊際的閒聊和此次“創作技術員”和“批評技術員”對談。剝離環繞在他身上的商業光環、深入解剖他的文本肌理,我不僅驚歎他紮實的考據力和創作嚴謹度,更敬佩他在這個技術加速與文化尋根並存的時代所堅守的文學初心與社會擔當。
——孫璐

孫璐(以下簡稱“孫”):謝謝伯庸同學接受我的專訪。你的10年外企經歷讓我聯想到T.S.艾略特在勞埃德銀行的歲月,還有身居保險公司高管的華萊士·史蒂文斯。但我感覺,雖同爲“職員作家”,你的外企生涯有些特別。它不僅是一種生命經驗,更變成了一種創作方法論,賦予了你一種獨特的文學“技術”。今天我們就以各自從事的“技術員”身份,把你的這些文學“產品”拆解開來看看。
馬伯庸(以下簡稱“馬”):沒問題,很難得能和職業的文學批評者聊聊。
孫:在我們討論“文學性”的時候,時常會提到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傢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概念,即通過革新語言和敘事結構,把熟悉的東西變得陌生,以產生新奇的審美體驗並延長審美過程。在你的作品中,我看到了一種雙向的“陌生化”: 一方面,你用諸如KPI、報銷等高度現代的詞彙描述古代,通過祛魅和世俗化而讓歷史變得“陌生”;另一方面,也更有意思,你其實是把我們現代人深陷其中卻熟視無睹的“系統性壓抑”給“陌生化”了,帶給讀者一種強烈的鏡像感。比如《長安的荔枝》中的李善德,看着他爲了運荔枝累死累活地算路程、搞冷鏈,讀者忍不住猛拍大腿:“這不就是我嗎?”
我的問題是:讓古人患上現代“都市病”的寫法,是你有意設計的一種布萊希特式的間離效果嗎?還是恰恰相反,通過一種看似荒誕的錯位,讓現代讀者帶入劇情,並意識到“系統對具體的人的異化”是一種不變的真相?
馬:我認爲“陌生化”是文學能夠被欣賞的一個必要條件,因爲讀者需要超出尋常經驗。但不是爲了“陌生而陌生”,因爲在我創作邏輯中,陌生化的底層指向的是一種“樸素的真相”。大部分讀者對古代的理解是被戲曲和傳奇濾鏡化了的。在帝王將相、成王敗寇的宏大敘事中,人們代入的是建功立業的英雄。但實際上,古代社會也是一個多層次世界。假如我們不代入將軍,而是代入一個負責軍隊糧草的小官呢?當我把“幾十萬大軍出征背後的後勤庶務”這樣瑣碎工作寫出來,那種崇高的“濾鏡”就褪色了。你看到的是一個不爲人知卻真實具體的小人物,如何因爲一道來自上層的指令而活活累死。我以現代都市職場的視角去理解,不是爲了穿越歷史,而是試圖還原一直被矯飾和忽視的底層歷史。而只要講出了這個“樸素的真相”,就足以給現代讀者帶來一種陌生感產生的衝擊力。
孫:這種“去崇高化”的角色設定,貫穿了你整個的歷史小說創作。從《風起隴西》到《顯微鏡下的大明》再到《長安的荔枝》,你不斷抽離出宏大歷史和英雄敘事,進行一種微觀史學的視角下沉。這是不是你對所謂的“英雄創造歷史”的根本性懷疑?
馬:這其實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小時候我也迷戀宏大敘事,喜歡看《戰爭風雲》、喜歡看英雄改變世界。但慢慢地,我的關注點變了,或者說我從“英雄史觀”轉向了“人民史觀”。幾年前我在博物館看到一塊漢代銘文磚,上面刻着“王復,汝使我作此大壁,徑冤我,人不知也,但摶汝屬。倉天乃死,當搏。”這句話太震撼了!這塊磚斷代在公元170年,距離“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黃巾起義還有14年。也就是說,14年前,憤怒的種子就已經種在了一個無名工匠的心裏。這種憤怒和絕望,纔是歷史真正的推力。英雄只是乘勢而起,而他們身後那些活不下去的小人物,纔是潮流本身。這就是我要寫的歷史,以及歷史背後那些微不足道的動因。
孫:而且你的人物非但不是朝堂之上的帝王、不是揭竿而起的草莽,也不僅僅是一些小人物,而是一羣“技術官僚”,比如《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張小敬、《長安的荔枝》中的李善德。這又讓我不由和西方的歷史小說進行對比,從沃爾特·司各特到希拉里·曼特爾,他們塑造的人物往往揹負着巨大的道德使命,甚至想要拯救世界。而你筆下的人物只想把手頭的活兒幹好,甚至只是幹完,以便保住“狗命”,有點像約翰·勒卡雷筆下那些疲憊的特工。漢娜·阿倫特曾提出“平庸之惡”,你的這些人物是不是可以稱爲一種“平庸之善”?
馬:就像所有的作家寫的都有自己的影子一樣,我想寫的也是我自己,而我本身就是一個平庸的小人物,沒有什麼野心大志,也沒有超脫時代的能力。卡夫卡的作品中,我最喜歡《城堡》,因爲它展示了一種“系統之荒謬”的美感:它沒有善惡,只是按自己的規則運轉。我的主角們就是在這種巨大的“利維坦”縫隙裏騰挪,試圖在規則之間,尋求自己的一點點尊嚴和自主性。在系統的荒謬與高壓下,一個人能保住底線人性和自由意志,就很“英雄”了。這種“平庸”的善,可能比宏大的道德口號更可貴也更動人。有一句話:“英雄就是認清生活的殘酷之後,繼續生活下去。”

孫:提到“系統荒謬之美”,讓我想起了閱讀過程中另外一個強烈感受,那就是你文本中的“精確之美”。這與當下人文學界探討的“新物質主義”思潮有某種契合,即“物”本身具有能動性和敘事的能力。在你的作品中,推動情節發展的不是人的意志,而是“物”的邏輯。比如《顯微鏡下的大明》,絲絹稅的算法決定了縣域的興衰;又如《長安的荔枝》,荔枝的腐爛週期決定了李善德的生死。我很好奇你在文學世界中,爲何對里程、物流、速度如此迷戀與執着?
馬:這也算是我作爲“技術員”作家的一種偏好吧。坦白講,我從弗萊德里克·福賽斯的間諜小說中學到了很多。他會極其耐心地描述槍管有多長,槍裏有多少顆子彈。在《豺狼的日子》中,他不寫那個殺手心理有多變態,而是事無鉅細地寫他怎麼去搞一張假身份證。這個過程看似枯燥,卻充滿了一種驚心動魄的“精確之美”。中國傳統歷史故事偏重寫意和抒情,缺乏技術性的細節描述。比如關於荔枝怎麼運,唐代史料幾乎是空白的,只有一些詩文以藝術的方式提及。這恰恰給了我機會,用一種數據邏輯鏈條去推演歷史,而當這種客觀、冰冷的物性與脆弱、有溫度的人性發生碰撞時,張力就出來了。
孫:但這種寫法是否也存在一種“功能主義”的傲慢?用精密的數學運算去解構“一騎紅塵妃子笑”,是不是在用理性主義的精確去殺死文學中原本可能存在的含混,那種模糊的、非理性的美和詩意?
馬:所以文學不能只有數據,“隔層紗”的美才是文學該有的。我做考據、挖檔案,是爲了給故事打“地基”,比如長安城的坊市結構、下水道走向,那必須是嚴絲合縫的,所以需要百分百精確。但是,如果你把所有東西都寫得如水晶一般完全透明,那就不是小說了。隔層紗,觀衆看到的就是皮影戲,數據和邏輯是幕布後的機器,但觀衆看到的是幕布上的人影,它是鮮活的、動態的,也是模糊的、可以引人遐想的。

孫:這形成了一種精妙的辯證,用精確主義的外部牢籠去反襯深陷內部的活着的人,他的異化或者突圍也因此更戲劇化了。在更廣義層面,還有另一組辯證,即結構與內容的相互成就。現在大家都在談“講好中國故事”和“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我看來,你的寫作提供了一個獨具啓發意義的路徑。在高懸念、強邏輯、快節奏等全球通用的現代“類型敘事”外殼下,實際包裹着中國最傳統的文化內核,比如道家哲學、士大夫精神等等。用“世界的瓶子裝中國的酒”,是否可以看作是讓傳統文化“走出去”的一種策略?
馬:可以這麼說。首先,不要妖魔化“類型敘事”。人類聽故事的本能是相通的,你只有用了講一個好聽故事的通用語法,表現出一種開放與接納,別人才願意聽你講。以《兩京十五日》爲例,那是一個典型的“公路片”或者“逃亡驚悚片”結構,它“走”到海外後反響特別好,還拿了一個頂級大獎。後來我瞭解到,抓住海外讀者的不是故事結構,也不是明朝背景,而是它提供了一個典型中國式的歷史觀,是千里遷徙的緊張感和共情力。所謂“講好中國故事”,本質是要“講好故事”,而這個故事恰好發生在中國。我是中國的作者,思緒流淌的都是中國的哲學與文化,這是無法屏蔽的文化基因,所以我寫的東西,不必刻意爲之,骨子裏一定是中國故事。
孫:這就涉及第二個問題,故事的內容,因爲用“世界的瓶子”,裝的還是“中國的酒”。讀者會被瓶子吸引而買下這瓶酒,但“酒香”纔是留住讀者的關鍵。那麼,講述一箇中國“好故事”,在內容方面你有什麼心得?
馬:沒錯!內核更重要。如今我們講中國故事,不能再停留在功夫、熊貓和京劇變臉上了。準確地說,我們要講的是與時俱進的中國故事,哪怕故事設置在古代,但內容要符合現代人的狀態和人文精神,比如對個體的尊重、對和平的嚮往、對系統性問題的反思等。只有價值觀與現代社會發展接軌,再通過故事這種載體,我們的文化底色才能真正被外界理解和接納。比如,在李善德的困境中,有着全球當代職場人都能體會到的孤獨與堅持;再比如,在《長安十二時辰》中,我把時間的顆粒感磨得非常細,因爲這才符合當代人以分鐘,甚至以秒爲單位來認知和切割時間,“時間焦慮”便很能讓現代讀者,特別是年輕讀者感同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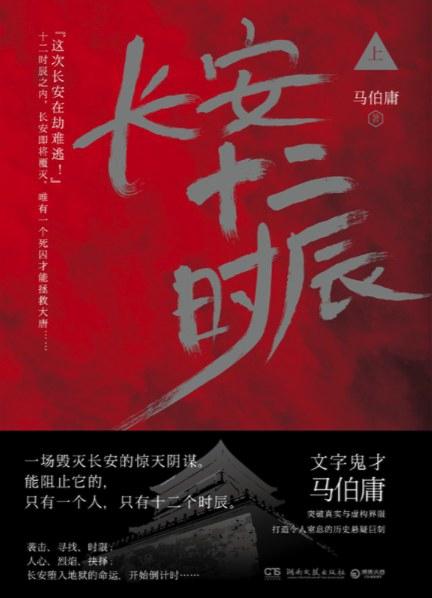
孫:悖論的是,正是“彷彿看到了自己”的當代感反而激起了讀者對古代的興趣,也激活了那些歷久彌新的傳統文化精髓。在你的小說結局中,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無論過程多麼驚心動魄,主角最後往往選擇隱逸,這與西方通常採用的打敗敵人、加冕爲王的征服型結局很不一樣。這可以理解爲是你有意進行的中國化處理嗎?
馬:其實是朋友提醒我才發現,潛意識下我都在寫“事了拂衣去”。無論是范蠡泛舟西湖,還是張小敬歸隱,都是中國人骨子裏的桃花源情結。我們不崇尚像西方那樣征服世界或是永享富貴,我們的終極理想是功成身退,迴歸內心的安寧。“從入世到出世”的轉變,是獨屬中國人的哲學智慧。有一個我特別得意的設計是在《長安十二時辰》中,張小敬跟身邊的跟班描述登上大雁塔後能看到的情景,無論是偷偷喂貓的小和尚、賣餅的老大爺,還是吹笛子的樂工、跳舞的舞姬,那些過着淳樸生活的普通老百姓纔是他忙前忙後想要守護的人。這就是典型的“俠之大者爲國爲民”的中國俠客精神,不少讀者都說這一段讓他們潸然淚下。我覺得這纔是我們要講的中國故事,士大夫的擔當與風骨遠比好萊塢的那套贏家邏輯更具感染力。
孫:特別是在這個高度內卷的時代,恪盡職守後“深藏功與名”,守護內心的一片自留地,何嘗不是對當代人的一種精神撫慰?剛剛你談到描寫大雁塔下百姓的日常,我感受到了強烈的畫面感和鏡頭感。也有評論說,你的小說似乎是爲“攝像機服務的”,具有與生俱來的改編體質,而這一點很符合被短視頻餵養、被倍速慣壞的當下讀者口味。你覺得你的寫作是不是也被影視化和流量媒介給規訓了?還是你有意無意地嘗試了一種“交互式”的小說形態?
馬:畢飛宇在分析海明威的短篇小說《殺手》時曾指出,這顯然是電影出現之後的作品,因爲海明威動用了鏡頭的語言和電影的思維方式。我承認我的作品有着很強的鏡頭感,但我認爲這是文學發展的必然,我們這些伴隨着影視劇長大的寫作者天然會帶有一種鏡頭感。但另一方面,我並不是爲影視改編服務的,因爲小說表達和視聽表達有着截然不同的底層邏輯,前者是非線性的詩化語言,能用多種敘事視角來傳遞信息,而後者需要把所有信息都轉化爲畫面或者聲音才能被觀衆感知到。所以,即使是從技術操作的層面,我也做不到爲改編而寫。多媒體的確爲小說增加了表達的新砝碼,但它不會削弱最本質的文學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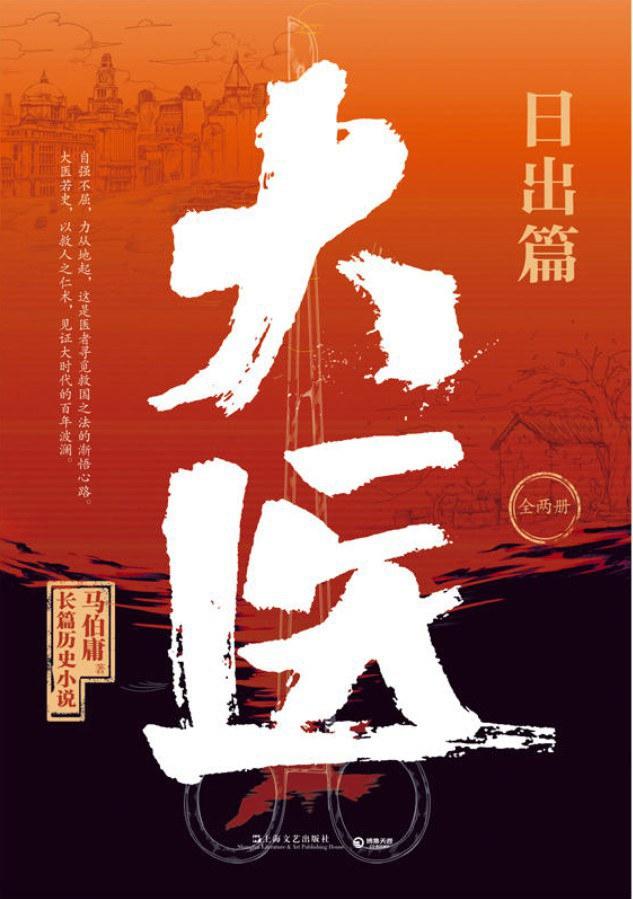
孫:說到這兒,不得不提《大醫》。相信很多讀者跟我有同樣的驚訝,在這本書中,你那種標誌性的、像遊戲通關升級式的緊湊敘事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80萬字的厚重,是對長達一百多年苦難的非常沉重的敘述。這是你走出懸疑和腦洞的舒適區,一次有意識的自我反駁嗎?
馬:應該說,這是我創作方法論的一次覺醒。就是從這本書開始,我意識到“樸素的真相”纔是最重要的。這本書裏的大部分內容來自真實史料,我沒有做任何誇張渲染或者戲劇化的加工,因爲那些紅十字會醫生們切實做過的事情本身就足夠震撼。當我看完當時的記載,我就想挑戰一下,不帶任何雜念地把這個“樸素的真相”用故事表達出來,會有怎樣的效果。
孫:那你有沒有擔心過,習慣了“馬伯庸公式”的讀者會對這種嚴肅、厚重的慢敘事失去耐心?
馬:這涉及另一種意識的覺醒,作爲一個小說家的社會責任的覺醒。當我得知曾有那麼一羣人做了如此偉大的事情、付出瞭如此巨大的犧牲,卻只是在當時報紙上留下了豆腐塊大小的記載時,我覺得我有責任把他們的故事寫下來,讓更多的人知道他們在歷史上的痕跡。我也相信,作家跟讀者之間是有默契的,作者真誠與否,讀者是能感知到的。儘管出版社起初對它的長度有些擔心,但書出了之後實際上反響很好。你會發現,即使是在這樣一個快餐閱讀時代,讀者對長文本依然有需求,他們願意慢下來。這本書算是我的一次漫長的任性吧。

孫:最後,我想問一個關於“侷限”的問題。我知道你搜集史料的能力極強,堪稱“單人數據庫”。但按照人工智能目前的迭代速度,若要比拼數據的挖掘與重組,人類作家是贏不了機器的。當我們正在走進一個“算力霸權”時代,當AI能比我們更快更準地考據,甚至推演歷史的可能性時,你覺得小說家手中最後那張不可替代的底牌是什麼?
馬:我覺得是聯想力。法國作家喬治·佩雷克有部小說《人生拼圖版》,他將一棟10層公寓樓按10×10的國際象棋棋盤進行分割,用99章對應99個格子間,然後分別描述其中的傢俱、擺設、日用品等等。通過這些物品的描寫,逐漸顯現出居住者的種種命運。假設給AI下指令,讓它細緻描寫每個房間的佈局,它能完成得很出色。但它呈現的只是說明書,不是佩雷克在描寫事物的字裏行間構建出的關乎人物命運的故事。因爲AI沒有主體性,也沒有目的性,它無法進行有情感的聯想,也無法用意識建立事物之間非理性的跳躍式連接。至少就目前來看,一個缺少目的性的算法推演,還無法引發讀者心靈共鳴。
孫:那麼,當下的AI發展,給你帶來了某種焦慮或者危機感嗎?
馬:當然有焦慮,但這種擔憂更多的是對下一代的寫作者。要知道,一個作家的成長往往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試錯過程,可能要花上幾年,甚至十幾年去寫爛稿子、去體驗無人問津的孤獨,在不斷的挫折和完善中形成正反饋,然後越來越好。但現在的AI不會給你這個時間,它瞬間生成的一篇合格的小說,會扼殺許多寫作愛好者初期的努力,挫折感會殺死大部分寫作熱情。AI帶來了一種人才斷代的危機,但我想說的是,要保住自己表達的熱情,因爲那種源自生命本能的、非功利的表達慾望,是任何算力都無法剝奪的,也是我們最後的防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