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諾獎得主拉斯洛獲獎演講:人類——這驚人的生物——你是誰?




12月6日—12日,今年諾獎在斯德哥爾摩和奧斯陸開啓爲期一週的諾獎周活動。活動期間,獲獎者將爲諾貝爾獎博物館捐贈一件有特殊意義的物件,與讀者展開多場活動交流,發表獲獎演說,並參加頒獎典禮。
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因“震撼人心、富有遠見的創作,在災難與恐懼的時代,重申了藝術的力量”(授獎詞)獲得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在他獲獎後的兩個月裏,中文出版領域也新增了他的兩部作品,短篇小說集《世界在前進》(99讀書人)、長篇小說《溫克海姆男爵返鄉》(譯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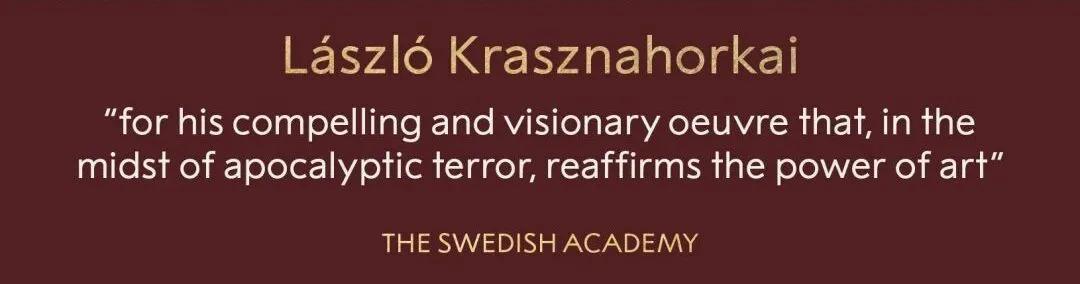
當地時間12月7日晚,拉斯洛在斯德哥爾摩瑞典學院作了題爲《人類——這驚人的生物——你是誰?》(Human being—astonishing creature—who are you?)的獲獎演講。演講中,拉斯洛穿越回自己的寫作房間,講述對科技時代和普通人命運的思考,又藉由一個流浪漢被追逐的故事,引申出了對人類尊嚴、對反抗、對希望的全部想法。
演講現場同時視頻直播,全文已在諾獎官網發佈(對報紙媒體開放發表許可©THE NOBEL FOUNDATION 2025),以下爲完整演講內容,由本文編輯鄭周明編譯。
人類——這驚人的生物——你是誰?
在獲得2025年諾貝爾文學獎時,我原本想與諸位談談“希望”。但由於我體內所有的“希望儲備”已被徹底耗盡,我現在只能先來談談“天使”。
我在房間裏來回踱步,一邊走,一邊想着天使。即使現在,我仍在走動——不要相信你們自己的眼睛:你們以爲我站在這裏對着麥克風講話,但我不是,我實際上正在不停地踱步,從一個角落走到另一個角落,再從原點折回去,如此循環往復、來來回回。是的,我在想着天使。而我現在就能告訴你們:這些是一種全新的天使,他們沒有翅膀。
假設一下,如果他們背後真長着兩隻翅膀——而且若那兩隻巨大的翅膀沉沉地從外袍後伸展開來——那天上的裁縫在替他們做衣服時究竟要如何設計?又是什麼不可知的神祕技藝在那間裁縫作坊裏飄蕩?翅膀當然是在身體之外,是那種“無形的身體”之外,那麼他們要把那翅膀安放在哪裏?在那件纏繞着他們同時又覆蓋着翅膀的斗篷之外嗎?或者反過來說,如果翅膀不外露,那麼這件斗篷又是如何把他們的身體連同翅膀一起包覆住的?
哎,可憐的波提切利、可憐的達·芬奇、可憐的米開朗琪羅、喬託、安傑利科修士!但這如今都不重要了,因爲這些問題已隨着舊天使一起蒸發殆盡。我談論的是新的天使——我開始在自己的小房間裏踱步,你們現在才“看見”我站在麥克風前,作爲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當我開始嘗試寫作,在僅有四米寬的塔樓小室裏擺出沉思姿態時,我的腦中已經出現了模糊的輪廓。這個塔樓房間並不浪漫,不是什麼象牙塔,它是用最廉價的挪威雲杉木板搭成的,位於一座單層木屋的右上角。之所以變成“塔樓”,只是因爲我的土地處在山坡上,這間加建的小屋房間便像塔一樣高高立起。原本我因書本不斷逼近地盤,不得不在底層加建一間房,而山坡的傾斜使這擴建部分自然升高,上層壓在下層之上,因此它成了塔樓。

拉斯洛位於郊區的家
我現在站在你們面前——實際上是在塔樓小室裏踱步——並不真的想談論天使,儘管那些圖像畫面仍活在我們心裏,由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的天才們賜予我們。儘管那些溫柔、崇高、令人動容的舊天使仍能觸動我們無法相信的內心,但我不是想談論舊天使。
如今只有新的天使。
新天使沒有翅膀,也沒有那甜蜜纏繞的斗篷。他們穿着普通的街頭衣服在人羣中走來走去。我們不知道他們有多少人,但據某種模糊的暗示,他們的數量與舊天使一樣多。
他們像舊天使一樣,在我們生命的關鍵時刻“突然出現”。如果他們願意被認出,其實很容易。他們彷彿以另一種節奏、另一種旋律踏入我們的生命,與我們這些在塵土中掙扎、踉蹌前行的人完全不同。
更重要的是:我們甚至無法確定他們是否來自“上天”。也許如今根本再沒有“上天”這個地方——它可能連同舊天使一起退出了宇宙,把位置讓給那永恆的“某處”,在那裏只有“埃隆·馬斯克們”創造出的瘋狂世界來組織新的空間與時間。
此時你們看到的,是一個老人,講着你們聽不懂的語言,站在諾貝爾文學獎的講臺前。但實際上,他在一間無法被暖氣加熱的塔樓房間裏,在挪威雲杉木板之間踱步——也就是我本人。我此刻突然加快腳步,因爲我意識到,要講述這些新天使,我的步伐必須與思緒的速度一致。
就在我加快腳步的這一瞬間,我猛然意識到:這些新天使不僅沒有翅膀,他們也沒有信息。他們來到我們身邊,只穿着街頭服裝,如若他們願意,可以完全不被認出來。但要是他們願意被認出來,他們會走向某一個人,然後,突然,一瞬間,我們眼前的霧障被揭落,內心的塵土也隨之脫落。
我們震驚地冒出一個念頭:天哪,是天使。
然而……他們什麼都不會給我們。他們身邊沒有飄着的字句,沒有光,也沒有低語進耳朵裏的一句話。他們一句話也不說,彷彿已變得啞然。他們只是站在那裏,看着我們,尋求我們的目光、懇求我們回望他們。
因爲他們要我們交給他們訊息。但遺憾的是,我們沒有任何訊息可給。過去,還有問題與回答,而現在既無問題,也無回答。
那麼,這算什麼遭遇?他們站在那裏,我們也站在那裏;他們無法從這沉默中得到什麼,而我們更無法理解其意義。啞者對聾者,聾者對啞者——如何能有對話、理解?
於是,此刻——允許我把自己也算進去——所有孤獨、疲憊、悲傷而敏感的人,會突然意識到:這些新的天使,其實是“犧牲品”。

我迅速掏出“聽診器”——我總是隨身攜帶——在塔室裏踱着步,輕輕把聽診器的膜片貼到你們每一個人的胸口。立刻,我聽見命運的聲音——你們的命運。我跨入某個命運,一種跳動令此刻,也令下一刻驟然改變,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時刻轟然降臨——震驚與坍塌的時刻。
因爲我的“聽診器”裏聽出了關於這些新天使的可怕故事:他們是“犧牲品”,不是爲我們,而是因爲我們。
我們知道世界上有戰爭,自然中的戰爭、社會中的戰爭。戰爭不僅以武器、酷刑、毀滅的方式出現,但在另一端,只需一個惡言、一句不公,一次不體面、輕率、侮辱性的舉動,一次對身體與靈魂的傷害。
因爲他們在誕生之初並不是爲了承受這些,他們在殘酷、卑鄙、玩世不恭面前毫無防禦。他們的純潔與無害無法抵擋人類的惡意。只要一次惡言,就足以讓他們永遠受傷。而我即便說上一萬句,也挽救不了。
因爲那些傷害根本不可能被修復。
好了,“天使”談論得已經夠多了。讓我們改談人類的尊嚴吧。
人類——這驚人的生物——你是誰?
你發明了車輪,發明了火,意識到合作是生存唯一的途徑;你獲得了驚人的智力,你的大腦龐大、溝回縱橫,複雜無比,憑藉它,你掌握了對這個世界的支配力,也因此得出許多後來被證明不真實但推動你進化的認識。
你發展、擴張、建立部落、社會、文明。你成功避免滅絕——雖然你也差點滅絕過。你站起來成爲智人,製作石器並加以使用,發現火。後來因爲一個細微之處——你的喉嚨不像黑猩猩那樣貼合——你得以產生語言,與大腦的語言中樞一同發展。

其後,你發明了文字,你掌握了哲學思考,把經驗與宗教分開;你發明了時間;你發明了舟車,跨越地球的未知之地,掠奪能掠奪的一切;你意識到力量集中之價值;你繪出那些被認爲無法觸達的行星;不再把太陽當作神,把星辰視爲命運;你發明並重新塑造了性別角色;你很晚但總算發現了愛情;你發明了情感、共情、知識習得的層級;最後,你進入太空,拋下鳥類,飛向月球,在那裏邁出第一步;你發明了能將地球炸燬數次的武器;你發明了科學,其靈活性使得“明天”不斷推翻今天僅能想象之物;你創造了藝術,從洞穴壁畫到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從原始節奏的黑暗魔法到巴赫。
最終,你隨着“歷史進步”,突然完全開始相信一無所有;你藉由自己發明的設備摧毀了想象力,你只剩短期記憶;你捨棄了對知識、美與道德良善這一高貴而共同的品質。
別動,你還要去火星嗎?不,別動,那裏的泥沼會把你吞下。
但你的進化之路,是如此壯麗、令人屏息。然而,很不幸,它無法再度重複。
說了夠多關於人類的尊嚴了。讓我們改說“反抗”吧。
我曾經試圖在我的書《世界在前進》裏觸及這一點,但因爲我對自己寫得仍然不滿意,我想再試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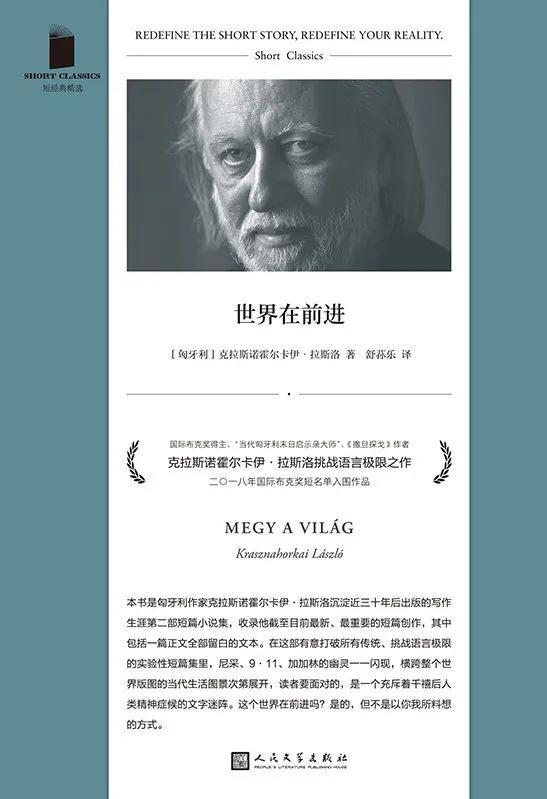
上世紀90年代初,一個潮溼、悶熱的下午,我在柏林,正在地鐵下層的某個站臺等車。和所有的地鐵站臺一樣,站臺在列車正確方向的起點處裝有一個巨大的、帶信號燈的鏡子,部分用於幫助司機觀察整列車廂,部分用於精確指示列車到站時車頭應該停在的那一釐米不差的位置,以便乘客上下車。鏡子當然是給司機看的,而紅燈則標示列車必須停止的垂直點,當乘客上下完之後,這些燈會變成綠色,列車即可繼續穿過隧道。
除此之外,鏡子下方到隧道入口之間的地面上畫着醒目的粗黃線,還有警示標牌提醒必須避免事故、遵守規則。黃線的意義是:即使站臺在黃線後還延伸了幾米,旅行者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跨越這條線。黃線與隧道入口之間是一片嚴禁進入的區域,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踏入這片禁區。
我正等着從克羅伊茨貝格方向來的列車,突然我注意到:禁區裏有人。
那是一個流浪漢。他的背因爲疼痛而彎曲,臉也因痛苦略微側向人羣,像是在尋求同情似的,他正試圖往鐵軌上方的步道小便。從他那痛苦扭曲的樣子可以看出,這個排尿對他來說極其折磨,他只能一滴一滴地排出。
當我完全意識到發生了什麼時,周圍的人也都注意到了,一件極不尋常的事情在我們眼前擾亂了這個下午。忽然間,幾乎是觸手可及的、普遍一致的意見在空氣中成形:這是醜聞,必須立即結束。這名流浪漢必須離開,黃線所象徵的規則必須恢復其效力。
本來,如果這流浪漢能順利排完,重新回到我們之間,然後慢慢走上樓梯離開,也許不會有問題。但他沒完,大概也無法完。而事情變得更加麻煩,是因爲在對面站臺突然出現了一名警察。他從那邊高聲喊叫,和流浪漢幾乎是面對面,語氣堅決地命令他立即停止。
這些車站爲了安全是這樣建造的:相對方向行駛的列車的兩條鐵軌之間有一個大概十米寬、近一米深的軌道。所以如果一位乘客想換方向,是絕不可能直接跳下軌道、走十米到對面站臺的,他必須走到站臺盡頭,上樓梯、穿過上層走廊,再下來。直接穿越軌道不僅“更加禁止”,而且是致命的。我如此詳細地描述,是因爲那名憤怒的警察——保持着某種尊嚴,但也利用着他的權力與善意——也必須按照同樣路線:跑到樓梯,上去,跨過走廊,再下來,才能到我們這一側。
在他試圖到達樓梯頂端之前,他已經喊了好幾聲,但流浪漢完全不理會他,仍然側着臉朝向我們,用無法改變的痛苦目光看着我們,同時尿滴繼續落在鐵軌上,這對規則、秩序、法律和常識來說,真是前所未有的侮辱。警察甚至可以說:這人“裝聾”,對他而言更是痛苦。
當然,流浪漢也把警察算在了心裏。他知道憑自己的痛苦和虛弱,絕不可能在警察趕到之前結束排尿並逃走。因此,當他注意到警察在對面站臺加快腳步,甚至開始奔跑,想趕到上方的走廊,再下來抓住他時,流浪漢用巨大的困難停止了排尿,朝我們的方向逃去,試圖儘快到達最近的樓梯並消失。
這是恐怖的追逐。
我們站在站臺上的每一個人都完全安靜了,因爲一眼就能看出:這逃跑不會有任何好結果。流浪漢的身體開始劇烈顫抖。他的腿和指揮雙腿的大腦似乎都不再正常運作。他看着那邊的警察每一米都艱難地推進着,而他自己這邊,卻只能靠可怕的努力,一釐米一釐米地移動,雙臂亂揮。警察看着兩人之間那十米距離,那十米對他來說是折磨、是不公平的障礙。而對流浪漢來說,那十米卻是延遲——一種毫無意義但真實存在的延遲,也許能給他帶來一絲逃脫控訴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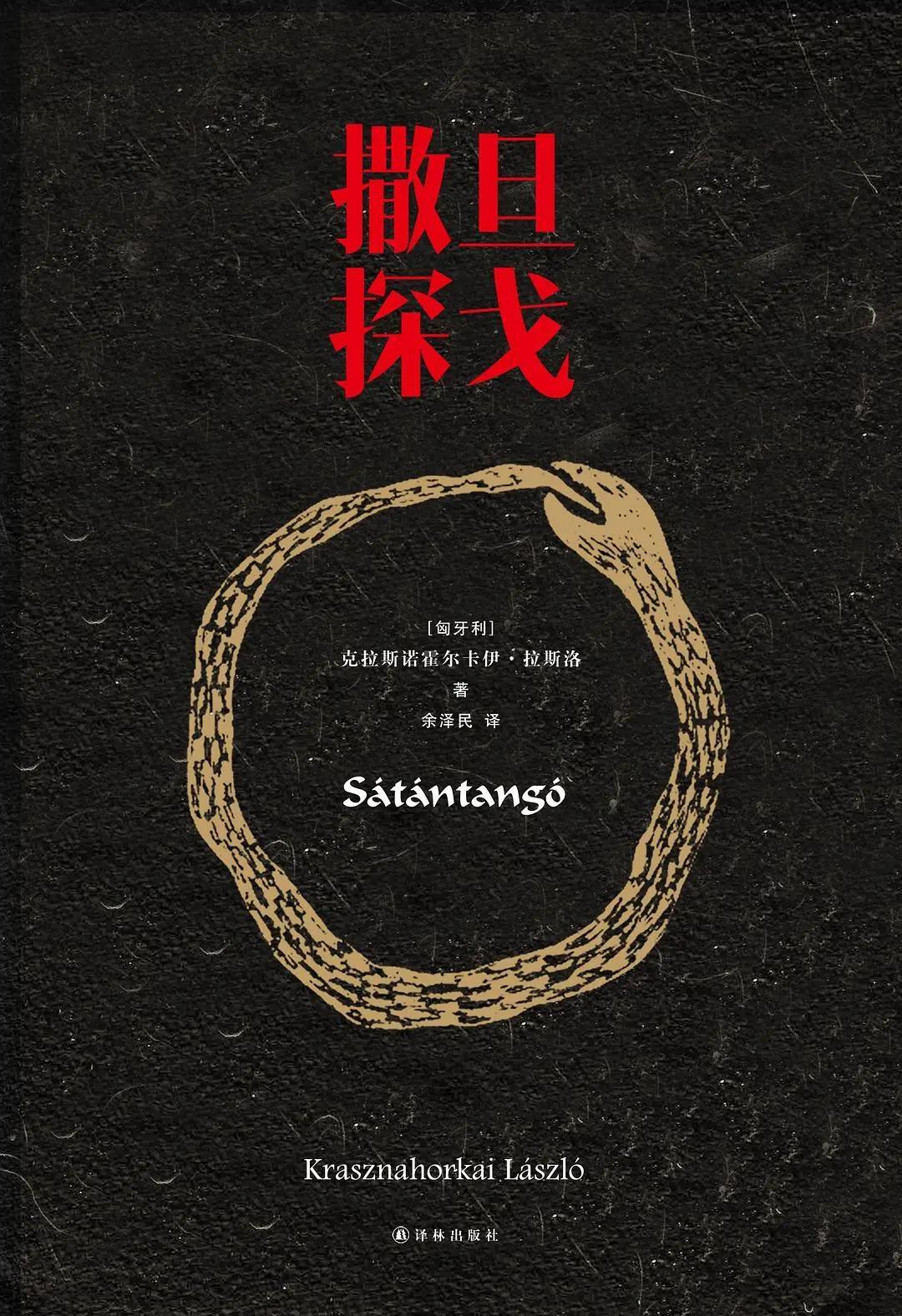
從警察的角度,他象徵着法律,象徵着所有人公認的善與正義;而對面那拒絕理性、違背規則的人,則象徵着惡。是的,在這一刻,警察代表着“必然的善”,但也在這一刻,他束手無策。
就在我羞愧地看着這場“米與釐米”的不人道競賽時,我忽然精神高度集中,而這種高度集中讓那個瞬間凝固了。停在他們互相注意到對方的那一刻:善良的警察看到惡的流浪漢正在禁區裏小便;而不幸的流浪漢也看到警察看到了他。
他們之間隔着十米。
警察抓緊了警棍,在奔跑的前一刻僵住了,他的肌肉繃緊,準備跳躍。那一瞬間,一個念頭閃過:如果他直接跳過這十米會怎樣?
而另一邊,受到十米“保護”的流浪漢則雙倍無助地揮動着手臂、劇烈顫抖。
就在這裏,我的注意力停止了,直到今天仍停在那裏。我腦中始終停留着那個畫面:憤怒的警察揮着警棍開始追趕流浪漢,那一刻,理所當然的“好人”奔向了衣衫襤褸的“惡人”,而且不僅僅是奔向惡,更是奔向惡本身。
在這一凍結的圖景裏,我直到今天仍能看到:遠處站臺上那個奔跑的人,每一步跨出一米;而在我們這一邊,那個有罪的、呻吟、顫抖、無力、幾乎因痛苦而癱瘓的人,每一步只能是一釐米。
是的,在這場競賽裏,善良——因爲那十米的存在——永遠追不上惡。
因爲十米永遠無法跨越。即便警察最終在列車進站時抓住他,在我眼中,那十米依然是永恆的、不可逾越的。我的注意力只感受到:善永遠追不上揮動着的惡。善與惡之間,沒有希望,一點也沒有。
列車帶着我駛離,而我腦中不斷迴盪着那顫抖與揮動的身影。突然,一個閃電般的問題穿過我的腦海:這個流浪漢——以及所有被排斥的人——他們究竟什麼時候纔會反抗?然後我揮去這個念頭,因爲我告訴自己:不,我想到的反抗是不同的。因爲那種反抗,是針對整個整體的反抗。
女士們先生們,每一次反抗都是針對“整體”的。而現在,當我站在你們面前,當我在家鄉那座塔樓裏的腳步變得緩慢時,那趟地鐵旅程又一次在我心中閃現。一站接一站亮起,我在隧道里穿行、卻從未下車。從那天起我就一直乘坐着那列地鐵,因爲沒有哪一站是我能下車的。
我只能看着車站一一滑過,我感覺自己已經思考過一切,也說盡了我對反抗、對人類尊嚴、對天使,甚至對於希望的全部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