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文學需向煙火氣與人情味迴歸



“縣城是觀察中國式現代化生動實踐的窗口,也是具有煙火氣、人情味,蘊藏無數故事、充滿生命張力的素材富礦和靈感泉源。”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邱華棟近期所言,無疑是對“縣城”與“文學”之間關係的凝練描述,同時也在向衆多寫作者傳遞富於啓示性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對於“縣城”與“文學”的觀察與想象,對於“縣城文學”與“文學縣城”的辨析與創造,首先需要回到“‘縣’場”,回到“‘縣’場”本應具有的“煙火氣”與“人情味”。
頗具意味的是,爲何要關注“‘縣’場”,以及怎樣回到“‘縣’場”的“人間煙火”,也間接引申出了晚近國內文學創作有關“縣城”與“縣城青年”的一個顯豁問題,即:現實層面與文學層面的“縣城”“縣城青年”存在明顯的結構錯位。包括當前因一類陳舊的、陰鬱的、黯淡的美學風格而在網絡社交平臺受到熱捧、模仿的“縣城文學”風,一方面這類潮流呼應了新世紀至今縣城文學書寫的突出特徵,但此類特徵呼應又是對現實社會正形成新變的“縣城”與“縣城青年”的背離。
而如果將視角轉至改革開放初期,其時一批聚焦縣城青年而書寫的文學作品恰恰首先立足於對同時期縣城面貌與青年狀態進行追蹤定位。1982年,《收穫》雜誌第3期刊發了後來爲路遙贏得廣泛聲譽的小說《人生》。《人生》及之後由導演吳天明執導的同名電影的熱映,某種程度而言也將生機勃勃、富於野心而又頗具才幹的高加林引申爲上世紀80年代縣城青年羣體的顯豁象徵。其實,那又何嘗不是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語境下縣城的氣質描摹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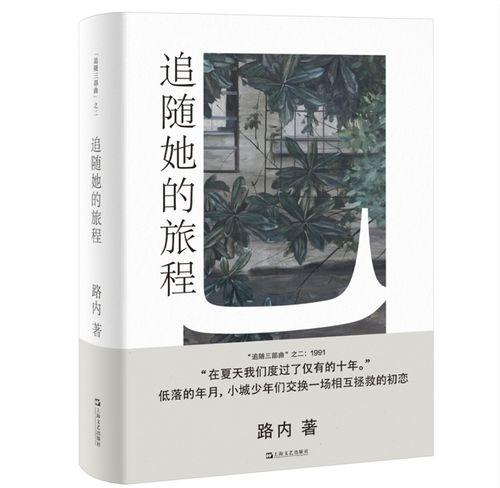
饒有意味的是,2008年,《收穫》春夏季長篇小說專號重刊了路遙的《人生》,同期還推出了路內的《追隨她的旅程》。由《人生》到《追隨她的旅程》,事實上也構成了改革開放以來縣城青年書寫從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的次第展開的邏輯框架。路內的《追隨她的旅程》從1991年“一個衰老的縣級市”戴城說起,18歲的技校青年路小路騎着自行車穿梭於寂寞與喧囂並存的戴城,他肆無忌憚卻又惶惑徘徊的縣城體驗與青春記憶也暗合當代中國社會的特殊轉型期。小說開篇第一句話是耐人尋味的,卻又是對上世紀90年代一類縣城青年生存境遇的揭櫫:“這是一個關於尋找的故事。”對於90年代小說內外的縣城青年而言,他們都似乎在尋找着什麼。
“尋找”的背面也可能預示着“出走”。三年後的2011年,阿乙在《人民文學》第11期“非虛構小說”欄目發表了中篇小說《模範青年》。這是發生在世紀之交的故事:小說敘述者“我”與警校同學周琪源在畢業後被分配到同一個縣城公安局工作,“我”不甘於接受一眼望到頭的乏味生活,選擇離開縣城外出闖世界,周琪源則囿於縣城鬱鬱而終。《模範青年》通過將“出走”的“我”與“留下”的周琪源作爲一組質地迥異的縣城青年鏡像,進而有意爲20世紀中國文學相關題材創作作出擲地有聲的“總結”。需要指出,阿乙的《模範青年》以“總結”的形式也在試圖昭示改革開放以來縣城青年的“標準”問題。而小說的題中之義,恰恰是世紀之交中國文學當中的縣城青年如何逸出片面的“標準”,尋求“異路”“新路”,在“模範”之外確認另一種“新人”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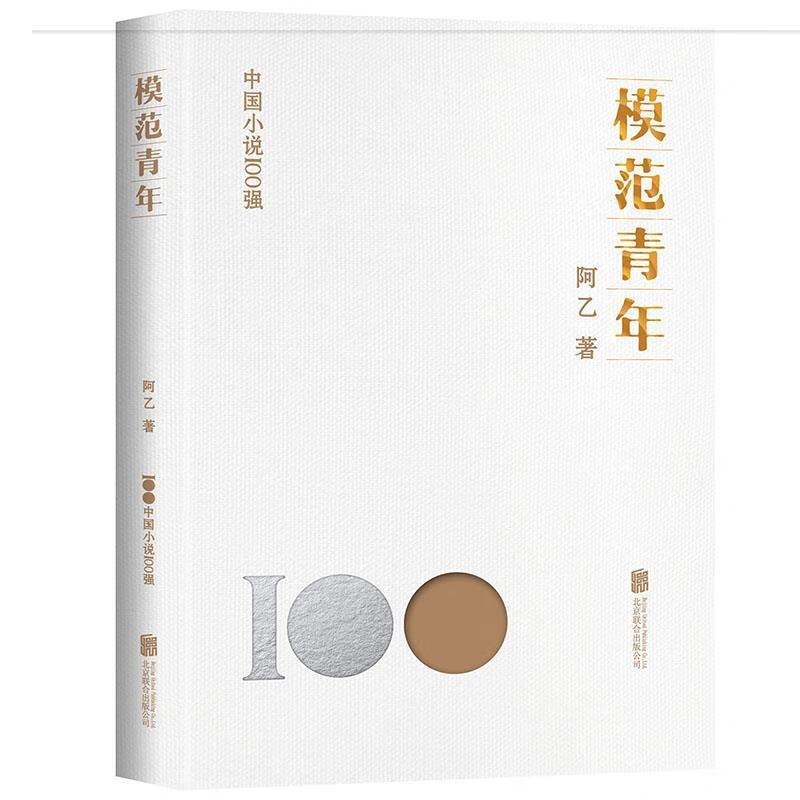
但理應引起重視的問題是,在《模範青年》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諸多文學創作所涉的縣城青年反而暴露出趨於概念化、同質化的形象特質與行爲表現,或者說,“縣城青年”內嵌的現實含義與時代趨勢,被一類滯後卻具普遍性的“標準”所覆蓋。而讀者也難以從被“標準”捆綁的文本里捕捉到如高加林、路小路那樣明晰的青年面目。
這其中一個不應忽視的原因,就在於那些“靈”與“肉”皆從縣城“撤離”的寫作者一旦進入縣城青年的世界,他們的敘述往往會失焦,往往會無所適從,往往會顧左右而言他,因爲種種這些已然被排除在他們逼仄的經驗版圖外。故而他們只能讓縣城青年出走,但出走並非意在開闢“新路”、鑄造“新人”,而是經由讓縣城青年被壓縮爲邊緣化的空洞符號,從而繞開對書寫對象深層次的體察與追問。
而隨着縣城青年從“出走”到“被出走”,相對應的,改革開放初期作爲城市與鄉村重要紐帶的縣城,在當下所見的一系列文學作品裏同樣喪失了具有區分度的空間感,更趨向於一類名曰“縣城”實則不知其所以然的“萬能背景板”。
因之,如果說上世紀90年代至新世紀初期“青年在縣城”的顯豁的文學主題是“出走”,新時代語境下我們則要觀照縣城青年如何“迴歸”縣城。
所謂“迴歸”,不僅指向文學作品內青年人物的精神結構與行爲方式,也關涉寫作者在視角、趣味、立場等方面的調整。對於這個時代有志於書寫“縣城”與“縣城青年”的寫作者來講,他們需要回到“此刻”“此地”的縣城場域,讓自我融入到縣城與縣城青年的煙火氣與人情味中去,充分感知生活在縣城的青年羣體真實豐盈的現實狀態與情感波動。

以顏歌的《平樂縣誌》與張楚的《雲落》爲例,這兩部近期出版的長篇小說不約而同地錨定於縣城的日常與細部,他們所聚焦的是作爲現實的人與動態的人的縣城青年,這也令小說中縣城青年的生活史、情感史與成長史皆有了紮實的落位與多元的指向。而《平樂縣誌》《雲落》等作品也在呈示敏銳的寫作者如何用可靠的行動力代替縹緲的想象,用真切的在場感代替滯後的“標準”。
事實上,只有首先向內抵達縣城與縣城青年的內核深處,方能對這個宏闊時代背景下“如何寫縣城”“如何寫縣城青年”形成觀念創新與空間再造,也方能令縣城與縣城青年有真正“走出去”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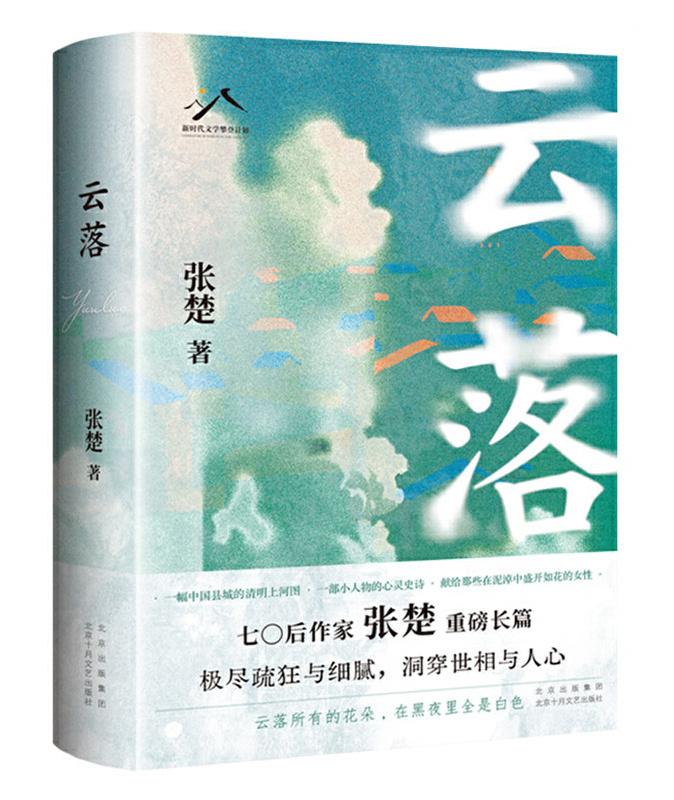
除此之外,對於縣城與縣城青年的把握也應返至這類題材創作尚未得到充分梳理的精神源頭。包括我們有必要結合精神源頭的內部與外部,去思考曾經的縣城與縣城青年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學的延長線上是如何存在的,又是怎樣“被剩餘”的,並通過對“存在”與“被剩餘”的重新確認獲得寫作的動力方向。南京師範大學何平教授在其主持的《花城》雜誌“花城關注”欄目“在縣城”專題裏談到:“應該一直到新世紀前後,縣城一直爲中國文學輸送着文學青年。他們裏面八九十年代開始寫作的,大多數還剩餘在縣城。這是那個時代文學繁榮的基座,即使他們不能成爲一個優秀的寫作者,至少是一個優秀的讀者,他們是縣城的小職員、教師、工人,等等。”由此而論,在文學創作維度重提縣城與縣城青年,其意義就不單是區分與確認某種特定的敘事空間與敘事對象,同時是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學“來處”的重新釐定。而怎樣迴歸、認領縣城與縣城青年的廣闊性與複雜性,也構成了新時代中國文學從業者亟待釐清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