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身記:時尚與醫療體系中的身體文化



在虛擬世界愈發高歌猛進、數字化幾乎入侵一切領域的今天,“身體”這個詞卻再次站在聚光燈下,成爲人們討論的熱點。即使是在最熱門的人工智能領域,具身性(Embodiment)也是其探索重點之一。英偉達公司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黃仁勳不斷在公衆面前強調,人工智能的未來趨勢將會是具身智能。故而,審視、認知我們的身體,以及附着於身體之上的文化,是極其必要的。
解除障眼裝備——服飾
想要認識身體,首先需要解除的第一道屏障自然是服飾。穿什麼以及怎麼穿,不僅僅是個人審美表達,更是社會觀念的投影。人在選擇衣服時並非選擇衣服本身,而是在選擇衣服背後的象徵含義。韋羅妮克·海蘭《穿衣自由?時尚背後的文化與抗爭》(下文簡稱《穿衣自由》)一書就提到了“具衣認知”(enclothed cognition)的概念:讓學生穿上白色長外套,並告訴他們這是醫生的白大褂,結果學生在需要專注力的任務中表現顯著提升。同樣的白外套,被描述爲畫家的工作服時,研究人員並未觀察到類似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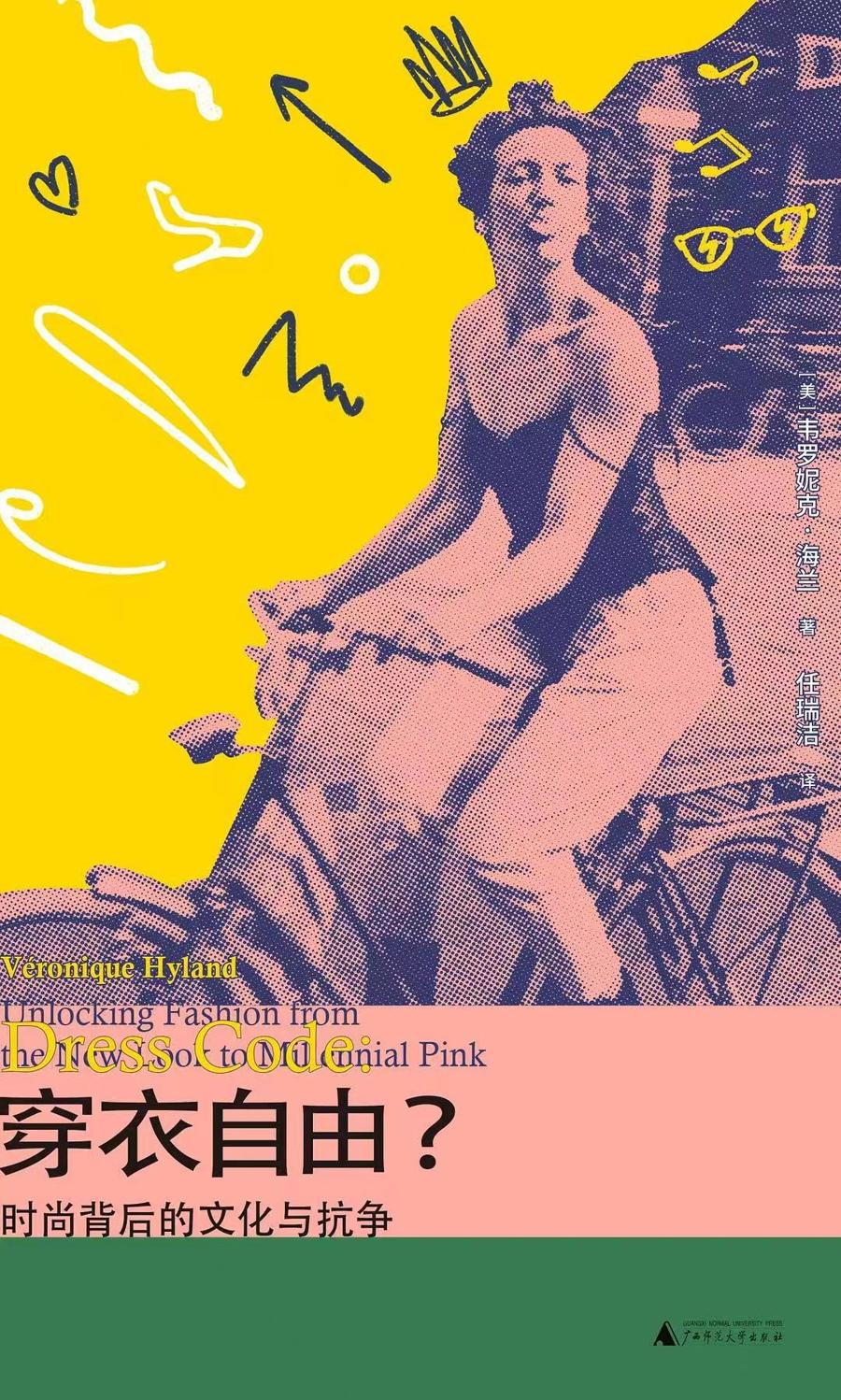
《穿衣自由?時尚背後的文化與抗爭》,[美]韋羅妮克·海蘭 著,任瑞潔 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5年出版
最具社會屬性的服飾莫過於制服。正如韋羅妮克所言:“機構常通過着裝要求來強化自身價值觀。控制你的穿着意味着某種程度的行爲約束,讓你服從於組織。這種約束從學生時代就已開始。”所以某種意義而言,並不是身體在穿制服,而是制服在“穿”身體。
穿制服有時也意味着“穿”權力。比如警察、軍隊等機構的制服,都有比較鮮明的等級符號。有時甚至不用十分高階,僅僅是穿着制服,就可以獲得更多權力。《穿衣自由》提到:“1947年的一項研究中,實驗者在街頭請求路人完成一些簡單任務,比如撿起地上的物品。結果顯示,當實驗者身穿警服時,路人的服從率遠高於穿着送奶工制服或日常服裝的情況。”
當然,制服文化並非一成不變。以我國爲例,一向被認爲擁有深厚且典型“展現美麗”制服文化的航空界,有關着裝的要求逐漸向着更安全、舒適和專業的方向靠攏。2021年,《民航客艙乘務員職業形象規範》頒佈,規定着裝應該以方便乘務員工作爲主,最大限度降低不安全因素。自2024年以來,多家航司推行便利安全的平底鞋,代替過去的“標配”高跟鞋。在美國,科技行業巨頭比起西裝革履的工作制服,更喜歡休閒舒適的穿搭,用來彰顯企業的創新和冒險精神。不過韋羅妮克提醒讀者注意:“大家都穿着帽衫,職場不會因此奇蹟般地變成公平競爭的場所。馬克·扎克伯格最愛的T恤是普通員工買不起的意大利高級貨。”
對普通職工來說,制服體系的鬆動不代表着裝權力的增加。下班之後,穿衣就會更自由嗎?韋羅妮克認爲,看似休閒鬆弛的“法式風格”實際上只是美國人一廂情願的集體想象。這點國內亦有相似情況,互聯網上的“法式風格”及其衍生出來的“知識分子穿搭”“老錢風”“南法度假風”無一不是營銷符號,人們希望通過服裝來“形塑”身體與社會地位,結果反被服裝控制,變得失去個性。服飾風格越多元,人們穿得越相似。
最弔詭的是,當人們已然接受了服飾的秩序——畢竟連“不時尚”現在都是時尚的一種分類,時尚界又提出了新的口號:“身材是最好的衣服”。《穿衣自由》最後一章得出的結論是:“隨着服裝變得更自由,對身體的限制卻悄然增加……我們看似擁有更多自由,但實際只是將審美標準從時尚界轉移到了其他領域……目前,身體形象的流行趨勢幾乎已超越了服裝的流行趨勢。”無論是健康飲食文化還是健身運動文化,都在強調身體的重要性,纖瘦健美的身材比奢侈品華服更能彰顯階級、品味和權力感。整本書包羅萬象地列舉了各種時尚背後對人的規訓方式,破除了時裝帶來的障眼法,最後卻拋給讀者一個更爲本質的問題——如何直面身體,並與其達成和解。
被誤解的身體——誤診困境
劍橋大學生殖社會學系博士、社會學家瑪麗克·比格的《製造誤診》是一部深入探討身體與醫學、科學之間關係的社會學作品。瑪麗克在序言中說到:“人們曾假定醫學是客觀的,醫學知識是權威的,這種觀念對女性有害。死亡率的高低往往與是否缺乏高科技醫療手段關係不大,而更多地與社會技術是否存在缺陷密切相關,因爲社會技術直接關係到醫療服務的可及性、響應性以及能否滿足患者的實際需求。”這正是本書最核心的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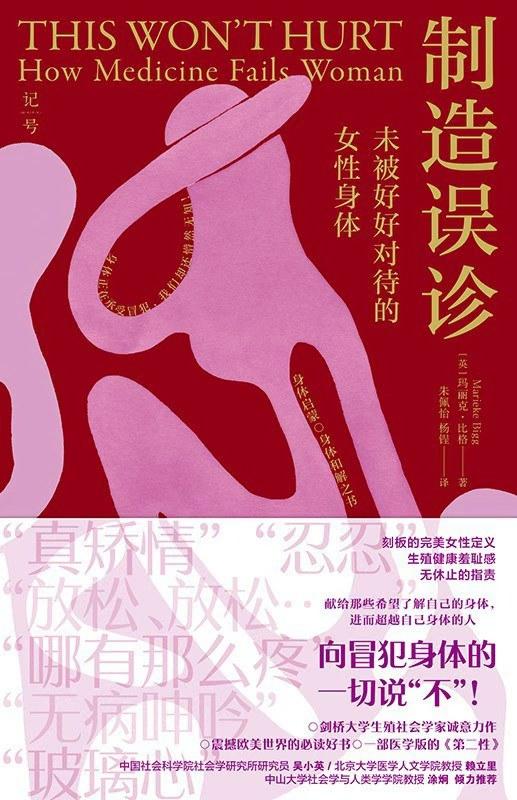
《製造誤診:未被好好對待的女性身體》,[美]瑪麗克·比格 著,楊 鋥 朱佩怡 譯,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25年出版
比如,女性的心臟病發病症狀可能有別於男性,有研究表明,女性心臟病患者一開始就被誤診的可能性要比男性高59%。女性的心臟病發作症狀總是被醫療人員認爲是壓力導致的心理問題而非生理問題,從而被忽視。許多高危婦女沒有得到充分的預防保健,面向女性的心臟病預防宣傳也比較少。與心臟病相反的情況是骨質疏鬆症,醫學界認爲這種病女性更爲常見,更傾向利用女性數據做研究。測量骨質疏鬆症的儀器是骨密度計,但是基於年輕白人女性展開的研究得出的骨密度參考標準很難適用於男性、兒童和其他族裔。況且骨密度並不完全代表骨骼強度,一些骨密度高的女性可能仍面臨比骨密度較低者更高的骨折風險。
瑪麗克認爲:“我們應該——也必須——用社會性別概念來揭示醫學的偏見,倡導將女性身體納入研究和試驗之中。”她覺得,研究者自身的背景和世界觀可能會影響他們的研究,科學研究人員和醫療專業人員必須引入性別變量,打破醫學研究盲點,反省固有的研究方法。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在過去,人們對激素的認識就是男女激素二元對立。但隨着科學和認知的變化,科學家發現兩種激素都能作用於所有類型的身體,它們還能通過各種生物學過程相互轉化並影響同一生理性別的個體。所以現在很多針對激素類疾病的治療,都會提供混合激素治療方案。2016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要求科研基金申請人證明他們在實驗中選用的動物的性別是合理的——過去很多研究都傾向只選用某一性別的實驗動物。如今,加拿大、美國以及歐洲大部分國家都制定了具體政策,要求將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納入臨牀前研究。
在醫療界需要平衡性別偏見的同時,患者也可能因爲社會性別原因無法準確報告身體疼痛。1991年有一項研究顯示:當男性研究人員開展試驗時,女性研究參與者會打出較高的疼痛評分;而當女性研究人員開展試驗時,男性研究參與者會打出較低的疼痛評分。有趣的是,2004年的一項後續研究顯示:當研究人員是地位較高的教師而不是學生,那麼兩性的疼痛耐受程度都會提高。可見患者會下意識地表現社會性別屬性,迎合某種既定的期待。比如,男性爲了維護自身形象,參與癌症篩查的意願比較低;而女性出於性別道德的需要,也不願參與諸如宮頸癌篩查這類婦科疾病篩查。提出這些問題,將女性視角納入醫學研究,不是爲了在醫療領域製造對立,而是爲了帶來更公平、更包容的科學氛圍。
在基因編輯、人工智能以及虛擬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似乎虛擬化、數字化纔是大勢所趨。然而,人們卻越來越多地將目光投向了裝滿自己喜怒哀樂的肉體凡胎,併發出一系列追問:什麼組成了我?身體的邊界在哪裏?是華服羅衣?還是疼痛與衰老?
這些問題恰如鏡子,封存着時代的困惑,也指向着未來的探索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