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非故事到文明星圖:扎克斯·穆達的中國迴響


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至今,中非文學文化交流不斷深入,數代中國學者將大量非洲文學經典引入國內。21世紀,中非關係持續升溫,國內對非洲文學的研究不斷深化。2021年,東非坦桑尼亞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摘得諾貝爾文學獎桂冠後,國內學界掀起了新一輪的非洲文學研究熱潮,非洲文學正從“深閨”走向世界。
扎克斯·穆達(Zakes Mda, 1948- )是南非知名黑人劇作家、小說家、詩人和畫家。他不僅是最受歡迎的南非英語文學作家之一,也是南非文學史上備受關注的黑人作家。2014年,南非政府授予穆達南非文化藝術最高獎“伊卡曼加勳章”,以表彰他在文學領域的傑出貢獻——將南非故事推向世界舞臺。繼去年12月引進出版《紅色之心》後,近期,深圳出版社的“南非文學譯叢”又爲中國讀者帶來了穆達的另外兩部作品——《與黑共舞》和《祖魯人在紐約》。
破除輾轉體認,共談中非文學交流互鑑
2025年6月24日上午,扎克斯·穆達蒞臨上海師範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國家重點學科,進行了“互文性與創作過程”的講座。講座由朱振武教授主持,與談嘉賓有非洲文學研究專家、浙江工商大學副教授李丹和杭州師範大學副教授藍雲春,校內外衆多碩、博研究生參與了本次講座。朱振武表示,此前,由於中非雙方受西方中心主義影響較深,且長期處在西方話語的構建之中,在文化接受的過程中需歷經輾轉方能體認,而這樣的輾轉隱含着一定的誤讀和誤導風險。經過中國學者持之以恆的努力,穆達譯作得以出版,並親自來到中國與各位專家、學者會談,這正是中非雙方堅持對自我的追尋與體認,開闢直接的文學交流對話渠道的卓越成果。而這場對話本身,正是對“輾轉體認”的破除實踐。

“互文性”泛指文本的意義並非由自身獨立創造,而是在與其他文本的“對話”中被不斷重構和生成。穆達說,許多西方學者認爲《紅色之心》借鑑了《黑暗的心》,還指出了兩部小說中的諸多互文性證據,而事實是他從未讀過這部作品,因爲在他所上的文學課上,教材並沒有把《黑暗的心》當成“後殖民文學的典範”。由此可見,受制於不同的語言、文化背景,學者對作者的意圖會產生不同程度的誤讀。對此,朱振武表示,中國學者應立足本土文化建構自主闡釋體系,對英美闡釋擇善而從、補偏救弊。
穆達認爲,文學作品中的互文性是常見且不可避免的,小說不僅可與其它文本互文,還可以與歷史、口述傳統、音樂、繪畫,甚至現實世界互文。交流中,中國學者不僅向穆達學習了他的互文性創作談,也向穆達介紹了中國魔幻現實主義大師——莫言,還爲穆達釐清了多種中文術語的區別,搭建了中非直連的知識橋樑。
根植非洲性,傳播南非故事的新聲音
作爲南非黑人作家,穆達的作品根植非洲性,爲中國讀者帶來了南非故事的新聲音。
穆達出生於種族隔離制度下的索韋託,父親作爲泛非大會長老,因政治迫害被迫流亡萊索托,14歲的穆達隨父踏上漂泊之路。這段經歷使他在科薩語與塞蘇陀語的夾縫中成長,既目睹了殖民統治對傳統社會的撕裂,也在萊索托山區的口述傳統中找到了精神原鄉。1970年代,他在俄亥俄大學攻讀戲劇碩士,後獲開普敦大學戲劇博士學位。2003年至今,穆達在美國俄亥俄大學擔任教授,主講創意寫作課程。
穆達在其流散生涯中,始終以筆爲刃,立足被殖民者創傷記憶,以口述傳統重構本土敘事,揭露文化滅絕之痛,解構西方話語霸權,體現着對非洲大陸歷史文化的深層認同和對故土的深層依戀。
小說《與黑共舞》發表於1995年,奠定其魔幻現實主義與社會批判交織的創作風格,故事講述了出生在哈沙曼地區的萊迪辛和蒂珂莎這對兄妹在南非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矛盾與掙扎,描繪了政變中人民生活動盪不安的場景,揭露了利益燻心下懷才不遇青年的猙獰,歌頌了堅守故土的人民的高尚品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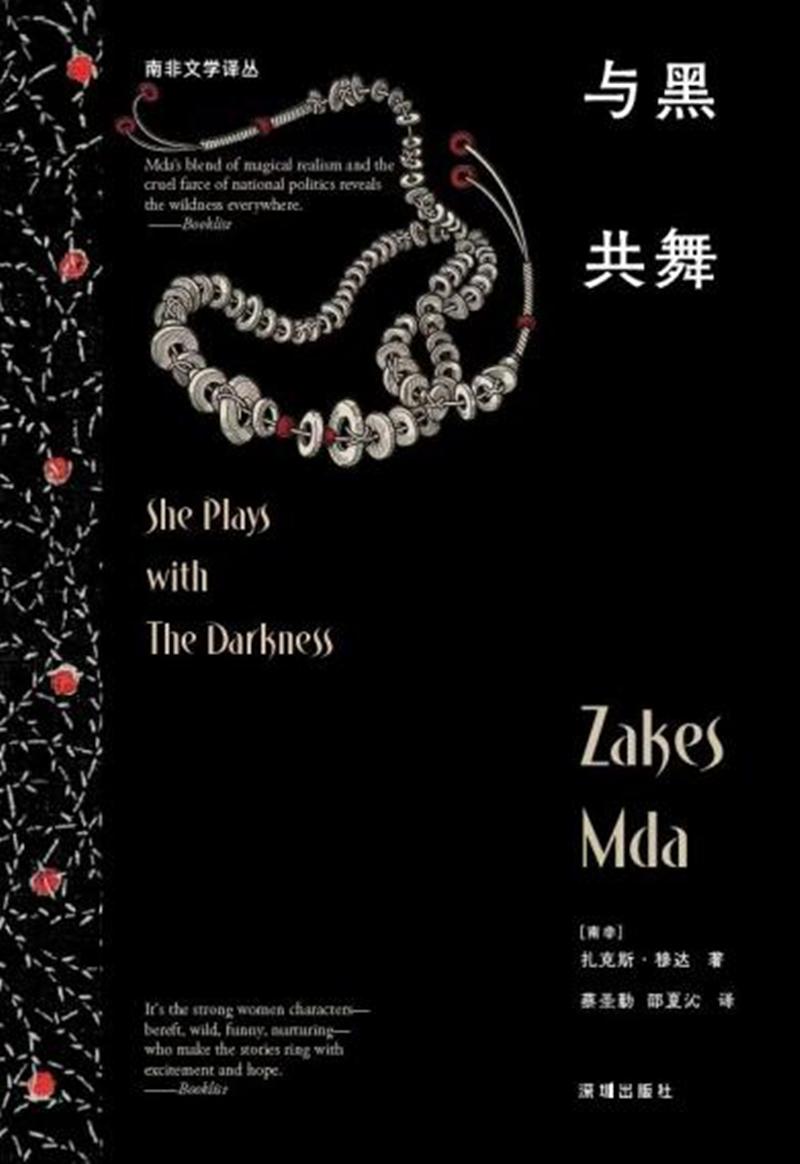
2000年發表的《紅色之心》則展現了穆達敘事技巧的精湛與歷史小說創作的才華,助力其獲得英聯邦作家獎,被《紐約時報》譽爲“新型歷史小說的典範”。紅色,對應着科薩人用赭石顏料裝飾自己的傳統,“紅色之心”既代表科薩族祖先的信仰與傳統生活方式,又體現當代科薩人對新南非建設的期許。故事以19世紀科薩族人的“殺牛運動”爲背景,穆達採用檔案拼貼的手法與多視角敘事,模仿科薩人集體口述歷史的方式,讓歷史不再是單一權威敘事,而是不斷被重構的記憶——既是對殖民官方歷史的抵抗,也呼應殺牛運動中預言的多版本傳播。穆達將科薩人先知的起源、科伊人神話中的創世神、英雄的故事,女先知的寓言融入文本,並通過非洲人對先知的敬畏,體現其對土地的虔誠與生命的熱愛和殖民者利用原住民的信仰製造衝突、掠奪土地的暴力與罪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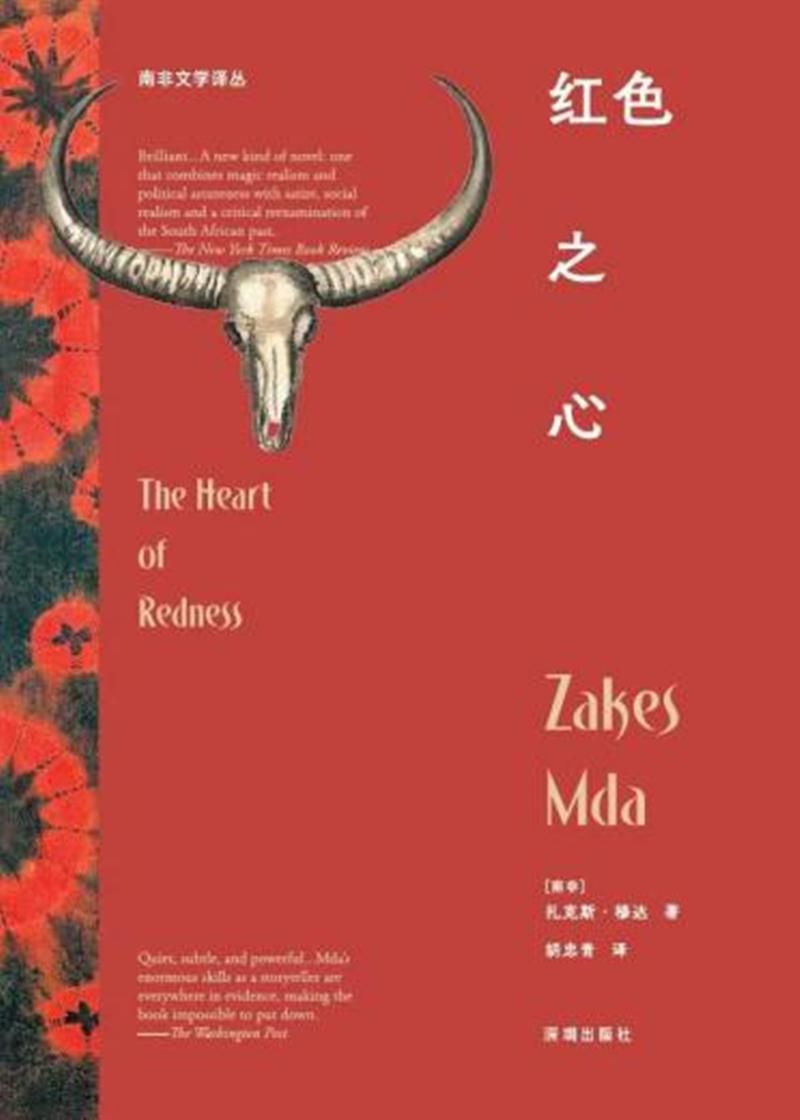
《祖魯人在紐約》發表於2019年,故事講述了在祖魯王國備受尊崇的武士姆皮耶津託姆比因觸犯王國禁令被迫流亡到了紐約,他的名字被白人簡化成 “艾姆-皮”。爲了謀生,他加入馬戲團,與非洲同胞一起忍辱負重,扮演“野蠻祖魯人”,以滿足白人對非洲大陸的污名化想象。穆達用寫實主義的筆觸揭露了“人種秀”“畸形秀”的骯髒貿易,以尊嚴敘事刺破西方獵奇想象。在艾姆-皮的歷程中,遇到了許多和他一樣被迫當成展品謀生的人,但艾姆-皮始終捍衛祖魯族的尊嚴,面對白人的歧視、剝削和羞辱頑強守住自己的人格底線。在故事的最後,艾姆-皮與國際博覽會上的祖魯人相遇,一同乘船回到非洲,致力於家園建設。這是一個跳着戰舞的當代英雄,在歷經磨難後,懷着樂觀的希望榮歸故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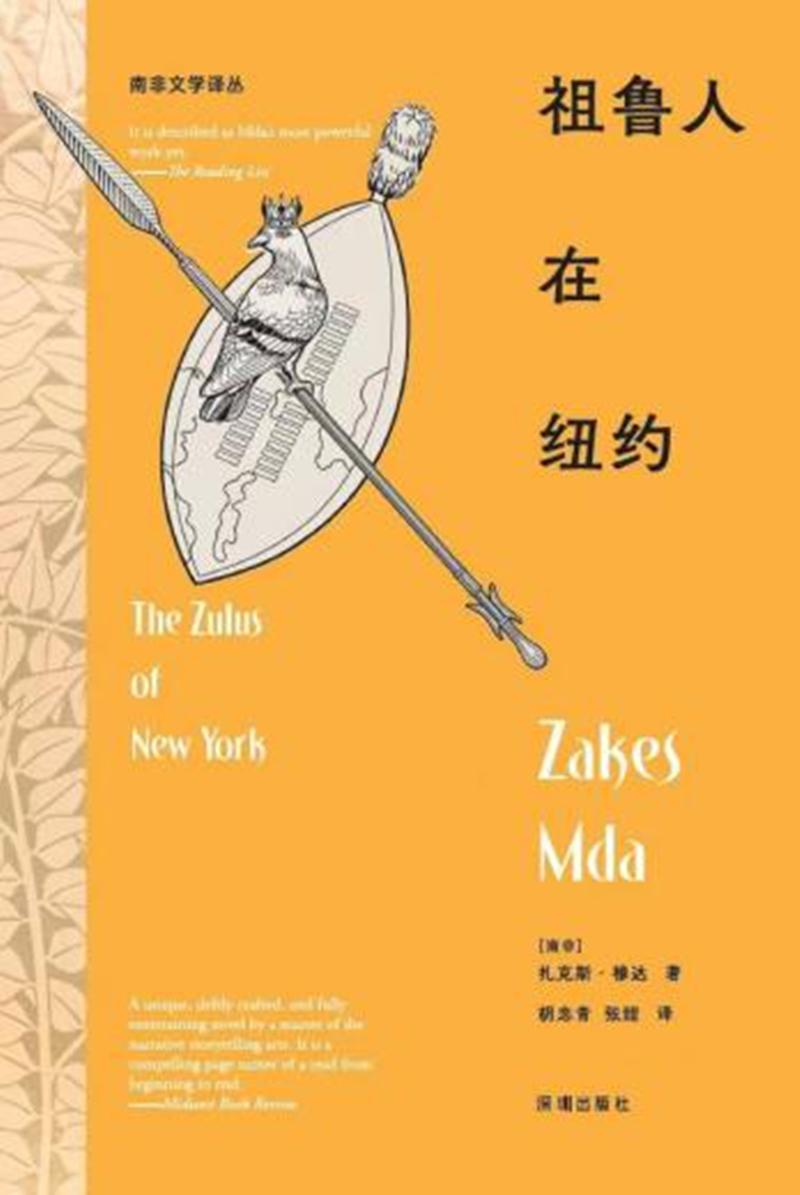
構建中國非洲文學學,重構文明對話星圖
若沒有蔡聖勤、邵夏沁、胡忠青、張甜等譯者的譯介引入,我們大概率會錯過穆達筆下南非故事的新聲音。從對20世紀外國文學翻譯的數量統計來看,國內對非洲文學的翻譯在六大洲的比例中仍是最少的。朱振武教授在《中外文學的傳播互鑑與歸異平衡——以“中國非洲文學學”的建構理路爲中心》一文中指出:實際上,非洲文學目前真正呈現給我們的首先是西方世界眼中的非洲文學,其次是部分非洲學者和作家呈現給我們的非洲文學,最後纔是中國學者在接受和研究了西方學者和非洲學者成果之後建構出來的非洲文學,這與真正的非洲文學還相去甚遠。可見,中國學者們構建“中國非洲文學學”,既是突破西方學術壟斷的戰略需求,亦是踐行全球文明倡議、繪製去中心化世界文學版圖的關鍵實踐。
近幾年,中國各界學者在非洲文學研究、譯介上均有重大突破。各出版社也加大了非洲各語言文學譯介的工作。閱讀、譯介、研究非洲文學,對世界文明的互鑑、融通、共生共棲具有積極推動作用。從蒂珂莎與壁畫共舞的山洞,到克羅哈村殺牛運動的歷史血痕,再到艾姆-皮在紐約跳起真正的祖魯人之舞,穆達的三部曲實則是同一顆“紅色之心”的脈動:讓被殖民撕裂的記憶,在互文性敘事與文明交流互鑑中重獲血肉。作爲中國讀者,我們不僅是在閱讀南非故事,更是在重構文明對話的星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