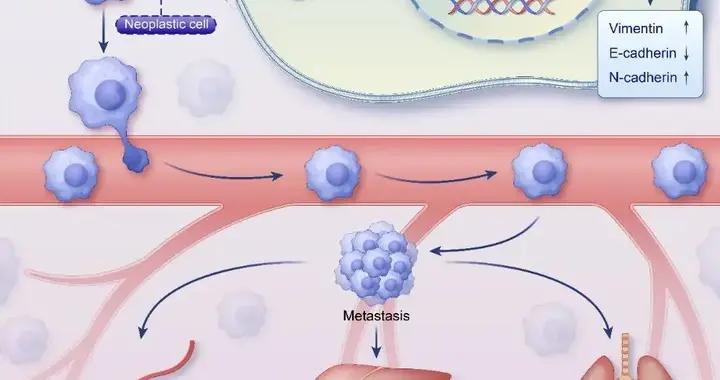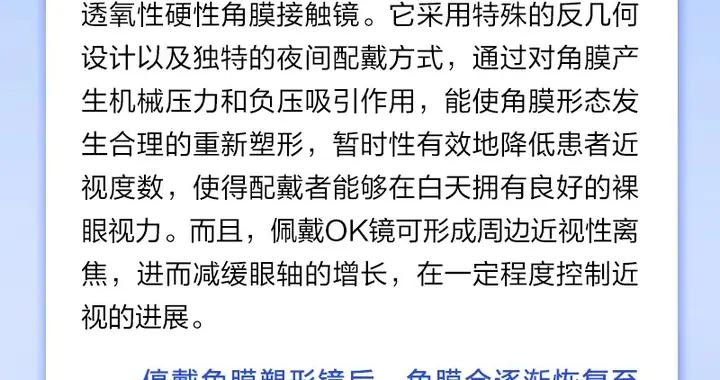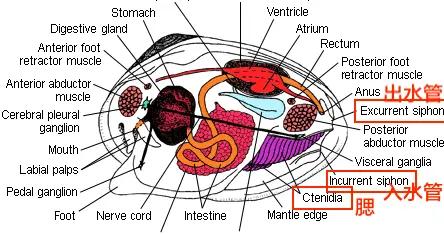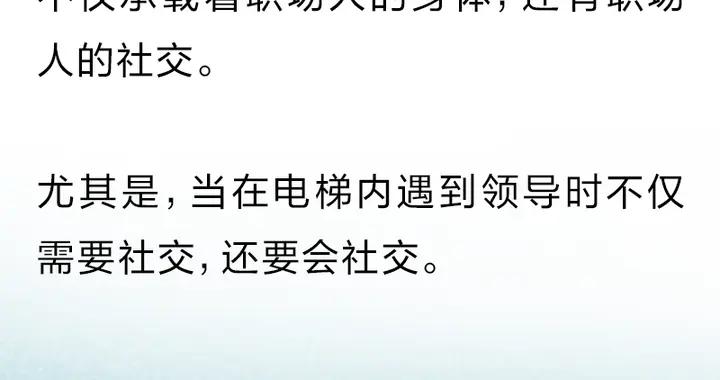多少短劇劇組住的酒店,是明星雲集的電視劇劇組根本住不起的
劇組酒店預算集體縮水背後。


最近,我和閨蜜A小姐約了個飯。
她是業內小有名氣的影視製片人,常年帶着劇組在全國各地跑。
我們見面那天,她剛剛從山東出差回來,曬得有點黑,邊翻菜單邊苦笑:“我這個夏天,彷彿在各城市酒店之間打卡。”
一聊到酒店,她就開始了滔滔不絕的吐槽。
“你知道我們現在帶劇組,最頭疼的事是什麼嗎?”她一邊撕溼巾,一邊抬頭說,“不是演員檔期、劇本過審,是訂酒店。”
我有點好奇:“是明星要求寶格麗、安縵大套房訂不到嗎?”
結果閨蜜直接翻白眼:“寶格麗?安縵?那種是拍廣告、走紅毯纔敢開口的事。我們拍劇動輒一兩個月,講真,要誰提這種名,全國都要給她拉黑。”
她解釋,大多數明星不會說“我只住XX酒店”,他們會留一手,寫在合同裏的是“五星級酒店套間”。
四平八穩,體面而模糊,背後的潛臺詞是:“我不指定名字,但你別太寒酸。”
真正的選擇,其實落在製片人手裏。
A小姐說她已經練出了一套引導式選房術。
“我一般會給演員團隊提供三到四個選項,都是在我預算允許範圍內挑的,比如某個國產五星酒店、一個新開的國際品牌、再加一個服務式公寓,然後讓他們自己選。報價我也不會一次說死,但會暗示哪家是最實用的。”

聽上去挺專業,但A小姐現實中操作遠比我想象中拮据得多。
“你知道我們普通劇組住多少錢的嗎?”她一邊喝水一邊說,“90-110元,最多140元,這就是我們每晚的標準。”
我驚訝:“你這連如家都訂不起吧?”
“說得好像我們住得起如家似的。”她笑着搖頭,“連鎖酒店現在根本不接我們這種長租單,除非淡季或者虧本促銷。”
“我們大多數時間住的,都是郊區的非連鎖酒店、私人老闆開的賓館,關鍵是要大、能改造,比如把餐廳改成服裝間、把地下室接上下水接洗衣機。”
見我錯愕表情,她又補了一句:“麥琪,你知道我們對房間唯一執念是什麼嗎?是衛生!”
閨蜜一字一頓:“我們反覆強調衛生。只要乾淨,別的都能忍。”
然後,她給我講起某次在重慶工廠區拍攝,爲了節省預算,住進一間不到100元的酒店,硬着頭皮熬了三個月:“每天回房,第一件事就是用溼巾擦牀板,用自己的毛巾墊着枕頭。我們自己知道住的有多寒酸,但也只能咬牙堅持。”
A小姐語氣很淡,像在複述別人的故事,但我能聽出來,這是行業共識:疫情後,明星依舊住五星級酒店套間,製片人卻在爲每一張牀位的10塊錢斤斤計較。
她說現在自己對劇照酒店的底線只剩兩條了:乾淨、能開票。
“剩下的,我全都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閨蜜感慨,她其實最懷念的是疫情期間拍戲。
很多人都覺得那時候劇組最難,但她覺得,那是自己人生住得最體面的階段。
A小姐回憶,前兩年,她還能用120元一晚的價格,住進某些協議價300元+的品牌酒店。
那時候行業風氣是隻要有預算,大連鎖也肯談,小酒店也肯降,製片人只要談得動,就能讓整個劇組睡得踏實。

現在,她說,二線城市想談到140元一晚的酒店都得求爺爺告奶奶,所以只能找那些常年接劇組的酒店。
“我們現在是縫縫補補過日子。”A小姐抿了口茶,用這個詞來形容現在的劇組製片的工作狀態。
她笑了笑,和我舉了個例子,提到上個月考察了一句上海遠郊區縣的經濟連鎖酒店品牌,外觀看着很舒服,結果一問價格,直接勸退。
A小姐隨口問一句:“有沒有協議價?我們劇組有幾十間長租。”
對方拼命搖頭,連試圖談判的空間都沒有。
閨蜜感受到了後疫情時代風向變化,國內連鎖酒店以前還願意和劇組聊聊,現在連開口說話都勉爲其難。
但她也說,幸好大家心裏都明白情況,包括明星。
A小姐慶幸現在的明星也沒以前那麼多王爺公主病了。
她說,自己見過某師奶收割機男演員要求住上海靜安香格里拉套房,但那種情況,往往是劇組客串、短住,時間可控,成本能算。
而跟組兩個月的主演,嘴上雖然寫着“五星酒店套房”,心裏其實都明白,真要選了特別貴的酒店,拍攝預算就得從其他地方砍回來。
“你選貴的酒店,我就只能減你片酬。”A小姐直言,“明星團隊都不傻,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畢竟這年頭,我們製片預算表上所有東西都在縮水,包括演員的待遇。”
她說得很平靜,像在談別人的事,但我能聽出那股疲憊。
閨蜜自嘲說,以前住得差也認了,畢竟那時候工資高,獎金多,年薪百萬算是常規行情。
但現在她早就降薪了,連帶劇組的額外收入都沒了。
“你知道我疫情前一年年收入多少嗎?”閨蜜抬頭看我一眼,沒等我回答,自己接上,“連以前一半都不到。”
她說完,語氣卻並不沉重,反而像是在陳述某種行業共識:“至少我還在牌桌上,就算沒被淘汰。”
A小姐其實也理解,大家都難,一家酒店住久了,前臺經理、客房大姐、保潔主管,她都能叫上名字。
有時候晚上收工回來晚了,順口多聊幾句,她也能聽見點有的沒的,誰誰工資被砍了,哪個部門裁了一半。
她反問我,“你有沒有發現,最近很多酒店房價漲了,但服務反而縮水了?”
閨蜜把這當成連鎖反應裏的其中一環。
“預算被砍的不止我們劇組。”她嘆了口氣,“還有劇組酒店。”

前段時間,閨蜜休假,在北京住進了一家桔子酒店。
她實在太累了,剛結束一部劇組的善後收尾,想着給自己放幾天假,住好點。
結果第二天一早,她下樓喫早餐的時候,看到一羣年輕人正圍在一樓大堂中央的大長桌前開會。
一開始她以爲是哪家創業公司在路演,後來聽了兩句才發現,那是另一個劇組。
拍短劇的。
十幾個人,編劇、導演、主演、場記,電腦全擺出來,帶着小耳麥在一邊剪輯一邊討論。另一邊,演員對着玻璃窗練臺詞,邊說邊拍,拍完立刻改劇本。

A小姐一愣,轉身回房的時候,跟我說了句特別諷刺的話。
“他們這種短劇劇組,反而還能住得起桔子這種輕奢。”
“我們正劇劇組,好幾百人的項目,還在郊區比誰住得更差。”
閨蜜說這話的時候,我能聽出來有點鄙視,還有點羨慕。
她當然看不上那些一集不到一分鐘、全靠封面和狗血劇情吸流量的短劇內容。
但A小姐也不得不承認,現在的資金、話語權、甚至年輕編劇和攝影的資源,都在慢慢往那邊流。
“以前我們會笑他們說拍快手戲,三天寫完,七天拍完。”
“現在他們反過來笑我們,說拍長劇纔是冤大頭。”
這場位移,是疫情三年後加速發生的。
大廠收縮,平臺控盤,營銷轉向,原來能燒錢拼製作的項目越來越少,連帶着,能撐起一個大中型劇組喫住行的預算,也越來越少。
而短劇呢?
內容輕,迭代快,回本週期短,不需要明星,觀衆也不挑,廣告客戶看重的是轉化效率,平臺看重的是停留時長。
更關鍵的是,投資人看到了結果。
正劇拼了兩年拍完,播出遙遙無期,短劇三天上線,一週變現,流量能換廣告,IP還能開發成第二季、換主演、再復活。
這一來一回,大家心裏都有數了。
閨蜜說,現在不是誰預算高誰話語權大了。
是看誰能用最少的錢,控住風險,撐到殺青。
她說完這句,沉默了一下,又加了一句。
“現在連酒店,都能看出誰纔是我們影視劇行業的主角了......”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旅界 (ID:tourismzone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