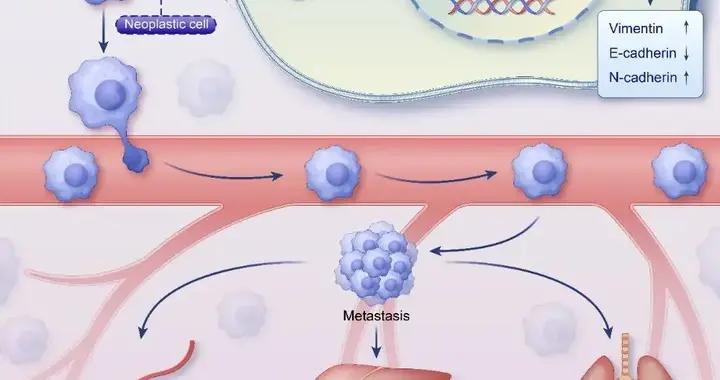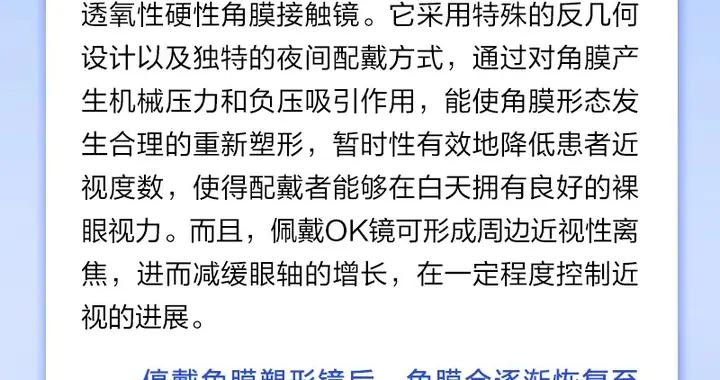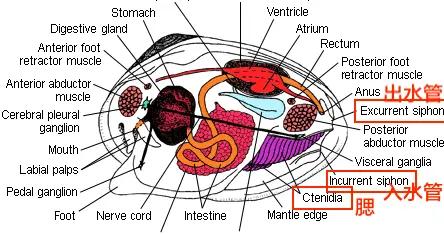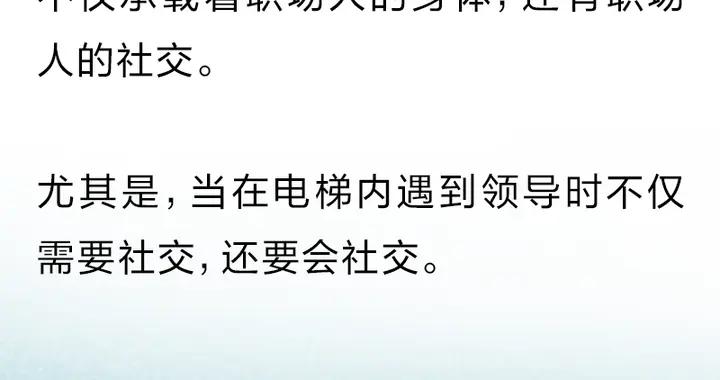無障礙需求很小衆嗎?它可以跟每個人都有關係 | 播客
你見過那種可以把聾人的手語轉換成口語的手套嗎?或者是一根集成了各種功能的新式盲杖?是不是覺得炫酷的科技能給殘障人士帶來很大的幫助呢?
國際殘障權利運動有一句標誌性口號,“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做關於我們的決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然而在現實世界裏,幫助殘障人羣的技術往往是非障礙者設計和生產的。
有些時候,非殘障者的考慮和殘障者的需求距離遙遠,還有時,兩方的溝通都存在巨大障礙。對此,果殼的播客“果殼時間”製作了一期節目,邀請兩位從事殘障事業多年、本身也是殘障者的嘉賓,從自身視角來聊聊,真實的無障礙需求到底是什麼樣的,殘障者希望如何參與其中。

歡迎小宇宙掃碼收聽↑
在普遍沒有考慮無障礙設計的環境裏,有些身體特徵讓殘障者處處碰壁,但正是這些特徵,讓他們更能發現所有人身處的環境、所有人都使用的工具應該怎麼改進。而這種改進不會只惠及殘障者,因爲每個人都可能在某一刻成爲那個遇到障礙的人,無障礙坡道的推廣是其中廣爲人知的一個例子,這次我們想聊得更多。
聽到最後你或許會發現,這期節目又是一個關於尋找和接納自我的故事,這完全可以是任何人的故事。
嘉賓介紹
吳少玫,AImpower.org (一家致力於爲弱勢羣體研究和搭建技術,以消除障礙並提供切實利益的技術性非營利機構)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少玫曾任Facebook和Instagram的研究科學家,領導推動了輔助類功能、人工智能促進包容、公平性等多個“技術向善”計劃。少玫擁有康奈爾大學信息科學博士學位,並分別在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和清華大學獲得了計算機碩士和學士學位,她是一名口吃者。
紀尋,奇途無障礙殘障社區創始人,殘疾人事業發展研究會理事,歐洲無障礙旅遊協會中國聯絡人。紀尋領導着一個20,000+人的殘障社區,並於2022年發起博物館無障礙測評項目,入選知乎燈塔計劃。迄今爲止,紀尋和團隊爲全國30+博物館創作了無障礙遊覽指南,影響了數十萬有無障礙需求的訪客。紀尋擁有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育學碩士和巴黎政治學院發展學碩士學位,她是一名罕見病患者和輪椅使用者。
以下爲節目文字實錄:
無障礙爲什麼是一件
值得我們投入的事
時間節點
02:44 入職當月成爲facebook新員工修bug大王,但是怎麼修好的bug還在反覆出現?
07:36 每天有5萬人在使用讀屏軟件功能,“好少”?(少玫補充:實際應在5萬~10萬之間)
11:02 貌似瑣碎的小問題日積月累,會形成一種感覺——我不重要
14:17 在洛杉磯大街上駕駛自動輪椅,讓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18:01 離開學術環境的支持,開始被社會毒打
21:14 只有1%~2%的訂單來自特殊需要旅客,爲什麼大廠願意投入人力和資源
明月 00:01
hi,我是明月,我們應該都見過那種很神奇的案例,高科技產品讓看不見的人又能看見了,讓癱瘓的人又能走路了。或者是一副手套,把聾人的手語轉換成口語說出來了。有了這些技術,殘障者的障礙是不是真的就被去除了呢?話說回來,殘障者面臨的真正障礙到底是什麼呢?他們需要的真的是通過技術彌補自身的所謂缺失,成爲和其他人一樣打引號的標準的人嗎?本期節目的兩位嘉賓吳少玫和紀尋都從事殘障事業多年,本身也是殘障者,我想請他們來聊聊真實的故障礙需求到底是什麼樣的,“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做關於我們的決定” 這句著名的口號在現實生活裏到底應該怎麼體現。
明月 00:49
在普遍沒有考慮無障礙設計的環境裏,有些身體特徵會讓殘障者處處碰壁,但很多時候,正是這些特徵讓他們更能發現所有人身處的環境、所有人都使用的工具,到底應該怎麼改進。聽到最後,你或許會發現,這期節目又是關於尋找和接納自我的故事,這又完全可以是任何人的故事。需要說明的是,嘉賓的言語障礙造成的卡頓痕跡並沒有在後期處理的時候完全抹去。在這期關於無障礙的內容裏,我們不打算簡單的用技術來修正這些瑕疵,希望大家也能在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裏更直接的感受這樣的交流和表達,他可能不夠流暢,但是最爲準確,也足夠真誠。另外爲了讓更多的朋友瞭解本期內容,文稿區附上了節目文字版的鏈接,歡迎查看。今天我們請來了吳少玫和紀尋兩位,那需要請兩位給大家單獨的做一下自我介紹。
吳少玫 01:48
大家好,我是吳少玫,那我現在是在做一個非營利組織,它的名字叫做AImpower.org,我們的宗旨就是想要和那個少數羣體一起來共同研究設計,並且重新創造對於少數社羣能夠賦能能夠喜歡的科技產品。那我在做AImpower.org 之前我是在 Facebook 工作,大概工作了 9 年多,我在那邊一直是一個研究科學家,做了一些人工智能相關的工作,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圍繞着殘障還有無障礙展開的。
明月 02:36
少玫自己一直是一路學霸出身,後來也在大廠工作,其實開始做這方面的工作會有一點誤打誤撞的感覺嗎?
吳少玫 02:44
對,我其實博士的時候沒有專門研究誤障礙,我一路是做一些算法,一些大數據,做一些大模型,比較純那個計算機一路出身的。所以我其實先前沒有特別的跟比如說終端的用戶接觸,甚至沒有特別想,反正每個人都是一個數據吧。但是後來我到臉書工作以後,他們有一個挺有趣的新員工入職的過程,就是你有 6 到 8 周的時間,你可以做整個公司每個產品,有比如說有一些小的bug,他們的目的是想要讓新的工程師可以熟悉整個公司全部的代碼框架,就是說每個產品他們的底層邏輯,理論上你是可以每個產品都試着做一下,還有每個產品團隊合作以後,你可以選你想要加入哪個團隊。
吳少玫 03:51
但是因爲當時我去之前我就想好我要加入他們研究團隊,所以其實我並不是特別需要去選擇,但是我就覺得挺好奇的,就是想要看這個大公司他們的所有的這些代碼框架都是怎樣,所以我就沒有特別的去篩選,就等於是說隨機看到哪個,隨便有一些急的 bug 丟給我,我就會做,所以說在這個隨機的過程中我就收到了有一個bug,是說要好像是修好 Facebook 那個 APP 裏面有一個按鈕,就是沒有alt-text,沒有label。
吳少玫 04:39
我當時收到這個 bug 的時候,我就是完全看不懂,完全不明白,因爲我就是去我們的那個 APP 上面看到了那個按鈕,上面是有寫文字的,所以我就很迷惑,我就說誒?誒,已經有寫文字了,爲什麼還有人說沒有文字呢?所以說後來爲了修好它,我就去研究一下alt-text 的含義,然後我就在這個過程中瞭解了一些無障礙的規範,然後我就發現其實也很容易修,就是加一個屬性alt-text,然後把它寫上去就好。我做完以後我就想說,唉,這個好像很容易修,然後我就想看一下我們整個公司的那個代碼庫裏面有沒有別的類似的問題。我就掃描了一下我們的整個代碼庫,我就發現,哇有上百個按鈕都沒有alt-text,我就順手全部把它們改了,改完以後我就獲得了那個單月修 bug 比賽冠軍,對,我也就誤打誤撞,後面我就領到了件 t-shirt,我就非常開心,信心大增。
吳少玫 06:13
這個就是我在剛入職待前兩週的事,所以說因爲這個鼓舞我,大概一有空我就掃一掃我們的codebase,看看有沒有類似的bug,我就修一修。然後呢?修久了以後我就發現每次掃好修完以後,過兩週又會有新的相同的問題出現了,我就發現新的代碼又沒加,或者是我先前加好了以後別人改一下又會給它刪掉,我就覺得有一點崩潰,我就想說是不是因爲實際上沒有人在用這個功能?就是說因爲這個alt-text 實際上是給那個讀屏器的用戶使用的,就是說要是視障用戶的話,他們看不見,就需要用一種軟件叫做讀屏器,就會把這個屏幕上的內容說出來念給他們聽,所以說如果有一個按鈕的話,你要是加上那個alt-text 的屬性的話,讀屏器軟件就可以正確地讀出它那個按鈕的功能。
吳少玫 07:36
這樣,所以我當時想爲什麼這麼小的一個問題一直都沒辦法徹底解決?我就想說是不是因爲實際上沒有人在用這個功能?那我就想看一下到底臉書的用戶多少人是在使用這個讀屏器軟件,然後我就跟別的工程師一起研究了一個辦法,可以檢測。當然這個其實也挺複雜,因爲有很多很多各種各樣的讀屏器,它們跟我們系統交互的方式也是有些差別,後來就發現大概每天有大概5萬個用戶。然後我就覺得,哇很多,因爲我先前真的,我也沒有親身跟盲人或者是說視障用戶接觸過,所以我也沒有看見大家如何使用那個讀屏器來登錄,或者是說使用臉書。所以當我看到5萬個人的時候,我就覺得,哇,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但是實際上我是蠻開心的,我就感覺到我做的事情好像每天都可以影響到至少5萬個人。我就回去跟有一些產品組,他們有特別多這種問題的組,我就同他們的產品經理交流一下,我就說你看很多人在用這個產品,然後你們組的code經常就會沒有加alt-text或者是別的這樣的問題,我就想要可以激勵大家,或者說可以讓大家比較重視這樣的問題。
吳少玫 09:32
結果大部分人都說,5萬?好少,當然他們也沒有明說,但是就他們反映就說,哎呀,我們還有很多更加重要的問題,更加緊急的目標,或者是說更加大的需求要改,這個我們沒有辦法調高它的這個優先級,所以我就有點碰了一鼻子灰。那我就想說,可能光給大家看這個數字還是不夠,因爲 Facebook 臉書每天登錄的有七八億人,所以說可能相對來說這個數字對於大部分產品經理來說並不是一個特別驚人的數字,所以我就想說,那我們就活生生的找一個視障用戶,然後錄下來,或者是問問他用臉書的體驗,然後把他這些痛苦掙扎錄下來反饋給我們的工程師們看。所以我就鼓起勇氣參與了用戶調研,我就親自去邀請了一些視障用戶,去跟他們聊天,做一些面對面的交流,就是理解他們使用臉書的挑戰什麼的。
吳少玫 11:02
從這開始我就踏入了無障礙的世界,因爲我覺得當我跟視障用戶或者是跟別的這些少數羣體用戶交流的時候,我覺得非常能夠感同身受很多他們說的東西,而且我也發現他們碰到的挑戰很多並不僅限於說有一個按鈕沒有標註,或者是說某一個功能沒有做好,而是這種無時無處、時時刻刻的這種隱形的障礙,就是當你每一天登錄的時候,你沒辦法確認有一些功能,昨天可以用的,今天還能用嗎?你的生活就是要隨時隨地的,要面對一些沒有辦法預知的挑戰,然後很多時候當你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去了解這個問題出在哪裏的時候,就是沒有人覺得這個問題是一個非常高優先級的問題,或者是覺得它好像不重要,都是小問題。
吳少玫 12:04
有的時候確實是,但是每天日積月累就會形成一個感覺,就是沒有辦法過去的難關,就會讓你整個人就是覺得好像我們自身就會變得不對,就是我的存在並不重要這種感覺。然後我覺得作爲一個女性工程師,在硅谷我也常常遇到類似的情況,可能很多都是小事,比如說全組去外面聚會的時候,去一個很遠的地方,當時我在哺乳期,但是沒有辦法吸奶,反正就是很多這些小小的地方,好像每一件單獨挑出來並不是說一個致命打擊,但是日積月累就是會造成讓你覺得好像我不屬於這裏,我不重要,大家覺得可有可無這種感覺,所以anyway,我就感覺需要做出一些改變。
明月 13:06
少玫從此找到了人生使命。今天我們要聊的其實就是少玫剛纔說的這些障礙羣體,其實不只是障礙羣體,是每個人其實都有一些障礙的時刻,如果總是感覺到自己不被重視,自己的需求得不到滿足的話,生活就會變得非常的困難。嗯,這是少玫,然後紀尋也可以來講一下自己的經歷。
紀尋 13:28
剛纔聽到少玫講的其實也有很多也是發生在我自己的人生的歷史之中,不同點是在於我對於自己,或者說對於無障礙的探索很多是源於我一些個人的經歷。因爲我自己有一種罕見病導致的殘障,罕見病叫做腓骨肌萎縮症,這種疾病就影響到了我的行動能力,因爲我的四肢可能都是變形的。
紀尋 14:01
不光說是要坐輪椅,還有像我的手功能也是嚴重的受限制。跟少玫的人生經歷有一點點相似的是,我以前也是在美國學習過一段時間,並且這一段經歷也是改變了我對於殘障對於無障礙的想法。 2011 年的時候是美國 UCLA 去學習國際教育和比較教育。
紀尋 14:30
之前在國內的時候,雖然其實也是有電動能椅這個選項的,但是可能是在於,第一是認爲你是一個殘障的女性,你可能沒有辦法去駕馭這樣的一個動力設定,然後包括周圍父母,可能也會覺得因爲你的手功能有嚴重的障礙,所以你沒有辦法去操作這個電動輪椅。但是我記得很清楚的是我在美國去尋求殘障學生服務中心的時候,他們就強烈地建議我去使用這樣的一個設備,當時可能也小小的叛逆了一回,然後就決定這次嘗試去駕駛電動輪椅。
紀尋 15:14
其實我在很多的地方寫過。當我去使用那臺電動輪椅在街上自由自在地奔馳的時候,我覺得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這種自由不僅僅是一種身體上的自由,也是一種精神上的,就是那一種你擺脫了別人對於你的很多的定義,社會對你的很多的枷鎖,然後你在人生的這個時刻決定小小的叛逆一回去做一個駕駛員,在洛杉磯的大街上去用這樣一臺輪椅,是這樣的一種帶給你更深層次的自由的感覺,可能會讓你覺得它對於我的人生的改變是更爲重要的。
紀尋 16:00
所以在洛杉磯使用電動輪椅的那一個下午,就徹底而改變我自己對於很多問題的想法,對於一些輔助科技,對於殘障的看法。在那之後又開始去嘗試用別的一些技術,比如說語音識別。因爲我剛纔也說了,我自己可能面臨的另外的一個問題是手功能的障礙,所以我打字、寫字都有很多的挑戰。這樣的挑戰可能讓我在國內的學術環境裏面其實是沒有辦法適應的。比如說去手寫字,我可能完全沒有辦法在一個限定的時間裏面去跟別人來答題用一樣的速度。
紀尋 16:43
當人在國外的時候,他可能會給你更多的一些學術上的支持,比如說給你更多的時間。但是同時我們也是在探索的是,那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技術能夠去支持你?所以也是在美國學教育的時候,開始使用他們自己開發的那個語音識別軟件,那個是 2011 年,其實國內應該訊飛也是在研發,但是還沒有那麼好。
紀尋 17:13
當時用的那個軟件叫Dragon,根據你的東南亞的說英語的這樣的一個語音狀態,來學習你的口音,然後來有一個更準確的識別,所以你的這個軟件裝在你的電腦上面的時候,你不停地去用它,也是在不停地去把你的數據輸入給它,去訓練它,讓它成爲你專屬的一個工具。
紀尋 17:41
所以可能就是在美國的這個學術的環境裏面,對於我而言兩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帶給了我很多的改變,並且也讓我想要去追求更多的人生的自主性,還有選擇的自由。比如說一個選擇,就是說暫時放棄了去讀博士。對,雖然說教育學其實我是可以直接讀博士的,但是我其實也會在想的是,那除了這樣一個學校裏的生活,我還能夠有其他的選擇嗎?那如果說我在一個真實的環境裏脫離學術環境的話,還能夠有這樣的一些支持嗎?我還會遇到哪些問題?當時我非常非常想搞清楚這樣一些問題,所以我就沒有去讀博士。那當然這也可能也是我被社會毒打的一個開始。
紀尋 18:44
無論是在中國求職也好,在美國求職也好,其實都會有遇到過這個社會對於一個有嚴重的肢體障礙者的審視,或者對於你能力的質疑,但我覺得這可能都是我個人成長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下來兩年工作的時間,這兩年做了兩件事情,一個是我去爲文化和旅遊媒體工作,去做翻譯,還有文案寫作。在與此同時我又會覺得這樣的工作雖然說可能帶來了更多豐厚的報酬,但是讓我對於我自己想要去探索的一些問題和我的社區就是距離的就比較遠了。
紀尋 19:37
所以當時我就去找到另外的一份工作,是在北京的一個罕見病的機構去做兼職。因爲我自己就是一個罕見病患者,所以我也是特別想說能夠去通過這樣的一些工作的參與,讓我跟我自己的社區去走得更近。到了 2014 年的時候,是中法建交 50 週年,所以當時就獲得了一份特別的獎學金,去了法國巴黎政治大學繼續學習另外的一個碩士學位,就是更加的專注於非營利組織,更加專注於公益還有國際發展這樣的一個學位。
紀尋 20:25
我能先喝口水嗎。
明月 20:27
不着急,不着急。
紀尋 20:28
剛纔少玫在講言語障礙的時候,我以前也跟她分享過,就是我自己也會有這樣的一些問題,主要是因爲肌肉萎縮帶來了一些心肺功能的障礙,所以會讓我有的時候講話會比較費勁,可能連續講了一段時間以後就會覺得上氣不接下氣的那一種,這可能是病理性的,所以我經常無論是採訪還是做演講,我都得在這個過程中去喝水,對,不好意思。然後到了 2014 年的時候,就是到了法國去攻讀另外的一個碩士學位。
紀尋 21:04
也是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之中,有機會去了世界很多地方旅行,並且開始對這個世界產生了更多的好奇。到了 2017 、2018 年的時候就開始跟旅遊相關的一些機構去工作,特別是在 2018 年的時候,也是非常的幸運,就獲得了全球最大的酒店預訂網站booking.com 的一個影響力的資助,開始來做一個創業機構,也是我現在在做的一個機構,叫做奇途無障礙,奇就是奇怪的奇,途就是旅途的途。
紀尋 21:42
其實當時我們在booking.com 開會的時候,我也聽過他們的一些彙報,他們可能一天產生的 100 多萬個訂單之中,可能只有 1% 到 2% 來自於特殊需要的旅客。對於他們這樣的一個大廠來說的話,這其實也是微不足道的。他們的一個觀點其實跟少玫剛纔講的臉書其實是很相似的,但爲什麼他們還要來做這件事?因爲booking.com,它不僅僅是一個線上的網站,它線下連接了千千萬萬的業主,這個網站能夠連接到的數千萬的業主中有無障礙設施的業主,基本上集中於那些發達的,並且是當地有明確的無障礙法律的國家和地區,而作爲booking.com這樣的一個公司來說,他們願意去投入人力和資源在這樣的一部分他們覺得並不是一個主要的客戶羣體的身上,也是因爲當地法律的要求。
紀尋 22:56
他講的這樣的話,其實也影響到了我很多的想法,就是當我們來考慮去解決這種障礙的問題的時候,可能每一個人都有很多的熱情和情懷,但是有很多時候又會發現好像是解決起來非常困難,我們其實在想的是這樣的問題的根源到底是在哪裏?我們應該也有一個主導力,要去花一些時間影響我們的法律和制度的建設,能夠讓它更適用於殘障和無障礙的發展。
紀尋 23:31
這可能是我在booking.com,也就是說是在歐洲的學習最大的一個感受。然後就是從 2018 年到現在我就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來建設這個叫做奇途無障礙的殘障的社區,去做無障礙旅遊的倡導,也開發了一個無障礙的數據庫。開始只有幾百人,現在大概能夠到2萬人的一個線上社區。讓我們跟殘障社羣可能走得更近和更緊密,也讓我們瞭解到更多他們的需要,所以我們後面也去開發了一些跟就業相關的項目。
明月 24:15
剛纔紀尋提到很多很重要的問題,比如說要有好用的工具,但除了有好用的工具之外,其實也要有整個支持你使用這個工具的環境,這樣才能讓殘障朋友感受到他們非常看重的這個自主性跟自由。剛纔其實用了比較長的時間讓兩位介紹了自己整個的歷程,我相信每一個投身殘障事業的人可能都有類似的心路經歷。就是在很多很多的自己生活的體驗或者是工作的觀察當中發現了這裏有一個巨大的問題沒有被解決,有巨大的需求沒有被滿足,然後自己不斷地被觸動,之後不斷地想要在裏面投入時間跟精力,最後可能像紀尋這樣做成一個很大的社羣,也可能是像少玫那樣去做一個創業的項目。剛纔用了這麼長時間,其實也是想沉浸式的讓大家體驗一下障礙人羣的事業裏面會有哪些問題以及哪些考慮。
一件“小”事:開會
時間節點
25:50 在遠程會議裏,口吃者發言變得更難了
31:44 你在線下開會時會拿着鏡子照自己的臉嗎?那線上會議爲什麼默認需要看着自己?
35:17 人和人之間的連結感,靠的是說話內容之外的東西,我想要認識你,想要相信你
41:59 口吃羣體其實對交流中的障礙特別敏感,有能力設計出更自然的線上交流工具
45:40 聽障夥伴對速記的需求,延展了我們對無障礙的理解
48:15 任何掃碼的動作我都蠻討厭的
49:58 我們的會議屏幕是個四宮格,左上PPT,右上演講人,左下速記,右下手語
51:46 找不到按鈕、按錯按鈕看起來是小事,但對自身的負面反饋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總有一天山崩了
55:45 唱歌比賽不應該只是爲唱歌好的人設置,言語障礙也可以參加,手語歌也是歌
明月 25:11
我一開始準備了一個小小的話題,就是從我們現在在用的這個視頻的軟件出發,因爲我們現在是遠程錄製,我們就需要使用一個視頻軟件,因爲少玫在國外,所以我們現在使用的是Zoom。那可能如果國內錄製的話,我們用的比較多的是騰訊會議,這個會議軟件大家應該非常非常的熟悉,就連小學生上網課的時候也可以非常輕鬆的上手來用。但是我現在想通過這個非常具體的工具來讓兩位給大家展示一下有些不能非常順暢使用這個工具的人羣,他們大概會面對什麼樣的障礙。這個好像也涉及少玫創業裏面的一個小的項目。
吳少玫 25:50
對,說起這個就是網絡會議的工具,其實我最明顯感覺到它對我個人來說的挑戰是在 2020 年,就是疫情開始的時候,大家全部遠程工作的時候。噢,對了,我剛纔好像忘記說我是口吃者,我也花了很多的時間來接受自己是口吃的身份,所以待會大家可能會聽到有的時候會有停頓或是重複,或者是加字。其實也是我對於口吃的一種,自己在調整的一種行爲。
吳少玫 26:30
好說到疫情的時候,開始全遠程的時候,我突然發現我在線上會議的時候就是更難發言了,而說着說着說着也會更容易心虛,就會自己fade out掉。當時這對我造成挺大的困擾的,然後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想說是不是我的問題,我還其實找了一些教練什麼的,訓練我的說話方式,反正就是一直都在反思是我自己的問題,我要更加勇敢,我要開口,我要開視頻、開音頻、 unmute,每次開會前都要做很多心理建設。但後來我把這個問題發在當時那個臉書內部也是剛剛成立了一個口吃員工互助小組。
吳少玫 27:26
其實我最早加入那個小組的時候只是潛水,因爲我其實還是挺害怕被人發現我有口吃的。但是疫情時候這個線上會議的問題就是非常困擾我,所以在那個口吃員工小組裏面,某一天我就突然看到另外有一個員工也發了相同的問題,他就發了一條帖子,描繪了跟我一模一樣的狀態,他就說他覺得線上會議很困擾,他覺得他都說不上話,他覺得他沒辦法完整表達他的意思,經常會中途就退縮,我就覺得我也完全有相同的感受。然後他的帖子下面就有幾十條回帖,都是別的口吃者,就是說這是非常正常的。大家也有相互出謀劃策,有的人說你可以關掉你的那個 self view,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的自己的樣子的那個小框。有的人說你可以在開會之前先跟大家講你有口吃,然後這樣可以告知大家,當你說話的時候儘量不要打斷,可以等得久一點。我就發現沒有一條建議是說你要去鍛鍊說話,你要去改善自我,全部都是說可以怎麼樣改變工具的一些配置,或者是說改變周圍人對你的反應。
吳少玫 29:00
我當時其實很感動,因爲長久以來我一直覺得口吃是我最大的弱點,是一個我要加倍努力,然後纔可以去以強補弱,我可以去跟別的同事算是站在相同的起跑線上平等競爭。所以我每次開會前我都非常認真地準備,有時候看到有些人進來好像就是隨口說說,我就覺得,哈,心裏又很羨慕,然後又會覺得有一些氣惱,覺得哇,這麼好的機會。然後每一次做演講 presentation 的時候,我都每一條每一張幻燈片、每一個字我都寫好,連停頓在哪裏都全部都要想好,然後練習很多遍。所以我就覺得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其實結果別人也看不到,效果也未必有多好。每次去講完以後,我自己心裏還是覺得很心虛, 也沒有很享受。
吳少玫 30:00
我覺得就是一個非常表演性的。但是我看到別的口吃同事給的建議,就是都是通過調整你這個工具,調整你的環境,可以讓你有一個更好的體驗,而非說反思或者是責備自我,所以這讓我其實挺感動的。後來我離開臉書以後,我開始做一個非營利機構,這個初衷就是,我覺得少數社羣或者是說殘障社羣其實有很多親身體驗,就是出於我們親身體驗以後有很多非常好的創意,非常好的想法,可以讓這個社會對於少數社羣更加友好。我就想要真的能夠把就是我們的創意,我們的體驗能夠發揚光大。
吳少玫 30:58
剛開始我也就是單槍匹馬,我也沒有任何的資金或者是資源,所以我就想說,那我就跟別的口吃的朋友聊一聊,然後我就去參加了很多口吃小組活動互助會,我就反覆聽到很多人就是說線上會議比較困難,覺得每次開完會好像就是脫了層皮。我就做了一些訪談,然後把結果寫了一篇論文,發在 2022 年的一個 CHI conference,就是一個人機交互的學術會議上,但是總體當然也是有利有弊。
吳少玫 31:44
其實殘障社羣是很會利用科技工具的便利性的,所以說大家也都非常能夠體會到,因爲有了這些線上會議工具,我們纔可以繼續工作,對吧?或者是還可以參與一些社羣事務,就是我們很多互助會都是遠程的。但是口吃者其實因爲我們對於這種交流實際上是有我們特殊的一些挑戰或是需求,所以我們從小其實是特別的敏感,對於交流中的一些困難,或者說人與人交流的障礙特別的敏感,比如說很多口吃朋友都和我說他們很不喜歡這個,你線上會議的時候默認可以看見自己的臉的這個功能。我也開始反思這個功能,說爲什麼我們這個線上會議它這個產品會設計成這樣?因爲實際上我們在線下開會的時候,並沒有人拿着一個鏡子照着他的臉一直在看,對吧?理論上是應該專注對方,專注別人,所以說當你可以看到你的臉的時候,我覺得很少有人不會因爲它而分心。
吳少玫 33:03
比如說我覺得我要是進去一個電梯的話,要是有一個大大的鏡子,很少有人會不去看一眼你的樣子,對吧?這就是一個人類的心理,實際上我剛剛開始錄的時候沒有關掉我的小屏,我就發現我時不時就會看一下我的臉,沒有辦法完全專注在兩位上,所以我就想說最早做出這樣的設計的人是誰?反正一定不可能是一個口吃者,因爲要是口吃者去設計的話,不可能做出這樣子的設計。
吳少玫 33:49
很多口吃朋友跟我說,因爲他們有的時候從小會去做一些口吃校正的時候,就是要被強迫長時間對着鏡子一直練習說話,很多人都會有那種創傷反應,並且當你口吃的時候,或者當你有嚴重口吃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是你最脆弱的時候,甚至有些口吃者他們會臉部會有一些肌肉動作或者是抽搐什麼的,實際上都是他們已經在非常努力的想要發出下一個音,想要說出他們想說的話,所以說這個過程中其實心裏已經有很多掙扎了。然後看到自己臉部的表情其實很多時候就是在雪上加霜,再一次會讓大家覺得更加掙扎,更加難受。可能每一次一點點掙扎,但是久了以後,很多口吃者就會覺得不想要再參與,就會覺得何必呢?太辛苦了。可能我就只是想說兩句話,但是萬一我口吃了,然後我又要看到自己的臉部抽搐,又要提醒我我的困難,我和別人不一樣,這些很多心理上的壓力就會讓口吃者更難參與,就會慢慢地形成一種結構上的挑戰。
吳少玫 35:17
也是談到線上會議,實際上至少跟口吃朋友聊完以後,我也意識到最大的困難並不是內容。我覺得比如說線上會議時候,我們說的內容可能和我們線下會議其實差不多,但是最大差別實際上是一種情感的連接。就是我覺得當我和你在同一個房間,比如說現在要是我們三個人是在同一個房間,真的是有那種氣場的交合,你知道嗎?就是看到你整個身體,甚至你的鞋子,你的襪子,然後你的身體的動作,你有沒有往前傾?你是放鬆的嗎?還是緊張的?然後你的眼神交流,這些我覺得人與人很多一大部分建立信任,建立這種連接感,就是都是靠這些說話內容之外的東西,對吧?我覺得我們從小就被教說,就是什麼要聽這些話外之音,就是很多這些都是靠這些你的動作,你的表情,甚至你的氣味來獲得的。我覺得線上會議就是真的把這一種人與人之間可以連接、可以相互支持的可能性大大的降低了。
吳少玫 36:40
這樣對於口吃的人來說特別困難,因爲很多口吃者可能是因爲我們說話的時候會比較有挑戰,但是從小就爲了應對這樣的挑戰,其實掌握了很強的用身體、用面部表情溝通的能力。我發現很多口吃者都是面對面聊天的時候讓人覺得非常的舒服,他們整個身體動作,他們整個表情、手勢,我覺得都是真的有非常強的這種不用說話就能夠讓人完成溝通的能力。然後他們這種能力在線上基本就是沒有辦法使用,就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他們平時說話是比如需要一些支持網絡,比如說有些口吃的朋友,他們說要是我去開一個會,我有點害怕的話,可能我會選擇一個我的要好的同事坐我的身邊,或者是說我去講一個報告的時候,我的眼神就會一直盯着一個非常友好,就是我的好朋友的臉上。但是在線上會議的話,這些方法就真的沒有可能,反而是一些讓我們覺得不舒服的方面又會被加強。
吳少玫 38:00
所以說線上會議這種它的設計上默認完全優先你的言語表達,或者是優先你說話的內容,然後把很多我們爲什麼要來說話、爲什麼要來開會的終極的價值,其實反而沒有辦法完全體現出來,對吧?要是我只是來說出我要說的話,那我就發給你一封郵件就好,或者是發給你一個短信就好,我們兩個找到這個時間坐在一起是因爲我想要相信你,我想要認識你,我想要知道你是一個怎麼樣的人,我覺得反之亦然,我也想要讓你知道我是誰,對吧?這些在我們這種線上會議的設計裏面其實完全就沒有得到很好的體現。
吳少玫 38:57
這個是我們過去兩年一直有跟口吃社羣,還有跟別的一些有這種言語障礙社羣有交流的一些反思,也包括一些比如說聾人社羣,他們也有他們一些很有趣的挑戰,所以我們從去年開始也有在跟口吃社羣一起重新設計線上會議。我們也發了一篇論文,有很多很有趣的想法,我們希望明年也可以發佈我們的工具,然後這個工具 100% 是由口吃者設計,目前爲止 50% 的代碼也是口吃者寫的。所以我們就也想要在這個過程中證明說我們少數社羣是有能力成爲科技的創造者,而非僅僅是使用者,我覺得這個也是一種連接到剛纔紀尋說的是一種我們的自主性的一個很好的體現。
明月 40:09
我們之前也經常會遠程錄製播客,也會用這樣的工具,但是一般來講,大家用這個工具之前其實都不會特別約定說我們要不要開視頻,而這次跟少玫約的時候,一開始少玫就強調說我們要開視頻。但是當時其實我並沒有太理解這個開視頻的意義是什麼,我以爲只是說大家看一下對方的臉,但是今天剛纔聽了少玫講這些之後,我才發現原來視頻的時候這種面對面的溝通有這麼多的意義。而且我剛纔觀察了一下,因爲我現在是把我們三個人都放在這屏幕上,我確實經常要不自覺的去看我自己,我甚至不知道怎麼把我自己的小框給關掉。所以我之前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情。這次其實之所以邀請少玫來,是因爲我們之前做了一個深度的稿子,就是講口吃以及口吃社羣他們做的一些事情。在那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口吃其實也算是一種言語的殘障,而且在醫學上來講,其實並沒有說一個方法可以矯正所有人的口吃,而讓大家不再口吃。而口吃者經歷的掙扎可能跟其他的殘障又不太一樣。那是那篇稿子教導我的事情。
明月 41:19
剛纔聽了少玫講了這些之後,我覺得我又學習到了線上會議的很多的知識,而且我發現好像說,口吃者,雖然他表面上看起來是有一些言語上的障礙,但是他們其實在這些事情上有優於常人的一些優勢。他們是這個問題的專家,如果他們不去發現這個工具的問題的話,可能我們這種隨便用用這個工具的人,永遠就是你給我什麼我就用什麼。那我看我自己的臉我就看好了,我也意識不到這裏有什麼問題,少玫他們新發布的這個工具我相信也非常值得期待啊。這裏要不要簡單講一下,大概有哪些出其不意的設計?
吳少玫 41:59
好啊,比如說我們現在有一個設計也是口吃者提出來的,就是可以讓你在你的屏幕的前景上面顯示一個像是sticker,就像是一個貼紙那樣的。你可以設計定製它,給它變得很可愛,也可以讓它變得很商業。反正就是寫你的名字,寫了如說你的職位。然後你還可以加上一點你想要跟這個參會者分享的別的關於你的信息。要是你是口吃者的話,你就可以分享“我有口吃,我有的時候說話會有比較長的停頓,請你們等一等我”。但是其實也可以有別的很多用途,比如說我上個星期感冒很重,完全失聲,我也可以寫說“今天我病了,沒有辦法說話,我會通過打字參與”。你就可以有一種更加自然的方式,不用說舉手,然後做一個非常大的昭示天下。
吳少玫 43:05
總體上我們的所有的功能都是要把口吃,或者是別的一些我們的脆弱性,或者是我們在線上會議的一些特殊的需求,可以常態化的一個趨勢,而非是說我要掩蓋口吃,讓我說得更流暢,或者是說讓別人沒有辦法知道我有口吃。而是通過一個自然的表達,自然地告知大家,讓它變成就是像是我今天感冒了,或者是我的家裏小孩生病在家,就是一個很正常的事。也讓大家可以更習慣地去對於別的參會者的需求,能有更多的意識,可以更瞭解怎麼樣去照顧相互的需求。
吳少玫 43:59
我覺得就像我們線下會議的時候,要是有人看上去好像身體很不好或者是很累的話,我覺得大部分人也是會問一聲,你有沒有很累啊?或者是你還好嘛?對吧?我覺得要是在同一個房間,我們其實有更多的這種可見度,但是因爲太遠的話,你就只看到你的肩膀以上,其實可能就是這種相互的需求,就可以更少看到。所以說通過口吃社羣的建議,我覺得其實大家可能也都可以受益,我覺得相互照顧對方就是人與人之間產生連接最好的方式。所以就是其中的一個小小的一個feature。
明月 44:45
我一方面覺得這些觀察這些設計都非常非常的細膩,另一方面我又在想口吃人羣他到底是經歷過多少的折磨,多少的困難,多少的生活中的不便,纔會觀察到所有的這些可以更增進人跟人之間在線上的時候溝通便利性的這樣的時刻,所以他們纔會得出這樣細膩的設計。那紀尋那邊因爲是有一個龐大的社羣,現在有接近2萬人,經常也要通過這種方式來組織大家一起開會。因爲其實現在包括各種各樣障礙的人羣,那不同的障礙人羣要共同使用這個工具的時候,可能大家也有一些自己的觀察。
紀尋 45:23
其實剛纔我們一直在講的是線上的會議,但是在講線上會議之前,我先想講一講線下會議,因爲我們自己對於線上會議的無障礙支持其實是來自於我們在線下組織會議的時候的一些體驗。因爲在 2018 年剛纔我們講過,就是說開始是做無障礙旅遊,因爲肢體障礙者他對於一些硬件的條件的要求會比較高,所以我們可能一開始基本上都是在關注輪椅使用者的一個狀況。
紀尋 45:55
但讓我完全沒有想到的是,我在 2018 年舉辦了第一次的一個線下的無障礙旅遊的分享會,來報名參加的有視力的和聽力障礙的夥伴,其實在我從事這個工作之前,我自己的生活圈子裏是沒有接觸過其他類型的殘障夥伴的。然後當我們在問他需要哪些無障礙支持的時候,聽力障礙者說需要速記或者手語,在速記和手語之間可能通用性更強的是速記。這樣的需求又會爲我們帶來了新的一個 TODO list,就是我要在會場上顯示速記,然後我還需要找到一個速記員。
紀尋 46:42
所以我們要把這樣的一些需求可能要去給我們的供應商來討論,比如說你的屏幕安排在哪裏?速記員又是從哪裏找,本身做會務服務的供應商,你有沒有這樣的一些資源?然後結果發現這樣的供應商是完全都不瞭解這些事情,所以又得靠我們自己去來探索。
紀尋 47:07
但也是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之中,我覺得是社羣中有這些無障礙需求的小夥伴是教育了我們,也是延展了我們自己對於無障礙的理解。也是在他們的支持之下,我們後來找到了這樣的資源,那第一期活動還是辦得很圓滿。那後來我們其實也會發現這樣的一個速記,對於我們自己的組織者也是十分的有幫助的,因爲大家知道就是在所有人分享完以後,你要開始寫通稿,就要來整理大家的發言,原本可能是要靠我們自己去做這樣的記錄的。但是因爲有這樣的一個速記的留存,我們自己的工作效率得到很大的提升,所以原本可能只是爲了聽力障礙夥伴的無障礙支持,最後是讓所有人來受益吧。其實後面就包括剛纔少玫在講的說線下會議中,我們有了更多的與人接觸的空間,但是這樣的一個空間和設置其實帶來了更多的挑戰。以我自己舉例子,我就非常的討厭在線下的會議中,組織者要求我們要拿出手機來做互動,可能你會經常看到說我們來掃碼。掃碼時大屏幕上可能會出現一個小遊戲讓你答題,或者說什麼會讓所有人要在這裏去做一件什麼樣的事情,要投票。因爲作爲一個肌肉萎縮的患者,我的手是沒有辦法舉起來的。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有點很尷尬的去找別人幫忙,然後來去掃碼,其實任何的掃碼動作我都蠻討厭的,包括我們用那個微信公衆號掃碼登錄,每次你都得找人幫忙。
紀尋 49:05
我也觀察過其他的視力障礙的夥伴,當大家被要求要一起來做這個遊戲的時候,也有他的非常尷尬的地方。就是我掃完碼以後你讓我答題,那往往又是一個沒有任何讀屏的系統,那我如何來參與你設計的遊戲呢?最後我們就是在會場其他人的歡呼聲之中,就度過了這樣的遊戲熱場的環節,就感覺其他人都很熱,我們就在那裏很冷。
明月 49:38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紀尋 49:39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相當於說,我沒有辦法跟上你的節奏,然後我碼還沒有掃呢,你就結束了。就經常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態,所以這可能也是在線下會議中我自己的一些感受。那接下來我就會來講一下我們組織線上的一些活動吧。因爲我們線上活動其實不能叫會議,就是我們經常用線上會議的形式去組織活動,特別是在疫情的三年期間,大家沒有辦法在線下見面的時候,我們用騰訊會議可能去上課。我們還搞過 k 歌活動,還搞過相親活動,就是各種各樣的一些活動。
紀尋 50:22
那在這樣的一個活動的參與者中,其實也是全障別的,有聽力的、有視力的、有言語的,還有其他認知障礙的,他們面臨各種不同的挑戰。比如說可能有人是會議軟件就不會用,完全不會用,你可能需要一點一點的教。還有一些需要無障礙的支持,我們現在可能對於聽力障礙者的支持,也是要速記手語的服務。
紀尋 50:51
當然我們也會在探索說,有了速記和手語,我把它們放在哪裏更方便大家。現在一般會議室採用一個四宮格的一個形式。左上角可能是放PPT,右上角是這個演講人,左下角是一個速記,右下角是一個手語。因爲我們每一次來做這樣的活動測試的時候,也會把自己的手機打開來看一看,特別是我們的一些活動還會直播,那如果說你有這樣的一個手機,或者說字幕的功能,但這個字幕顯示在哪裏呢?如果你只是顯示在屏幕的下角這一行的話,那你打開手機可能就看得不太清楚,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求大家使用四宮格的這樣一個形式來顯示,這可能也是我們測試過,大家可能體驗都還比較好的方式。
紀尋 51:46
但是也就會出現更多的問題。比如說我們如果要在這個會議中去邀請需要使用讀屏軟件的夥伴來參與一些活動,比如說去發言,還有一些是喜聞樂見的合影環節,那他可能就沒有辦法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找到那個按鈕。對,要不然就是可能會也會按錯按鈕,其他人在講話的時候,他把語音打開,那可能會造成吵鬧,然後可能會有很多人去抱怨。這樣的一個過程之中也會讓他小小的受到一些傷害,他可能會說我並不是故意的。像合影環節也經常是這樣子的,大家可能都是從小會要求你同一個姿勢,或者要同一個手勢,同一張假笑,來拍個照,對,但是如果讀屏功能做得不好的話,我們的視障夥伴他沒有辦法去做這樣的一些操作,畫面可能會豎着的,或者說是橫着的,反正就是跟別人的都不太一樣,他這個調整過來就調整不好,然後也很着急。
紀尋 53:01
然後他們其實也會再強調一點,說我現在旁邊沒有人可以來幫我來做這樣的操作。如果說是靠我自己,我想獨立去完成這件事情,但是好像在現有的一個技術支持之下,又沒有辦法去完成,這讓他們非常的沮喪。其實也像少玫剛纔講的,雖然你覺得這好像並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你在日常生活中,如果說你經常遇到這樣的事情,這樣一些對於你自身負面的反饋,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總有一天就是山崩了,然後他會影響到你參與社會活動的方方面面,因爲我總會預期在下一次活動裏這個人要讓我幹嘛,那個人要讓我幹嘛,如果我沒有辦法去配合這樣的一個集體的活動,那我可能會受到指責,或者說組織者說不想讓我再參與了,導致他可能下次就不來了,然後把自己封閉起來的這樣的一個狀態,所以我們自己其實也是會覺得蠻沮喪的。
紀尋 54:05
也是希望做會議軟件的夥伴也可以探索出一個更加無障礙的界面吧。剛纔我在講話的時候,少玫在不停地按這個reactions,其實這也是另外的一個功能嘛,就你跟別人來互動,他講話你給他鼓掌,你給他貼紙,或者說怎樣。那其實對於視障夥伴來說,他也想去做這樣的一些互動,但可能是沒有辦法發現按鈕,或者說是讀屏讀不出來。再回到剛纔我講的這個二維碼,可能因爲我自己對於這個二維碼有了非常不好的體驗,那我們自己的一個普遍的做法是說在參加會議之前,我就要把所有人拉在一個羣裏直接發信息,那無論說是視障夥伴還是怎樣,你也不用再去找這個二維碼在哪裏了。
紀尋 55:04
那對於我這樣的一個手機也舉不起來的人來說,我就直接用我的手機去掃碼。而且可能提前拉一個羣,雖然你的工作量可能會更大一點,但其實也會讓別人的交互性更好點,因爲有人可能會在活動開始之前就會在羣裏面聊天了,他也會詢問一些問題,也會讓組織者做一些相應的準備。
紀尋 55:33
所以可能這樣的一個動作並不是很大的改變,但是可以提升大家參與的容易度吧。我覺得這可能是一點。我們現在可能還會遇到的另外的一個問題,是其他的一些活動。比如說我們以前去做那個全民 k 歌,就是我們會有一個線上 k 歌的活動,當時也是經歷了很多挑戰。一個是視障者讀屏那個問題,雖然好像有很多 k 歌的軟件都宣稱自己是無障礙,但是你真正用的時候你會發現不是那麼一回事兒。最後大家都是會瞎按,真的就是瞎按,我就等他一下,他按到那個鍵可以開始唱了,就唱了。
紀尋 56:16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遇到過,說是像言語障礙,非常非常嚴重的言語的障礙,就你完全聽不清楚他在講什麼。然後他說我要來唱歌,因爲我們唱歌有一個環節是你要獨唱,還有一個環節是你要跟人家合唱,然後我們那個言語障礙的夥伴,跟他合唱的可能是我們社羣裏一個唱歌比較好的一個夥伴。
紀尋 56:40
就是即便是在殘障的社羣裏,你會發現大家對於這樣的一個夥伴的包容度也沒有非常的高,大家也會在想的說你這唱的是什麼?你敢來唱歌。或者說是你影響到了你的partner,然後就非常的不公平。但我們當時也在想,那他想來參加這樣的一個比賽,這是他原本的聲音,我覺得這個聲音也是人類聲音多樣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唱歌比賽並不應該只是爲那些唱歌好的人來設置了,每一個人都應該有這樣的一個機會,所以爲什麼我們要禁止他來參加這個比賽呢?那即便最後的分數可能不盡如人意,但是我覺得這個可能也是我們的生活中要去面對的一部分。還有一位聾人朋友,他是用手語來唱歌的。
紀尋 57:38
同樣是這樣的一個問題,手語也是一種語言,他爲什麼不能夠用他自己肢體表演的形式來參加呢?當時我記得也挺有意思,因爲他們的合唱環節 partner都是抽籤決定的,他們的表演形式是唱同一首歌,然後就是他的那個肢體小夥伴唱歌,他用那個手語來表現,其實也是完成得非常的好。我記得我們當時直播的觀衆值的最高峯,就是這一組選手。其實在那之後我自己也開始去關注一些手語的表演形式,這個可能也是我們唱歌比賽的社羣和組織者,以及包括我們唱歌比賽還有一個大衆評審團,他們都是網上招進來的一些網友,可能大多數都是非殘障的,一起來完成的這個項目,也在這樣一個項目中去學習不同殘障羣體的需求。
虛假的無障礙vs真實的無障礙,
無障礙到底是誰的責任?
時間節點
01:00:20 推個輪椅,送些米麪油,拍個照,就叫“助殘”?
01:02:59 無障礙測評項目的篩選問“能不能自理”,我作爲一個不能自理的人,覺得這樣的詞非常刺眼
01:06:47 經常有人重新發明手語手套、盲杖,這是爲了滿足殘障羣體的需要,還是爲了滿足自己?
01:10:20 給一些新的裝備,社會就覺得已經盡到責任,而把最難的那一部分留給殘障羣體自己
01:13:35 殘障是複雜社會系統中的複雜問題,怎麼可能用簡單的技術解決
01:16:04 融入是雙方的事,殘障社羣已經做得夠多了,是時候讓社會伸出手了
明月 58:37
我覺得我不僅對線上會議一無所知,我對唱歌比賽也一無所知,而且我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感受,就是如果一個人他平時不關心殘障羣體的話,他想象中的那種無障礙可能是被宣傳的例子充斥着,比如說腦機接口,讓一個沒有辦法溝通的人,他可以打字了,可以跟別人溝通了,或者是一個外骨骼讓一個不能走路的人可以走路了。這是宣傳中我們印象中的那種無障礙。
明月 59:05
但其實真正的障礙人羣,他日常生活中面臨的就是這種,能不能掃到二維碼這樣的非常非常小的問題。如果你不是殘障人羣,你不瞭解需求的話,你想象出來的那種對於殘障人羣的支持或者是無障礙的設計,可能跟他們的日常生活的需求是完全沒有關係的,我想把它定義成是一個虛假的無障礙跟真實的無障礙。
明月 59:29
剛纔你們講的那些其實是真實的無障礙,那很多我們在市面上能看到那種宣傳的無障礙的案例,其實就是一種,我感覺它更多的好像是爲了顯示這個公司的技術有多牛,但是它並沒有考慮到說能不能大規模應用,不管是成本上還是在需求的滿足上,能不能去大規模的去滿足這些殘障人羣的真實的需求,有的時候還會是一個過度的設計,跟殘障人日常的生活根本沒有關係,這是我覺得非常非常割裂的一塊。之前其實溝通的時候紀尋也講到,因爲你們的社羣很大,也會有一些助殘的團體來跟你們溝通,想要來就是所謂的幫助你們。就這個溝通其實就面臨着這種大家對於對方的需求根本就完全不瞭解,所以展示出一些很變形甚至是會傷害你們的動作。
紀尋 01:00:20
對,其實關於助殘,5月18日就是第35屆助殘日,它對照的是12月3日,國際殘障人日。到了中國中文的一個語境裏面可能會用了助殘這個詞,因爲大家在自己的思維裏面會覺得殘障人士比我個人弱小,我們需要以一種扶助幫扶的態度去來幫助他們。當然我覺得我自己可能還是先認可很多人的這樣的一個發心,但是當我們用這樣的一種態度或者說理念來做殘障工作的時候,會造成了一個非常大的影響是,在你沒有意識的情況之下,你正以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俯視這個羣體。特別是在一些特定的日子裏面,可能也是一些形式主義上的,比如說我照個相、推個輪椅。我們殘障社羣裏經常遇到的一個幫扶,就是給你送一些米麪油。這個在前段時間的易烊千璽那個電影裏好像也有一些展現。送完了以後就大家一起去拍個照,然後可能還要在你的標題底下再一起合個影。我記得比較奇葩的一件事情,好像是某一年的年底,有一個食品廠商,他來找我們來送臨期的食品,這個食品好像是水餃還是什麼的。
紀尋 01:01:57
大概是很多,可能還有一個星期就過期了,他就讓我們去,就在南京市來找很多殘障羣體去發放。後來我們其實也去找了,但結果就是被很多人罵了一通,說難道你真的認爲現在殘障夥伴是喫不飽飯了嗎?或者說你讓我們在一個星期之內消耗這麼多水餃。你並不知道我自己真實的需求在哪裏。這個可能也是廣泛的社會羣體對於殘障夥伴真實的生存處境認知的偏差。
紀尋 01:02:33
可能並不是說我們最迫切的一個需求是要生存的資源,很多殘障夥伴說的是我想要更多的發展的資源,我想要去融入這個社會,我們現在並不是說真的是缺喫的或者缺穿的,而是說我需要更多的機會去工作、去出行,去融入社會。我們現在可能也會發現,好像是在“沒有我們參與,就不要做與我們相關的決定”的這樣的一個倡導理念之下產生而來的一些研究,或者說是殘障的一些項目,它好像表面上是說希望能夠納入殘障的視角,試圖在營造一種我們和殘障羣體共創的方式,但其實有可能是造成了殘障羣體中更大的分裂。
紀尋 01:03:34
我舉一個例子來說。我們在做這個無障礙的測評的一些項目裏面,它的篩選的過程之中,又會用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方式把殘障者分層次。比如說你會就能經常看到一些篩選條件是問你“能不能自理”,但是並沒有對“自理”做任何的解釋。
紀尋 01:04:05
我作爲一個不能自理的人,每次看到這樣的詞都覺得非常的刺眼。在同樣是肢體障礙者的羣體之中,可能有人的自理能力好一點,獨立的能力好一點,那有的人的能力差一點,但是對於參加這種無障礙測評項目的情況來說,他們永遠都是在挑選那種能力更好的,或者說是輕度的,能夠無限接近於非殘障的夥伴去做相關的測評,卻忽視了更多重度障礙者的需求。而這可能又會造成了那些本身更加重度的殘障的夥伴更少獲得了社會的資源和支持。
紀尋 01:04:47
這個可能是第一點。第二點,我們其實也在這個過程中會接觸到,很多的研究者可能以一些我們覺得不是非常正確的方式在獲取殘障夥伴的數據,比如說他們可能在沒有任何倫理委員會批准的情況之下,去在殘障社羣裏面去發送各種各樣的問卷。然後在問卷中可能也會用我們看來會比較刺眼的一些詞語,比如說稱呼聾人羣體爲聾啞人,以及去問一些比較隱私的問題,並且沒有意識到問這樣的問題是否是涉及到了別人隱私,或者說是不是能夠去對於別人造成不好的影響。因爲我們也不知道我們的數據將會被用於哪些地方。這個在我們日常運營中還蠻常見的,並且我也在這個過程之中看到了社羣和一些所謂的專業夥伴之間權力不對等的關係。
紀尋 01:05:59
就是這樣的一些人,他可能用他自己本身的職位和社會的地位,他的更強的一個權力去獲取了這樣一些數據,然後讓自己可能成爲特殊教育領域、殘障研究或者社會發展領域的專家。但其實後面的代價是很多被他們濫用的數據,或者說是一些殘障夥伴在無意識的情況之下去參與了一些研究,並且也沒有獲得相應的credit。我覺得這一點也是讓我會覺得比較難過的一個地方,但是也是希望未來能夠去做出一些改變的地方。
吳少玫 01:06:47
對,我也覺得無論是像設計產品或者是像剛纔紀尋分享的助殘的活動,我覺得他們這一類行爲其實都是主流社會爲了實現他們想要的價值而進行的,而非是說真的是想要滿足殘障羣體需要的價值。比如說像很多產品的設計,像那個剛纔明月老師分享的有一些產品就是感覺和那個殘障羣體的現實很脫離,比如說因爲我在專門研究無障礙,我在這個行業也有十幾年了,我也看了很多產品,我看了很多模型機或者是已經開發出來,或者是一些研究,就是真的一大部分都是非殘障的研究者想當然設計出來,爲了滿足他們對於他們本身的智識的肯定,或者是說對於他們本身作爲人的一種良心上的一種滿足感,脫離殘障現實開發。比如說舉一些例子,好像經常有人重新發明手語手套,就是讓聽障羣體戴着那種手套,然後可以把手語轉化成聲音,就是轉化成口語。
明月 01:08:15
這是一個特別典型的不從使用者的需求出發的案例。
吳少玫 01:08:19
對,就是非常好笑,因爲它完全就是從一個聽者的角度出發,從一個聽人的角度出發的一個產品設計。因爲你想一下,要是一個聽障者戴着這種手套,就算他可以完美地把手語轉化成口語,大部分情況下其實沒辦法,但是就算他完全解決了技術問題,可以把手語轉化成口語的話。但是他這個只是單向的,只是讓聽人能夠破譯這些手語的信息,但是完全沒有考慮到反方向的交流,聽障者還是沒有辦法獲得這個聽人社會的信息。所以說,如果每一個聽障者都要戴着這種手套,有可能導致沒有人再去學手語了,甚至就是說更少手語翻譯的存在。所以說結果可能是對於聽障社羣,反而是造成更大的傷害。然後相同,還有最近好像我也常常看到一種智能盲杖,把那個白色盲杖,傳統的已經大家用了很久的白色盲杖,裏面加上很多手機、 GPS 傳感器,然後很多東西。但是這個很大的問題是通常它需要電,需要充電、需要電池。但是盲人出門你要是走到一半沒有電,這個盲杖就廢了,或者說要是下雨的話呢?
吳少玫 01:09:58
這些都是完全出於一個炫耀,我覺得科技好炫,這些好東西放起來好酷,但是完全沒有從受衆羣體角度出發的設計。經常看到這種設計我就覺得很無語,並且每隔一年就會有一個新聞出來,又有人重新設計這個智能手套,又有人重新設計了這個新的盲杖,覺得他們背後還有一層邏輯,就是殘障羣體必須用這些各種各樣的裝備或者是設備變得更強,變得跟非殘障羣體一樣,這樣的話他們的問題就都解決了。
吳少玫 01:10:39
所以他這個默認還是說你要是看不到,你是缺失了,所以說,那你就多花點錢買一點更酷的裝備,但是這些花銷、這些努力又都全部完全單一的放在殘障者本身身上,與此同時就讓這個社會好像就可以變得不用做任何事,殘障者自己去花錢買裝備就好了,就可以非常自然地融入了。
吳少玫 01:11:09
但是現實不可能,這個融合應該是全社會的責任,並不僅僅是一個少數羣體,並且已經是弱勢,已經是通常很多情況下找工作甚至都會受到歧視,然後本身資源、金錢就會比較少的一個羣體的責任。主流社會不想要承擔責任,然後通過發明這些,通過給一些米油糧面,或者是給一些臨期餃子,或者是給一些新的裝備,我已經盡到責任了,我就沒有什麼別的需要做的,可以減輕罪惡感、內疚感,或者是享受做好事的快感,但是與此同時又把所有的最難的那一部分真正可以融入社會,最難的那一塊又單獨留給殘障羣體自己來處理,所以我覺得這是很不負責任的事。
明月 01:12:12
對,我覺得少玫這裏就提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無障礙到底是誰的責任?這中間也有一些觀念的轉變,就是所謂的醫療視角和社會視角。那以前很長一段時間就是醫療視角,就覺得有障礙的人,他是自己有問題,那他應該有這個責任來作爲被矯正的對象,不管是用什麼醫療的手段,還是用一些科技的手段,那你自己要去彌補你自己那個所謂的缺失的部分,這個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無法在環境裏面適應,是你自己要通過付出的一些成本來去讓自己適應這個環境。
明月 01:12:47
當然醫療的視角肯定也是有它的意義的,我們不能完全說否定它,因爲確實是有一些治療的需要。但是後來主流的觀點逐漸轉變到社會視角,就是說這個社會有責任讓各種各樣的人來融入,如果有些人融入不進來的話,那其實是整個環境的問題。應該改造環境和工具,讓更多的人可以在其中適應,在其中可以正常的生活,是可以去發展,去工作。不用說我非得給不能說話的人設計一個說話的手套,這種荒謬的東西,那這種東西它不只是被設計,而且剛纔少玫說是反覆被設計,他還是說我要來矯正你。這個不僅是居高臨下、自上而下,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傲慢,也很有侮辱性的。
紀尋 01:13:35
我自己想補充的一點的是,我覺得現在很多可能以技術爲主導的觀念,那他可能是想用一種非常簡單直接的方式去解決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而這樣的一種思維它是線性的,就好像說是你有一個問題,我就提供一個解決方案,解決完了以後你就可以和別人一樣。但是他沒有意識到殘障其實是在一個複雜的社會系統中,由不同的社會問題交叉而導致了一個更加複雜的社會問題,那這樣的一個問題可能包括你來自於什麼樣的社區,甚至於你來自於一個什麼樣的階層。然後還有一個是比如說現在我們來討論的技術的解決方案,那可能你前期的所有的社會經濟因素又影響到了你是否能夠有足夠的資源,從很早以前就開始去獲得可以支持你去發展的這樣的一些資源的等等一些資源分配的平等性的問題。殘障也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可能我們是需要更多的去考慮整個系統對這些殘障夥伴在不同層次的支持。
吳少玫 01:14:52
對,其實補充說一下,我覺得醫療視角,我對他有最大的反思最大的衝擊,其實也是從神經多元的角度出發。因爲口吃現在也就是慢慢研究發現它也是屬於神經多元性的一種,然後加上別的一些,比如說比較有名的自閉症譜系。一是它是人類多樣性的一部分,二是很多它是沒有辦法通過手術或者什麼去糾正的,並不是說它們會越變越糟,並不是一個會發展的疾病,而是當你的大腦裏面神經型就會有某一些構造,讓人與人之間想法做事、感知世界的方法不一樣。
吳少玫 01:15:40
所以說對於很多的神經多元團體,近幾年他們的倡導,還有加上對於這個現象的研究,也讓別的很多這些少數社羣朋友,或者是這些醫療界的專家也就意識到醫療模型的侷限性,有些東西就是沒有辦法醫好的。但是我覺得與此同時,我也並不是完全否認醫療系統它們的作用,因爲其實我本身也有認識,一是很多口吃者,像在美國,他們其實專業就是從事這種言語治療師的職業,所以他們本身就是這個醫療系統的一部分。二是其實也有很多進步主義的,非常支持這種社羣發展的醫生或是研究者,而且至少我個人的觀點是融入其實也是雙方的事,雙方都要伸出手。就是我也沒有完全說殘障社羣不應該做出努力,像我本身我也有繼續持續的去參加互助會,或者是參加言語治療的訓練。但是我的目的並不是讓我說話說的跟沒口吃的人一樣,而是讓我可以更加自如的口吃,可以讓我更加沒有恥感,更加有這種應得感的去口吃,去說出我想說的話,而非是就是把我想說的話咽回去,或者是說改變我要說的東西,讓我聽起來和別人一樣。然後與此同時,我覺得殘障社羣已經做得夠多了,我們真的已經花了很多努力。然後目前很多產品設計,特別是無障礙產品的設計也都是集中在讓殘障社羣學會用這個軟件,用這個產品,或者是說變得更好,學會更多的東西,就是我們已經做得夠多了,與此同時社會就做得太少,一個非常需要做的就是讓這個社會也伸出他的手,也要做多一點。
吳少玫 01:17:54
所以說我也沒有否定說殘障社羣自己也有我們的路要走,比如說像剛纔那個提到的殘障社羣內部裏面可能也會有一種鄙視鏈。像口吃者之間也沒有說我們口吃,所以說我們想法全都是一樣,就是有些口吃者也是想要說話說得更加流暢,我也可以理解。但我覺得重要的是你有這種自主性,可以做出你的選擇,而非是你覺得沒有選擇,你被逼着一定要說話流暢,或者是說你因爲恐懼一定要改變你說話的方式。
成爲“我”,即便是缺陷明顯的我,
爲什麼是最重要的事
時間節點
01:21:53 無條件地愛小孩之前,能不能先無條件地愛我自己?
01:24:43 通過把自己作爲研究對象,我和同事們產生了100%的信任
01:27:01 是誰接納?你自己接納,那你的父母真的接納嗎?
01:29:31 我爸爸去社交場合從來都是隻帶妹妹,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還有一個女兒
01:32:25 希望言語治療進醫保,個人提了三四年也沒回應的事,社羣幾個月就辦完了
01:34:05 環境和規則都是可以改變的,前提是你必須知道你是誰,必須找到你的同溫層
明月 01:18:36
我們這從這期節目一開頭到現在,其實一直都在強調一個非常非常重要,可能是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殘障社羣自己的主體性。我來決定我要什麼樣的東西,我來決定我要怎麼用它,而不是說之前有一種你給我什麼我就用什麼,我是一個這個東西的接受者和使用者,不管它好不好用,我覺得有就很好了。那肯定不是這樣子的,大家要從一個被動的接受者和使用者變成一個共創者。之前少玫舉的那個口吃社羣一起去設計一個視頻軟件,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那我記得在文獻裏面看到一個案例,就是針對言語障礙有一種輔助的溝通系統,應該是給大家一些詞,讓大家選來組成一句什麼話來讓自己來表達。但是言語障礙者就覺得我根本就沒有表達出我的意思。我看到一句話特別有意思,說當他想要罵髒話的時候,他根本就是無能爲力的。因爲他選擇非常非常有限,都是很規規矩矩的、很文明的那種話。並不是說大家就想要不文明還是怎麼樣的,但是其實在口頭表達的時候,肯定會有很多很多的那種不規則的,我臨時想出來的,甚至是不太符合語法那種表達規範的那樣的話,但是那就是最真實的自己。
明月 01:19:56
之前我們做那個口吃的稿子的時候,裏邊也有一句很打動我。就是少玫提到說口吃者想要用自己的方式來講話,即使是講得磕磕絆絆的,但是找到自己想要用的那個詞是非常重要的。其實很多口吃者已經學會了去僞裝自己,講話講得很流利,但是大家會覺得那個不是我,那我成爲了一個別人,並不是什麼成就。那這裏也想要談一下說這個身份認同的問題,爲什麼說哪怕自己已經學會了僞裝另一個看起來更“正常”的狀態,但是保持自己這種,會讓不太瞭解的人覺得有一些異常的狀態是非常重要的。
吳少玫 01:20:37
我個人其實是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我覺得也算是個人成長的過程,我的個人自我接納自我正視我的殘障有兩個很重大的因素,一個是我跟很多殘障者工作,我越跟很多殘障者工作,我覺得我就越可以正視殘障,因爲我就越發現其實我們大家和就是帶引號的正常人就沒有什麼不同。
吳少玫 01:21:04
我也我覺得先前可能因爲從小環境或者是社會原因,自己心裏對殘障或多或少也是有污名化,對口吃也是。因爲從小說話口吃的時候就會經常被家長或者是老師呵斥,就是說你有很嚴重的問題,你要好好想清楚,或者是你的說話方式不對,這種羞恥感,這種污名化,自己也是需要很多時間去消解它。
吳少玫 01:21:35
所以說跟別的殘障社羣合作,然後交流,特別是在一起工作,不僅僅是把他們當做殘障者,而是就是和他們一起寫程序,一起創造東西,真的有起到很大幫我對殘障去污名化的作用。然後另外一個很重大因素可能是有小孩,雖然我也沒有催生的意思,但是對我個人來說,我覺得有了孩子以後,對我有起到自己的一個反思的作用是,因爲當時看一些育兒書,然後書上就會想說,你要想清楚你想要你的小孩成爲一個什麼樣的人,然後當時我也在反思,OK,那我想要我的小孩成爲一個哪一種人呢?我就想說我想要他,可以很自我的活出他想要的生活,我也沒有想規定他想要過出哪種人生,我想要他有這種可以自己選擇自己想要過的人生,然後可以就是不受外界框框條條的限制。
吳少玫 01:22:41
然後當我有這種想法以後,我就開始反思爲什麼我覺得好像從小到大一直就都想要成爲一種別人,比如說程序員的話,好像就是想要被別人認爲我跟男的程序員一樣強,或者是說話的時候想要被別人認爲我和沒有口吃的人一樣說得好,反正就是都是想要拿別人作爲我的標準,想要去被認可成一種和我完全不一樣的人,所以我就意識到其實這個過程是也對於自己其實上是一個很大的消耗和很大的否定。
吳少玫 01:23:21
所以可能因爲這個,我就對我孩子,因爲我對他們的愛或是期待,就是讓他們可以真實地活出他們內心,可以照着他們自己的天性生活,然後可以做出他們自己想要的選擇。與此同時我覺得我也在問我自己說,我對我的小孩可不可以無條件地去愛?我也在想說,那我能不能先無條件地去愛我自己呢?然後我就意識到我好像也沒有辦法,我好像從來就沒有感受到,或者是很少感受到這種無條件地被愛或被接納,我自己也不太瞭解怎麼樣無條件地去愛自己。
吳少玫 01:24:05
所以我想也從自身開始,先試着去無條件地接納自己,無條件地去愛自己,然後在這個過程中也鍛煉出無條件去愛我們下一代,或者是愛身邊我們在乎的人的能力。所以說我自己反思這兩個因素起到了很大的讓我接納口吃的作用,讓我終於“口吃出櫃”。讓我參加口吃互助會,從一開始,就是不說話,到慢慢的參加各種論壇,然後到我去年寫了一篇自田野,把我自己作爲口吃的經歷寫成一篇論文告諸天下,但是我覺得在這過程中也是非常治癒的,我覺得也讓我正視到一些很多我先前很害怕的東西,並且至少讓我的同事讀過這篇論文,他們也在觀察我,也把他們的觀察寫下,我覺得也讓我和我的同事產生了一種很大的信任,覺得可以很放心、很真實地面對他們。
吳少玫 01:25:11
其實老實說,以前我在我同事面前,雖然我告訴他們我有口吃,我經常其實還是不太放心他們對我口吃的反應,他們心裏會不會對我有一些什麼想法。但是通過跟大家一起,以我作爲一個研究對象,大家很多討論,我現在真的是 100% 的信任我的同事,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寶貴的事,我先前從來沒有過。
明月 01:25:40
今天咱們雖然聊的是殘障的問題,但是其實好多問題絕對不僅僅是殘障的問題。上面剛纔講這些關於接納自我的整個的心路歷程,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會有類似的體驗,那可能殘障這種特徵更能幫助人走過這個體驗的時候,可能是某種助力?不知道這麼講好不好。
紀尋 01:26:03
我覺得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可能也是分階段的,當我來做殘障的工作的時候,我肯定是一個經常在公開場合介紹我自己,也會用殘障的身份來介紹我自己的這樣的一個人,那我可能會發現在我們社羣裏的很多的夥伴中,他並不希望讓別人發現他有殘障,無論他的殘障是顯性的還是隱性的。
紀尋 01:26:33
如果是顯性的殘障,他可能願意在網絡空間裏隱藏自己,然後裝作跟別人一樣。那如果說是隱性的,可能就像少玫以前的那一段經歷,就是我要盡我最大的方法去隱藏我自己的殘障,讓我顯得跟別人一樣,並且在一個主流的市場環境下去跟別人競爭。然後我要做得更好,甚至於最好。
紀尋 01:27:01
遇到這樣的一些夥伴,其實我自己是沒有辦法理解的,我好像是很早之前就接納我自己是一個殘障者。這可能是跟我自己本身的殘障程度比較重有關,然後又是顯性的,所以我沒有辦法做任何的隱藏。我可能就自然而然的在很多種場合需要去跟別人解釋,因爲我的這樣一個殘障,我要坐輪椅,所以我需要這裏怎樣,或者說對不起,我沒有辦法在這個會議中用很快的打字速度來記錄,所以請某人幫我記錄一下,所以我自然而然的接受那個過程。
紀尋 01:27:40
但是對於很多處於中間狀態的人來說的話,他可能還是處在一個我希望有種方法去隱藏這樣的一個狀態,我就不希望別人發現我跟其他人有什麼不一樣的一個狀態,那即便我有,我也希望盡我最大的努力去彌補。我覺得這好像是我在經歷的對於殘障的認知的第一個階段。然後第二個階段我發現,這個議題可能比我想象的更加的複雜,就是關於接納。是誰接納?你自己接納,那你的父母真的接納了嗎?我去參加很多的小組討論,我開始回溯大家的人生經歷和家庭經驗。我覺得我遇到了很多,可能我看到了以後會讓我痛哭流淚的經歷。
紀尋 01:28:29
我記得非常清楚的是我們的社羣裏有一個夥伴,廣州的一個殘障的女孩,可能跟我是一樣的疾病,也是比較嚴重。她就講了自己人生中的一個片段,她說在廣東那邊,可能因爲家庭一些宗族關係比較多,他們經常有這種家族的活動。她說每當有這種活動的時候,我爸爸媽媽從來都不帶我出席,就好像我家庭裏沒有這樣的一個人存在一樣。雖然我們都覺得她爸爸媽媽其實對她已經非常好了,就是第一照顧得很周到,然後可能也帶她經常去旅遊,但可能這侷限於她的一個小的家庭。當親戚關係的網絡放大的時候,你會發現她的家庭可能在以一種方式去隱藏,而她自己可能也在過程之中去隱匿自己。
紀尋 01:29:31
而這樣的故事其實也發生在我自己的成長經歷中,因爲我還有一個妹妹,然後我突然回想起來了,我小的時候,我爸爸去參加無論是婚禮還是生日宴會,或者同事的一些百日宴這些社交場合,他從來都是帶我妹妹而不是帶我。我覺得甚至於他的很多同事可能只知道他有一個女兒,並不知道他的大女兒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態。所以我覺得可能當我一部分覺得我自己可以接納的時候,但有另外一方面你是沒有辦法和自己的人生和解,那就是你沒有辦法否認,即便在外人看來我是一個受到家庭支持比較多的人,但是我依然是沒有被這個家庭所接受的。
紀尋 01:30:24
這可能是讓我在成年的過程之中非常痛苦的一部分,甚至於也爲我帶來過精神上的困擾,這樣的一個傷痛也是你要花一生去治癒的。只是我在過去沒有想這些問題的時候,是以一種非常硬殼的態度去面對這個世界,你讓你自己顯得很堅強、很堅毅,其實是打一個殼子把自己保護起來,而並不想讓這些很脆弱的地方讓別人知道,但是實際上它就是真真實實發生在你的人生裏的。
吳少玫 01:31:08
紀尋你說的我也很感慨,因爲像我是差不多完成對口吃的自我接納,但是我的家人或是以前的朋友,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別的一起工作的人可能也沒有完全接納。父母經常還是說我沒有口吃,只不過是我緊張,或者是因爲我小的時候缺少鍛鍊或者是害羞,我就是在現在還是要繼續甚至跟我父母解釋這件事,但是我覺得可能我也沒有必要。然後在工作的時候會,噢對,比如說最近我在開一個國際會議,我覺得可能或多或少大家覺得你有口吃,爲什麼你還要上來發言?然後你講的時間也比別人多。我以前有要求說我可不可以發言更多時間,一半的時候就會被說不可以,因爲這樣的話不公平,這樣的話別人就是感覺每個人發言時間必須要一樣,所以我覺得雖然好像在美國學術環境好像已經非常比較開放,比較包容,但是還是會,我覺得也沒有完全就接納。
吳少玫 01:32:25
但是與此同時我覺得其實我還是不後悔我公開的宣揚我是口吃者的身份,因爲我覺得這其中除了對我自身有益,其實可能還有一些或多或少的一個環境的意義,一個社會的意義。
吳少玫 01:32:45
就比如說我在臉書的時候,當我開始參加臉書口吃員工互助會的時候,當時臉書的醫保沒有包括口吃,就是沒有包括言語治療的費用。我就跟別的口吃同事說了一下,然後大家就都覺得,唉,這個很不對。所以我們大家一起提了一個倡議,然後半年以後他們就改變了這個醫保。但是其實相同的倡議,我先前在我沒有公開我自己口吃者身份的時候,跟我們的人力資源提了很久,已經提了三四年了,因爲我一直有在自費做這些治療,最後都沒有得到回應。基本上回應就是說只有跟你工作相關的才能夠得到醫保。這個就很難去證明,因爲我的工作主要就是就科研。但是後來我跟別的口吃者聊了一下以後,就 6 個月我們就完成了他的這個政策的改變。我就覺得,哇,這個就是因爲我正視了我是口吃者的身份,我才找到了我的社羣,然後我才獲得了這種比我單槍匹馬大得多的力量,然後有一個這種結構性的改變。
吳少玫 01:34:05
去年我有遇到一個紐約的口吃者,他和我說他的公司就是當他聽說臉書改了臉書的員工的醫保以後,他去和他的公司談,然後他們公司也同意加入對於那個言語治療的覆蓋。我就覺得這個就是可以慢慢的有一個漣漪效應。這是因爲我們敢於站出來,敢於發出聲音纔會發生的,並不是公司或者是說社會自發就是出於善心給的,都是我們自己倡導出來,自己抗爭出來的。但是你要發聲,你要去倡導,你必須要知道你是誰,必須要找到你的社區,你的同溫層,我覺得這個是算是鼓勵我去每次公開告知我是口吃,或者是去參加這些會議然後發言的一個最大的動力。
吳少玫 01:35:06
其實我是非常害怕的,我手裏都是冒着冷汗,我身體還是有一些應激反應的,但是我覺得對我來說最大的理由並不是說個人,是說我覺得這些學術會議應該聽到更多口吃者的聲音。因爲在我發言之前,我從來沒有聽到任何口吃者在這種國際級的學術會議上作出演講,或者是這樣沒有公開的口吃者的演講,所以我覺得當我在臺上非常費力地口吃,說不定以後有一個學生或者是年輕人他也有口吃,下一次他就會有勇氣走上臺去發出他的聲音。其實像我先前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是可以隱藏的,隱藏以後其實也讓我有一種安全感,但我現在我覺得我就可以放棄那一類隱藏的便利,因爲我們站出來可能可以對除了自己,但對於別人、對社羣、對於社會可能都會有更大的意義。
明月 01:36:12
嗯,這也是我們這期節目想要去做到的一個小小的努力,就是至少讓殘障者自己的聲音能夠真正的被大家聽到,社羣的力量真的非常重要,有了社羣之後,大家不再是孤單的一個人去對抗整個社會觀念的問題。大家一起發聲纔有可能去改變社會的觀念,以及改變那些結構性的問題。
明月 01:36:36
那殘障者的需求不是說要把每一個人矯正成一個其實有障礙的環境裏面規定的特別標準的人,而是要讓這個環境來適應每一個不同的人的需求,因爲人跟人肯定就是不一樣的,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一樣,所以我覺得這是在更大範圍的意義上來講,對所有的人都非常重要的事情,絕對不只是對殘障羣體。
明月 01:37:00
少玫之前在紀尋的活動上面引用了一句話,我覺得特別好,所以我這裏想要再念一下,也是一個殘障者說的,她說“我不僅是想要在別人的桌子上獲得一個座位,我是想要跟我的殘障夥伴一起去構建一個比桌子更宏大的東西”,我覺得這也就是大家都一起在努力的事情。其實這個話題非常非常的大,我們今天聊的只是裏邊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後面我們可能再聊一次關於社羣如何讓所有的殘障者有更大的自主性,能夠走出去,能工作,能更決定自己的生活是什麼樣子。那今天只能先聊到這裏了,非常非常感謝少玫和紀尋特別真誠的分享。謝謝。
吳少玫 01:37:44
非常感謝明月老師。
紀尋 01:37:46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