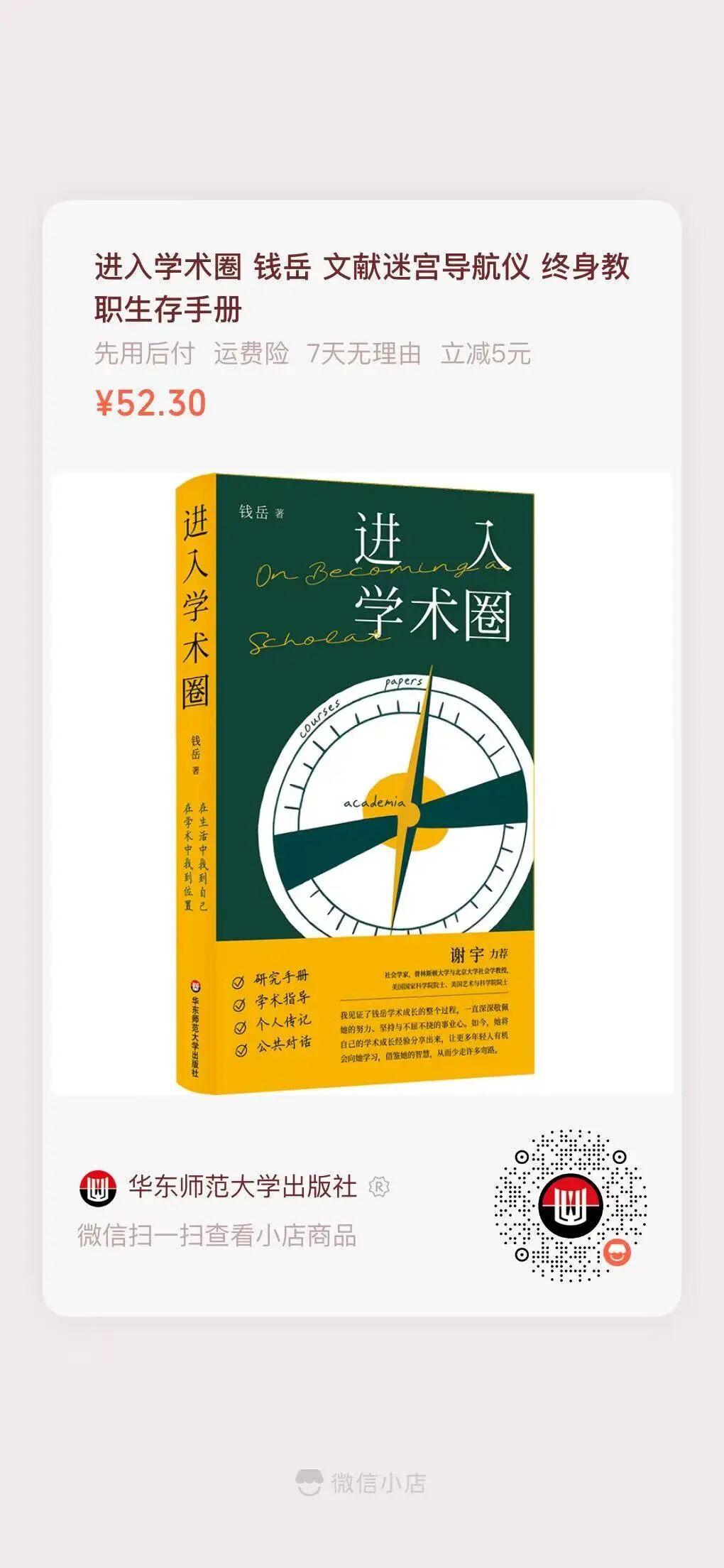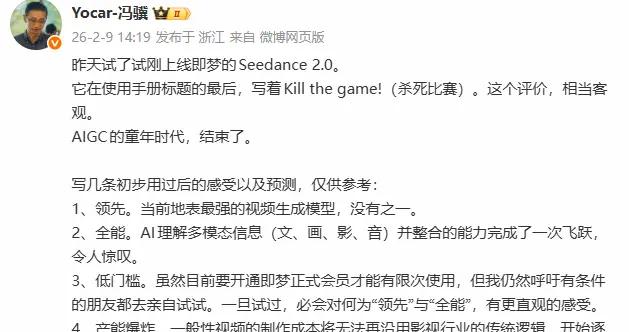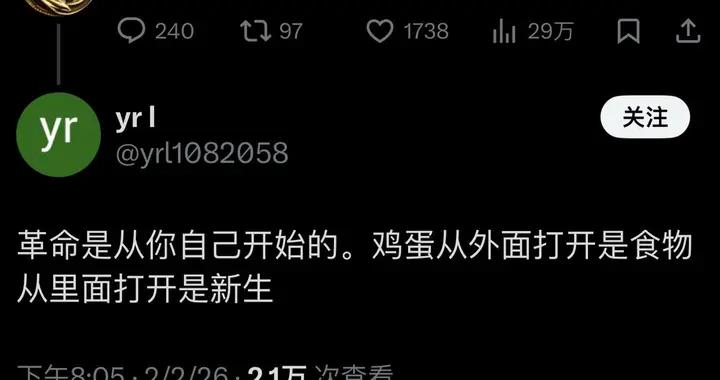非升即走壓力之下,“青椒”如何面對學術內卷?

今天想給大家推薦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錢嶽的新書《進入學術圈》,這不是一本教人如何“成功留下來”的經驗手冊。它並不試圖告訴我們怎樣多發論文、提高基金申請成功率,或怎樣在評審體系中佔據優勢位置。相反,這本書從一開始就直面一個更基礎、卻常被忽略的問題:當一個人真正進入學術圈之後,如何與這套高度競爭、不確定、長期承壓的體制相處。
圍繞這一問題,作者錢嶽以自己讀博以來十五年的學術經歷爲線索,系統梳理了學術道路上的關鍵環節——從科研訓練、論文寫作、求職與“非升即走”,到心態調整、身體邊界與長期發展的可能性。書中既呈現了學術研究的艱辛與樂趣,也不迴避現實制度帶來的焦慮、內卷與消耗,並嘗試把這些個人體驗放回學術體制與評價體系中理解。
這本書既寫“怎麼做研究”,也寫“如何生活”。它關心的不是如何在競爭中勝出,而是如何在現實約束之下,找到一種相對可持續的工作方式,把學術熱情轉化爲長期可行的行動,而不是被績效和比較不斷侵蝕。
在學術界工作,內卷已成爲一個無法避開的現象。國內外“非升即走”的體制,讓很多博士生和青年教師壓力非常大。博士生需要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才能畢業,要在國際或國內一流期刊上發表相當數量的論文才可能找到教職。而青年教師要在頂刊發表論文以及要拿國家級或省級的項目基金纔可能晉升爲有終身教職的副教授。在這樣的環境下,人不僅可能變得浮躁,而且常常陷入無盡的擔憂之中。在這一章,我來分享一些對應對學術內卷的感想。如果讀者能夠想通自己在內卷的環境下如何自處和享受做研究的樂趣,將會對心理健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01 放棄對KPI的執念
在一個講究績效、生活節奏很快的社會,很多人都高度重視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如果做學術的人也總是希望有立竿見影的KPI,可能會經常失望,那麼心理健康狀況自然堪憂。斯坦福大學的周雪光老師在受邀出席北京大學的一次活動時分享過一個例子:“我帶過一個博士生,是北大中文系本科畢業的。他讀社會學PhD一段時間後告訴我,他不想讀博士了。他說,他更喜歡那種每天結束時就可以看到一天成果的工作,而研究工作需要很長週期才能看到結果。他後來轉到商學院讀了MBA後到公司工作了。我雖然爲他惋惜,但也支持他的這個選擇。”(周雪光、孫飛宇,2018)
周雪光老師分享的不是個例。我有時候指導學生,也發現有的學生不願意“浪費時間”,做事情要隨時看到KPI。但是做學術,很多時候可能你花了很多時間,最後卻要從頭再來。在這個過程中,老師可能並不一定指導得了。我們走的每一步彎路,都是成長。很多研究的想法最終需要自己去琢磨。我讀博時,有一次清理數據要抓狂了,跟統計分析能力出類拔萃的小夥伴哭訴說“我想找個角落邊畫圈圈邊哭”。沒想到小夥伴說她也常常有這種感覺。但是哭過之後繼續找解法,大概就是研究者的日常吧。即使現在我成了一個更成熟、更有經驗的研究者,也不代表我每天的KPI都很高。比如,我2022年開始做的一個項目,數據分析做了三個多月,一直找不到故事線。本來只用一年的數據,後來加到四年,然後又把十九年的數據全部整合了。一共三個版本,每個版本近五百個職業編碼,我逐條整合,眼睛都看花了。在這個過程中,我跟合作者每週定期見面討論,一遍遍地推翻之前的分析,一起討論如何能夠更具創新性地使用和整合數據來回答研究問題、提出新的研究問題、驗證基於理論提出的研究假設和潛在機制。雖然看似做了很多無用功,但那些“無用功”激發了靈感,爲之後進一步的探索打下了地基。而基於這個項目寫出來的論文,經過三輪同行評審之後,直到2025年暑假才正式被學術期刊錄用。
如果我們堅持訓練自己深度反思、總結教訓和舉一反三的能力,那麼我們犯過的錯誤和走過的彎路都有它們的意義。讀博和做科研是“長線投資”的過程,不能每天都盯着KPI(比如總是想着,我今天工作了十個小時,我明天就能看到十個小時的產出)。論文寫了很多年,被拒了好多次,每一次都從頭再來——這在學術界“打怪升級”中再常見不過。如果你覺得需要每天檢查KPI來保持動力的話,那麼可能對於自己“是否讀博”“是否在學術界工作”等問題要三思。如果你決定在學術界“闖關”,爲了你的心理健康,或許應該把眼光放長,而非盯着每天的KPI,將其作爲判斷自己工作效率和績效的指標。
02 被卷和主動卷的區別
我以前跟心理諮詢師提到過,我對於自己是否能夠拿到終身教職感到擔憂。我是一個很容易焦慮的人,而且凡事喜歡往最壞的方面想,同時我又非常追求安全和穩定的感覺。因此,如果系主任跟我說一般每年發表兩篇一作的論文就差不多達到評副教授的標準,我會在心裏默默給自己定下每年發表四篇論文的目標。因爲只有我的表現大大超過了普遍的標準,我纔對自己成功評上終身教職有萬無一失的信心。心理諮詢師問我:“你有沒有想過,你這樣做,其實是在加劇學術界的毒性和內卷呢?因爲你發表多了,別人也被迫覺得壓力很大,不得不多發幾篇文章,以免自己掉隊太多。”我當時一下子愣住了,我從來沒想過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可能會加劇學術界的毒性。我的這一經歷讓我想到了網上關於主動卷和被卷的區別的討論。
一篇微信公衆號文章裏提到一位北京大學的同學說:“現在我們好像都非常反對這種內卷的文化,甚至說到誰特別努力上進,主動完成很多任務,就會被冠上‘卷王’的稱號,非常招人恨。但是明明有些人就是自己想要上進而已,也沒想逼着別人和自己一起卷,只想認認真真把事情做好,怎麼就成了一種罪過呢?”(夏白鹿、張昕,2023)我非常理解這位同學的困惑,在現在競爭極大的環境下,努力工作的人彷彿僅僅只是做自己,就可以讓評選和晉升的標準水漲船高,加大同輩們感到的競爭壓力。但是,我自己不同意“主動卷”的這種說法,因爲這個詞有點污名化被內在回報驅動而努力工作的人。
很多學者是真心對研究非常感興趣,所以長時間的工作對他們來說並不是負擔。我以前跟一位大牛合作一個項目時,他已經是頂級學校的傑出教授了。照理說,發論文對他來說已經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了,他的事業、名氣、影響力和學術貢獻也不需要通過多發一篇論文或多拿一個項目基金來證明。但是他工作非常努力,常常跨時區開會,有時候他的當地時間已經是晚上11點了,他還跟學生或合作者開組會。學生在展示自己數據分析的初步結果時,他總是可以非常敏銳地問出至關重要的問題。在學生展示之後,他可以給出一針見血的修改建議。每次開會的時候,我都特別佩服那位知名學者,因爲他真的精力極其旺盛。其他人晚上11點都昏昏欲睡或頭腦混沌,但他還可以高效地開會或工作。不光是晚上,在週末和節假日開會對他來說也很常見。他曾經跟我們說過:“如果按我的工作時間來說,我的薪酬遠遠低估了我真正的工作量。但是我不在乎,因爲我工作不是爲了錢,我喜歡工作,工作讓我快樂。”這位知名學者算不算“主動卷”?他確實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但是我很少看到他對學生施壓,也很少把自己的工作習慣和時長強加到學生或合作者身上。如果學生需要他的支持,他會抽出時間認真地給予指導,他也鼓勵學生有自己的生活、愛好和人生計劃。類似這種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其實已經不在乎卷不捲了,對他們而言,他們只是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當一個人專注當下,往往可以獲得心流體驗。比如我發現,當我覺得焦慮、煩躁的時候,試着靜下心來分析數據、寫論文、改論文,反而能讓我暫時忘卻煩惱並沉浸於最純粹的快樂中。從我自己的經驗來看,與其一直擔心數年之後是否可以拿到終身教職或評上正教授,不如享受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的過程。能走上學術這條路,主要是因爲我真的還挺喜歡做科研的。在讀論文和寫論文的時候,我可以忘記喫飯、忘記時間,很投入地做這些事情。比如說改論文的時候,可能等我發現時,已經改了五個小時了。改完之後,我是覺得特別高興的。因爲在改論文時,我沒有想別的事情,我不去想這個論文到底會不會被錄用,我只是想當我花了五個小時改論文,我的論文是不是更好了一點。這個匠心創造(crafting)的過程本身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想,對這個世界上絕大部分的人來說,生活還是大於學術的,追求學術不應該以犧牲身心健康、疏遠家人朋友爲代價。對看上去“主動卷”的人來說,如果他們覺得這種工作強度沒有影響他們的生活質量、身體健康或親密關係,可以維持一個自己比較滿意的平衡,那成爲努力高產的人沒什麼錯。當然了,對於那種可以心無旁騖地投入工作的人,我們也需要問問,他們是不是把生活的其他一些責任轉嫁到了自己身邊的人的身上?如果你屬於高產努力的人,也可以反思一下你的生活方式,與你在乎的人溝通一下,看看你的時間安排得以實現,是不是因爲你身邊的人做出了某種犧牲。相反,如果一個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同伴的壓力或職場的競爭,感到自己不得不努力工作拼業績,那麼可以想象,這個人會承受非常大的壓力,非常容易感到焦慮和負面情緒。如果一個人每天都覺得做科研很煎熬,完全是因爲外在的壓力而工作,頻繁地因爲“被卷”而感到窒息,或許那個人也應該反思一下學術道路是不是真的適合自己。
我還想補充的是,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看,主動卷和被卷,很多時候關鍵不在於人,而在於體制。比如,國外大部分的學校,其“非升即走”的崗位招了學者之後,主要的目的還是支持他們,希望最大程度地幫助他們獲得成功。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同事曾經說過:“如果我們在幾百個候選人裏面選擇並招聘了一個人,但是最後那個人沒有拿到終身教職,那麼這不是那個人的過失,而是我們整個系的過失,因爲我們沒有提供足夠的支持,來讓一個優秀的人展現才華和獲得成功。”這些學校大多把招聘“非升即走”崗位的青年教師作爲一種長期的投資,希望能給他們提供職業發展的土壤,助力他們做出創新性研究。所以,學校普遍明白有些好的研究、風險高的研究花的時間比較長,也明白研究的質量並不完全由期刊的排名決定。同時,在職稱評定的時候,國外的學校不會將同事之間互相比較。一個人要拿到終身教職,只需要在某個領域做得足夠好,而不需要玩荒野生存的遊戲,去打敗系裏面或學校裏面的其他同輩同事才能晉升。而且,很多學校明白,對於“優秀的學者”的定義是很多元的:有的人可能發表數量比較少,但是每一篇都非常有影響力,開創了新的領域;有的人甚至可能沒發表幾篇學術期刊的論文,而是著書,其學術作品通過有影響力的大學出版社發行;而對項目基金來說,那更像中彩票一樣,中了當然更好,沒中的話也不會成爲對一個人的學術水平或貢獻的徹底否定。所有的這些體制設計,都可以讓還在“非升即走”崗位上的學者有更多的安全感,也感覺自己的才華和能力被珍惜和重視,因此他們可以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集中在如何做出有影響力的研究上,而非一味地加入內卷大軍去努力滿足職稱評定過程中時刻在變的標準。希望我們的學術體制能夠將支持青年學者看作對實現科研創新的長遠投資,能夠倡導用更多元的方式去定義學術成功,能夠鼓勵學者之間的良性合作而非惡性競爭。也希望學者不需要迫於競爭和生存的壓力加入內卷大軍,希望更多的人能找到學術的樂趣,無愧於心地努力工作。
03 傾聽身體的信號
近幾年高校青年教師因病早逝的新聞頻發,讓社會大衆對學術界的“內卷競賽”以及高校教師的過勞和困境有了更多的關注。我也跟學術界的朋友一起討論和反省過,在高強度的工作和評職稱的壓力下,再加上把學術工作當作天職的使命感,讓我們常常不自知地“剝削”和透支自己的身體。我們甚至習慣了壓抑對身體的感覺,一直忽略身體的信號,有時候等我們發現時健康的損傷已經比較嚴重了。
比如幾年前,我在申請一個國家項目的時候,每天從早到晚地寫申請,精神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寫項目申請期間,我的身體沒啥異樣。但是交了項目申請之後,我感覺身體的骨頭好像碎成了一塊一塊的,坐骨神經和背部下方都隱隱作痛。後來我通過鍼灸、按摩、整骨治療了好長時間,才慢慢恢復。還有一次,我從北美去亞洲出差。在飛機上睡覺,下飛機就開啓工作日程。完全沒有調時差,強行按照亞洲時間,每天精力充沛(hyper-energetic)地演講開會連軸轉。後來在機場候機準備回家時,我就感覺嗓子有點疼了。等回到北美,立刻嚴重感冒而且失聲了,在牀上躺了好幾天才恢復一些精力。
我想,很多學術界的朋友一定跟我一樣,因爲長期過度工作(overwork),經常忽略或下意識地壓抑自己身體的信號。比如,我們一直要求自己平衡生活、家庭、育兒以及貪婪的工作(greedy work)
,包括回不完的郵件,一個接一個的項目、一篇接一篇的論文……很多時候,我們的身體已經超載了。此時,學會“做減法”就顯得格外重要。不重要的旅行,能取消就取消;不重要的聚會,能不去就不去;不重要的工作或機會,即使看上去很光鮮,能放棄就放棄。按時作息,保命要緊。內卷的環境和競爭的壓力,對我們的影響不言而喻。但身體健康是一切的本錢,是我們能夠產出學術成果的前提條件。學會傾聽並且重視身體的信號,我們才能可持續性地工作和生活。
參考文獻:
[1] 周雪光、孫飛宇,2018,《學記|周雪光老師“學記”紀要》,元培學學學,
https://mp.weixin.qq.com/s/9tNH40Wm6QbuL4-91-BE3g。[2] 夏白鹿、張昕,2023,《主動卷和被動卷》,Dr昕理學,
https://mp.weixin.qq.com/s/bI-_-sSsbA1rUV9sR_0k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