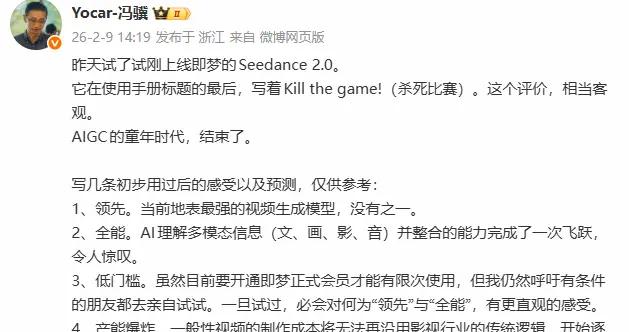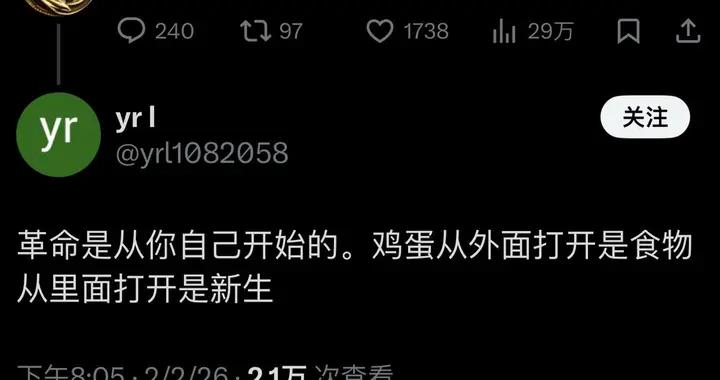真正決定中國科學未來的不是錢,而是人

2025年11月9日,“科學人才與中國科學的崛起”——“知識分子”十週年圓桌論壇。
2025年11月9日,“科學人才與中國科學的崛起”——“知識分子”十週年論壇在北京中關村舉行。
過去十年,是中國科學加速崛起的十年,無論科研投入、平臺建設、論文產出還是國際影響力,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科學人才選擇回國。此次論壇的圓桌討論中,幾位知名學者圍繞“科學的未來從‘人’開始:怎樣建設新型科研文化”,展開了討論和碰撞。
圓桌主持人:
周忠和 “知識分子”總編輯、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所研究員
圓桌嘉賓:
陳十一 寧波東方理工大學校長
金之鈞 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北京大學能源研究院院長
饒 毅 北京大學終身講席教授
張 崢 香港大學教授、港滬創研院首席科學家
以下是圓桌討論實錄,文字經過編輯。
周忠和:我們圓桌論壇的主題是——“科學的未來從‘人’開始:怎樣建設新型科研文化?”科學的發展離不開制度、文化與環境的共同支撐,但最核心的永遠是“人”。今天的中國,科研競爭已經從引進多少人才,轉向如何讓人才成長、留下,並做出原創性成果。無論是大學、科研院所,還是企業研發體系,大家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怎樣建設一個真正以人爲本、健康的科研生態?
今天我們請到了幾位在不同領域深耕多年的嘉賓,共同探討:科學家需要怎樣的環境?我們又該如何留住最具創造力的人?
第一個問題是“爲何回來?”過去幾年,越來越多科學家選擇回到中國。中國科學家“迴流”的動力究竟來自什麼?是科研資源、制度環境,還是歸屬感?您認爲哪一點最重要?
陳十一:1998年,我在北大任教,全職回國是在2005年,到北大工學院擔任創院院長。爲什麼回來?首先是因爲北大要建工學院,對我盛情相邀。當時我在美國已經是教授、系主任,也惦記着回國做點事。這是一份樸素的感情——我從北大畢業,母校希望我回來,我也很願意。當時林建華在北大當常務副校長,我們以前是北大同學,彼此很信任。能夠回到自己喜歡的地方、周邊有信任的人,這是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
第二個原因是平臺。在美國我雖然系主任做得很好,但總感覺平臺有限。現在很多人回國,感覺國內機會比國外好,那時候我就看出來機會了。不回國的話,我不相信自己能走到“東南西北”——我當過北大副校長,南方科技大學校長,參與創辦西湖大學,創辦寧波東方理工大學,並擔任首任校長。在我看來,國內最重要的優勢是平臺。
2005年到現在剛好20年,我在20年前的預見今天顯現出來了:要行動就早行動,要有前瞻性的眼光。
周忠和:您把“歸屬感”放在第一位,把平臺、機遇放在第二位。其實也許兩者同樣重要。我們請金老師談談。
金之鈞:我是1993年回國的。當時去的是前蘇聯,回來就是俄羅斯,回來第一個樸素的感情是回報。我還感到中國改革開放形勢應該是越來越好,對未來的判斷,感覺回國未必就發展得不好。我也做了準備,實在是幹不贏,回報回報祖國再走也可以。但是回來以後就沒有再“走出去”,就一直在國內發展下去了。
周忠和:金老師回答得非常實在。不過我發現你們兩位講的更多是個人經歷,而我問的是中國科學家整體的“迴流”現象。
饒毅:我們看一下世界,美國科學怎麼崛起的,跟人才聚集的關係非常大。中國人一般認爲美國從來都偉大,美國科學從來都很好,這完全是誤解。1940年之前,美國科學在世界上是非常不重要的,除了邁克爾遜-莫雷測光速實驗突出以外,生物有摩爾根,其他大部分的學術是很差的。
20世紀本來應該由德國科學技術撐起來,成爲“德國世紀”,結果德國發“精神病”,自己把自己廢了,一大批人才因爲二戰跑到美國。美國的國家崛起,其中很重要的成分是科學人才在美國聚集,當時沒有什麼人因爲“歸屬感”去美國。除了家鄉在美國的奧本海默,他在歐洲不能主導任何學科,回到美國把事情做到了極致,大部分人去美國都是被迫,但這種“被迫”形成了巨大的洪流。美國崛起與科學人才關係極大。
目前我們中國,全國從上到下、從裏到外,絕大部分人都相信,國家的崛起和科學人才有關。這是很寶貴的,對我國的科學崛起很重要。
同時我們大家現在才知道,美國社會從來不認爲科學家重要,要不然不可能對着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隨意一個一個耳光扇過去。美國處於一個很危險的境地,但是大部分華人還沒有看見這一點。
與世界歷史的經驗教訓對比,是一個很有趣的方面。我們能看見美國當時崛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科學以及科學所需要的人才,但美國社會並未普遍真正看見。美國的精英當然看見了,但是它的文化裏面沒有這一點。
張崢:我用八個字來總結一個公式,就是“趨利避害、家國情懷”。家國情懷是放在桌面上講的,趨利避害(一般)是關起門來講的。饒毅剛纔講的,當時德國或者歐洲的科學家到美國去,是趨利避害,而前面兩位老師(陳十一、金之鈞)講得更多的是家國情懷。
我們做理工科的人喜歡把一個問題拆成獨立的變量,“家國情懷”“趨利避害”。隨着時代的變化,這兩個因素的權重會不一樣。現在的年輕人開始回國,也是因爲國內發展起來了,有很多做科研或者創業的機會;現在的形勢下這兩個變量也相對更不獨立,相關性更強。
周忠和:在人才引進招聘方面,各位嘉賓都很有經驗和觀察,你們都當過校長或者院長,除了你們自己非常有魅力、個人的能力、影響力之外,主要靠什麼來吸引人才?
先從陳十一老師開始,寧波東方理工大學已經匯聚了100多位創校教授,爲什麼能夠吸引到一批世界頂尖的學者?
陳十一:一所高校靠什麼吸引人才?我在南方科技大學,吸引的主要是國外人才,而不是國內人才。我和國內很多校長都認識,也認同在國內高校“挖人”不是健康的生態,所以邀請國外人才很自然。
還有各方面的因素。第一個因素是學術環境,讓大家感覺在中國會比在美國幹得還好。剛纔魯白講了一句話,我其實一直是這麼做的:hire the best people and leave them alone(把最好的人招聘來,然後放手讓他們幹),這也是我在美國幹了二十年,學到的大學獨立研究的核心價值觀。不是給他很多KPI,要求做這兒做那兒,研究經費怎麼花。優秀的科學家,不管是做基礎研究,還是做產業應用,都要激發內在的創造力。
第二個因素是,我當時在南方科技大學膽子比較大,深圳市政府也提供了比較多的經費支持,我們給歸國人才匹配了相當於他們在國外的薪酬,2015年開始,我們就招聘了一批國外回來的人。當然,現在這樣做已經不稀奇了。
除了家國情懷,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家庭,要給他們體面的生活、好的工作環境。
東方理工100名PI中,90多名都是從國外回來的。吸引海外人才全職歸國,首先要有一個好平臺,能在這裏成長,有機會成爲世界著名科學家;第二,有健康的身體、幸福的工作生活環境,就這點而言,寧波是不錯的,房子僅3萬元一平方米,我們能讓大家安居樂業,安心回來做科研。
周忠和:謝謝!金老師,你這幾年創立了北京大學能源研究院,“雙碳”是一個非常熱門的領域,又有北京大學這塊金字招牌,引進人才是不是相對容易一點?
金之鈞:你說得很對,我在職業生涯當中變了三個單位,不同的平臺,吸引人才的主要因素也是不一樣的。
北京大學主要是平臺大,我們面臨的競爭是跟一些世界知名大學的競爭。我2020年組建能源研究院以來,從國外吸引了四位助理教授回國,應該說沒有費太大的勁,這是我在引進人才當中最容易的引進。但是對他們的培養卻應該是最困難的,因爲他們都比較年輕。
我想着首先是“頂天”,儘量讓他們多接觸學科前沿,在國際上更加活躍,所以每年都支持他們出國,跟國際上保持密切的聯繫。第二點,儘量把他們帶得要“落地”,帶到企業當中去,帶到地方政府當中去,所以他們這四位都先後在油田或者在鄂爾多斯地區開展了相關的業務工作,這對他們的成長是至關重要的。第三點,我到北大來給我一個重要的任務,北大要做有組織的科研,所以我們拿到了地方的經費、拿到了中石油的經費。在安排他們的工作時,有組織的科研怎麼保持他們的個性,讓他們個性更好地成長,這是我特別小心、特別關注的事情。
我來北大之前,在中國石化工作,擔任勘探開發研究院的院長。我們先後引進了5位行業內頂尖級的科學家到研究院來工作,其中有3位是外國朋友,有2位是外籍的華人。這個引進就比較費勁,靠的什麼呢?靠的是兩方面,一方面是創造一種幹事業的環境,第二個是薪酬待遇,這些人的引進完全按照國際標準,並且全部都是用外匯來支付的。他們在國外是什麼標準,我們基本上比國外的工資還要再加一點,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另外一點,來了以後,感到比原單位有更好的工作環境。即便是這樣,最後3位外國朋友都先後離開了我們這個研究院,在離開的時候我都要跟他們喫頓飯、長談一次。
周忠和:金老師,他們爲什麼走了?是錢給少了嗎?
金之鈞:也不是錢少,最主要還是文化的不適應,他們先後把夫人也帶過來了,最後跟我講說在這裏工作三年就沒朋友了,到這裏就特別的枯燥,適應不了國內的文化環境,就離開了。
當然離開的時候有兩位學者提了一個共同的問題,我說你們有什麼建議?他說最主要的建議就是一條:國內爲什麼那麼重視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這個評價體系特別不有利於團隊建設,大家都去爭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平常的工作誰做?其他的作者誰當?這個問題提得非常關鍵,我在這裏也把它說出來和大家共享:我們的評價體系如何做?
周忠和:謝謝金老師!饒毅老師,25年來您參與了十餘箇中國前沿科研和高校的機構建立或者改革,包括主持了其中幾個,最近的經歷包括首都醫學科學創新中心和北京腦研究所,請問招聘人才方面有什麼經驗和體會?
饒毅:首先,一定是單位的上級領導支持正確的改革。沒有這個前提,所有的條件都沒法提供給人才。
過去這些年,有少數單位覺得就是要改革,要不然不會找我去,找我去的都是要幹真事的人,包括北大。因爲他們支持,我才能建立適合科學家工作的環境。建立這樣的工作環境之前,會要求上級領導給出整個框架性的同意條件,所有職能部門配合。在這個環境裏,沒有KPI,沒有第一作者、通訊作者,沒有CNS(《Cell》《Nature》《Science》),按照不同年齡段和不同學科,允許科學家們在自己的領域儘可能做到最好。
在北大生科院,我們有老師幾乎沒發過什麼論文,升爲正教授,現在也還一直堅持做重要的工作,工作很努力,論文產出很少是因爲突破不容易,很多人也都支持他。同樣我們有發過《nature》、沒有拿到終身教職的,這兩種情況都有。我們評價的時候,也一定是分開,按照各個學科來請評價專家。
因爲學校領導支持我這項工作,所以我們堅決不按CNS,一定按真正重要的科學。不是每個人都同意,學院有人反對、職能部門也有人以前不僅笑話我,還經常到外面去罵我。但是既然學校支持我,學校知道這是對的,我也知道這是對的,讓他們罵。
這個過程走下來,我們吸引的人才也留在了我們這裏。十幾年前,我們待遇是最高的,現在待遇不是最高、研究經費也不是最多,但是有一個好處,吸引你來,一定是讓你安心做重要的工作,這一點全國很多單位做不到。
很多單位招年輕人來,要他第二年申請多少,第三年申請多少,每年都再去申請比如100萬經費,不斷申請內部經費,這還不算要求申請外部經費的情況。也就是說年輕人來,沒有一步到位給到所有支持,而是不斷讓他跳舞,他哪能不浮躁呢?他急得要死。
我們北大生科院,學校授權,只要請人,不管多年輕的人,六七年的資助全部到位。這個環境,對於特別願意做科學的年輕人來說,比其他因素可能都更有吸引力。所以我覺得,是靠真正適合學術的環境來吸引人才。
周忠和:謝謝饒毅老師!我的理解除了一些共同的理念,比如說不管,不要折騰研究人員,給他們創造這種環境之外,當然跟你的個性,能夠頂住壓力,或者找到更好的伯樂的領導,也是有關係的。我剛纔有點不理解,金老師你們那幫老外爲什麼後來就待不住呢?當然還有第一作者、通訊作者這些問題,可能還有外部資源對他們的壓力,是不是跟這些有關係?
金之鈞:也沒有。我覺得文化不適應可能是最主要的,他們說得也很真誠。因爲是外籍人員,有澳大利亞、加拿大的、美國的,來了以後,幹了三年,滿合同期以後,他們就提出來不能再做下去了,感到很孤獨。
我們引進的2位外籍華人都留下來了,並且幹得非常好。引進本身很困難,孩子上學、夫人工作、在國外的養老保險等等,其中有一位我跟他談了9次。
引進難,引進來以後用好更難,最主要的是搭建隊伍。其中有一位搞地球化學的,我們院有一個重點實驗室,整個交給了他,讓他做實驗室主任,我做學術委員會主任,給他站臺,有困難給他排除,所以他的成果出得非常快。還有一位,因爲國內這方面的基礎薄弱,做這個方向的人不多,所以人才的搭建就比較困難,我們差不多花了五年時間,從海外、國內高校引進來,最後組成了10個人左右的團隊,也給他保證了軟件、計算機等條件,慢慢他纔起來。回國以後,他們這些人要進一步地呵護、進一步適應,創造環境更重要。
周忠和:謝謝金老師,這是很好的補充。張崢老師,你創辦過亞馬遜雲科技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現在又到了香港大學,在你的觀察中,頂尖AI人才迴流中國的趨勢明顯嗎?
張崢:這個問題我後面有機會再談。引進人才和用好人才,還是找對人才更重要。
原創型人才的公式也很簡單,就是能夠以第一性原理爲前提的條件之下,有想象力,加上執行力,就這麼簡單。這些跟你是不是院士、有沒有終身教職不搭界。你可以看一個人的工作,看他的想象力是不是夠,做得是不是紮實?這是一類人才。
還有一類人才,我覺得要有能力,有信心,要挑戰第一性原理。第一性原理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否則我們還在牛頓世界裏。像張益唐這樣的人才,他就有能力、有信心去顛覆第一性原理。這樣的人才比第一類更少一些。
在當下的地緣政治的形勢下,這樣的人才有一個特點,就是糾結。爲什麼呢?因爲好的科學家一定是要有全球視野的,絕對不應該是井底之蛙。從AI這個領域來看,大模型發展到現在,華人貢獻的突破性東西其實不多,從0到1關鍵性突破的地方中國人還是少,中國之外的人才做出的原創性工作還是比我們多很多。所以,有全球視野的人才一定有想和全球科學家緊密連接、交流、合作和競爭的多維度需要,在當下這個切割的局勢下於是處在既要又要糾結狀態,夾在家國清情懷和趨利避害之間。所以,這樣的人才一定也很焦慮。
找對人才之後,爲什麼在意怎麼去考覈他?他有自己的使命,一定會努力做出原創性的成績,做不出來自己走了,並不會賴着。我們真正要做的就是支持。當然,你要在源頭上找對人,不對的話就會有一大堆管理成本。我這也是以第一性原理來思考問題。
周忠和:謝謝張老師!對青年科研人員來說,當前體制下“激發”創造力的最大障礙是什麼?資源分配、評價體系、科研自主性的不足,也可能還有其他問題,哪些是最需要優先解決的?還是從陳老師先開始。
陳十一:我在國外當教授幾乎從來沒感覺這麼卷,僅經歷了一次終身教職評審(tenure)。我們當教授要17封推薦信,其他都不用,你把這個領域全世界的頂尖專家問一遍,說陳十一這個人學問可以,符合霍普金斯正教授的標準,他就給你終身教職。
學術是要有學術規矩的,其中,推薦信是最重要的,你在學術圈子裏的聲譽是最重要的。現在很多單位要看你申請到的經費,要看你發表的論文數量。哪一天中國的好大學把KPI制定得更科學,人才能留住,學術也能上去,纔是我們最樂見的學術生態。
比如日本當初提出,50年要得30個諾貝爾獎,做法之一就是給予持續支持、穩定支持,找到好教授,看他們在本領域教授裏的推薦信,給他們持久支持。如果以此判斷教授的水準,可能會更好。
周忠和:您不要KPI,大學排名呢?
陳十一:全世界的頂尖學者對你的學術的看法,這就是你的KPI。
周忠和:謝謝!金老師,您也說說科研文化方面的問題。
金之鈞:對,剛纔陳校長講的我很同意,考覈體系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導向標。除了這個以外,社會資源的獲取也牽扯了很大精力,大家都明白爲什麼爭帽子?有帽子他們有資源。還有一點,由於整個社會環境在快速發展,大家都顯得比較浮躁。爲了克服這個問題,我們對少數青年科學家的支持力度在持續加大。但是我觀察,即便拿到了一些高投入或強度高的科研項目的青年科學家,還是要去爭項目,自身坐冷板凳的精神和做法也還不夠。所以科研的文化,包括寬容失敗、沉得住氣、十年磨一劍,這種大的環境都不夠。
周忠和:對基礎研究投入本身不足的話,不足就會卷嘛,尤其青年研究人員就會更加捲。饒老師,您有什麼高見?
饒毅:我首先要說清楚,我63歲了,所以跟下面說的事情毫無利益衝突。中國目前與自然科學相關的科技最大的癥結,就是選拔各個單位的領導。凡是領導好的,自然會支持建立好的體制,自然會招好的人。領導是不是真正的德才兼備,就是關鍵。“才”是真正的才能,不是靠假的KPI堆起來的。“德”一定是對自己單位,對中國是真正做貢獻的,而不是拍馬屁。
我們知道有些單位研究經費空前的多。所以資源不是缺乏,中國對科學投入的經費我認爲超過了中國科學家的需要,可是很多單位領導能力上存在很大問題,我覺得這是悲劇。如果各種單位沒有真正德才兼備的領導,支持選拔教授、支持年輕人,好的環境就都不存在。如果有這樣的領導,不管是校領導、院領導還是系領導,就能創造好的環境。
周忠和:我部分同意饒老師的觀點。我覺得有一定的道理,其實很多領導包括學校、學院的領導,他們可能沒有你們北大的金字招牌,沒有你這種個性,我猜可能他們還會有一肚子苦衷,選誰可能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饒毅:要知道,國家對自然科學的支持力度是極端大的。
周忠和:我承認我們基礎研究包括使用經費方面存在很大問題,但是我依然認爲基礎研究的投入總體上還是很不足的。比如以一個數字爲例,2024年基礎研究佔研發經費的比例是6.9%,還遠低於發達國家的15%甚至更高。
張崢:我在大學是進進出出的,主要在工業界,所以學校KPI到底怎麼弄?其實我沒有真正地瞭解,所以這方面沒有太多可講的。但是我覺得考覈到底是爲了什麼?從系統優化的角度來看,考覈的目標就是在有限的資源下,提高原創的能力。
另外,在現在地緣政治的情況下,好的人才一定是焦慮型人才,所以要他們配好“按摩師”。大家不要想多了,是心理按摩。
周忠和:我覺得可以有一定的焦慮,過分的焦慮可能是我們現在青年人員存在的一個問題。科研生態問題確實是一個太大的問題,這裏面有很多,包括評價、資源等等。
我們還是轉入下一個問題,時髦的AI問題。AI時代的科學人才培養,會有怎樣的新模式?在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今天,我們需要重新定義“科研人才”嗎?我們要培養的是“會使用工具的人”,還是“能提出問題的人”?又怎樣培養“能提出問題的人”?這也許是僞命題,我不知道,大部分人默認AI時代會改變很多,也許有人覺得AI沒有說得那麼誇張,也許本身就有很多泡沫、很多噱頭,想聽聽你們的看法。
陳十一:前陣子,我剛剛參加一個校長論壇,其中有一個尖銳的問題:AI來了大學教育怎麼改變?大學還存不存在?也許大家都不來讀大學了。
我的觀點是大學還要存在,大學不僅僅是學知識的場所,剛剛林建華校長所講,大學還是使人成長的一個場所、一個共同體。AI可以改變教育形式,但大學培養人才的職能不會改變。從第一次工業革命到第四次工業革命,牛津、劍橋、麻省理工還存在。這是我的基本觀點,AI可以給教育帶來很大的提升。我喜歡用AI來提升各類的改革、學習,但是大學培養人才的基本職能,建設共同體、讓年輕人跟大家一起成長,這個內稟不會改變。
金之鈞:首先我們要擁抱AI時代,要高度重視AI的發展。我這些年也在關注AI+能源或者能源+AI,個人的體會是,AI的到來比原來計算機到來或者互聯網到來對我們工作、生活、科研帶來的便利會更大。另外,在這個過程中,作爲大學人才的培養、綜合性能力的培養、創新能力的培養和學科交叉的培養,將顯得更加重要。
周忠和:饒毅老師這麼謙虛比較少見。張老師,他們都不是搞AI的,你是做AI的,從你的視角來看,我們這場革命對研究人員,我剛纔說的這些問題有那麼嚇人嗎?
張崢:我有時候在外面做學術講座,結果有學生站起來舉手問,AI來了我怎麼辦?我的附加值在哪裏?
我不光自己做AI,也是一個重度的AI工具使用者,跟它一起寫文章之類的。
我的感覺是這樣,假如要用好AI,有幾個非常重要的能力。第一,你要問出好問題。第二,你要非常敏銳地能夠捕捉甄別它裏面的錯誤,它會有幻覺。第三,它會說出一些想法,是你沒有想到的,可以啓發你。
我現在港大那邊有一攤事就是做AI教育,我自己也做了一些實踐。我覺得AI來做老師,至少有兩點遠超任何人類的能力。第一,在AI眼中,沒有任何一個問題是愚蠢的問題。我們每個老師,不管你是不是好老師,對傻問題的容忍度都是有限的。但你跟AI說我還是不懂,能不能舉個例子再簡化簡化,它有無窮的耐心。第二,它真的可以因材施教。假設我們把每個人的大腦看成是一個貝葉斯模型,你本來有稍微陳舊一點的知識,現在我教你,你的知識會更新。但是每個人的先驗是不一樣的,比如有人喜歡聽古典音樂,或者有人就是喜歡體育。我們今天做AI通識教育,給物理系的講,給哲學系的人講,給每個學科的人來講,用的例子都應該不一樣。從不同的先驗更新到同一個後驗,得到新知識,路徑可以不一樣。那麼請問有哪個人類的老師能夠那麼來教你?從這兩點看,AI假如做老師有非常大的潛力。並不是說不需要人類老師,人類老師有人類老師的用處,但是這兩點在我們教育系統裏面現在是挺大的缺失。
我對現在的教育系統一直是批判性的,這一點AI可以幫助你培養真正的好奇心和批判能力。我們需要重新考慮教育流水線應該怎麼去做。
周忠和:張老師,我理解你的看法,提出問題、判別、鑑別問題,包括質疑、判斷力,這本身就是優秀科研人員應有的能力。AI實際上是幫助我們更好地放大這樣一種能力。本身不擅長問的人,如果利用了這樣一個工具,可能會比以前會問問題的人會獲益更多。
張崢:所以我的看法,假設你要用AI來寫一篇文章,文章是20分或者0分,我想看你的是你當中的步驟,你跟AI之間的問答。
周忠和:但是AI比過去提供了更好的合作討論者和老師。我們再轉入最後一個問題了,今天海淀區很多領導在這裏,可能會比較關心科研成果轉化的問題,我們不能光談“沒用的科學”。一般人認爲,基礎研究與產業應用的距離更近了,在促進成果轉化與應用的人才和機制方面,各位老師有怎樣的經驗和觀察?
先從饒毅老師開始,首都醫學科學創新中心在促進基礎研究和臨牀應用融合方面,有什麼不一樣的做法?能不能簡單透露一點?
饒毅:我肯定不能代表首都醫學科學創新中心,梅林老師是主任。我如果說了什麼東西,等於給人無形的壓力。
我現在換個角度說,生物醫學的基礎研究與轉化的距離非常近,所以對我們這個行當來說,這是一個事情的兩個方面。我讀書的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Boyer,1973年發明重組DNA技術,1976年創立基因泰克(Genentech),是近代世界的第一個生物技術企業。他就是一個生化系的老師,做細菌的研究,當時根本看不出來跟應用有什麼關係,結果幾年之內就開創了世界性的產業,把當地舊金山灣區的產業也帶起來了。
我還有一個老師,我做夢也沒想到,我的博士後導師,當年是一個青年才俊,很年輕就做了哈佛教授,我是1991年到1994年在他的實驗室做博士後。我們那時候都知道他從波士頓每個月要飛一次去舊金山,這麼大牌的一個教授1987年在舊金山開了一家小公司,我當時根本沒搞清楚那個公司叫什麼名字。直到疫情來了,一個著名的公司,叫吉利德,我說這個英文大概是什麼?是不是Gillette,我記得老師的公司跟剃鬚刀公司的名字有點像,就查了一下,果然就是。人家就是三個老師帶一個醫學院的年輕畢業生開了一個公司,當時我們大家都笑話他,說他是浪費時間,結果他就變成了世界前十大藥廠。世界前九大藥廠都是1970年以前就存在的一些原來的藥廠,通過金融手段關停並轉融合成了九個,只有他那一個是新型藥廠。他的特長是什麼?這裏沒有一個東西是他實驗室的,創業的時候公司號稱有他們三個教授的技術,即反義RNA。公司1987年成立,到1994年他們自己都不相信這個技術了,賣掉了。後來有人做成了,雖然很長時間沒有用,但是他們懂這個東西,摸着石頭過河,最後通過不同的方式,變成了世界前十大藥廠。
所以這些例子都是一些真正的教授,他們跟企業家、投資人真正合作,就可以推出來很大的事情,而不是很小的事情。所以我覺得對生物醫藥產業來說,支持基礎研究,自動會出來可轉化的成果和判斷力,也自動會出來創業人才。
周忠和:陳老師,回到你這裏,寧波東方理工大學提出要打造“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工程教育體系”。能不能簡單給我們說一下?
陳十一:感謝周老師具體地關心我們的辦學。前兩天在論壇上碰到一位MIT的教授。MIT是一所以科學和技術爲核心的大學,而寧波東方理工大學簡稱EIT。他形容MIT像一個“U型”結構,一方面是論文發得好,另一方面是轉化做得好。但是MIT的模式教授通常不能自己管理企業,有發明一般讓學生去轉化,這是第三代大學的特徵。
寧波東方理工大學有一些新想法。
第一,中國教授科研成果轉化的動力不足,原因是學校佔股太高。以前我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比例是4:3:3,教授佔4、學校佔3、學院佔3,學校和院系佔比太多,不知道現在是否有改變。到南方科技大學我就改過來了,我們膽子比較大一點,80%給教授,學校跟院系佔20%。到了寧波東方理工大學,學校和院系佔比更低,其目的就是促成教授順利完成科研成果轉化。
第二,第四代大學的核心是創新型大學。全球討論非常多,下一代大學到底怎麼樣?中國的大學要服務國家重大戰略,美國人也學我們,現在也講創新與影響力。我一直在構思,允不允許教授在第四代大學中創新模式?讓教授自己去轉化。我們正在做嘗試,最近有教授在做純固態電池,讓市裏企業投資。這位教授是該領域的全球頂級專家,能不能由他自己去做成果轉化?我們還在探索。同時也在思考,大學如何讓純粹的研究到轉化的鏈條更短一些?
周忠和:謝謝。金老師,3年前你創立了北京大學鄂爾多斯能源研究院,聚焦成果轉化與應用落地。你做這件事,人才方面有什麼經驗和教訓?
金之鈞:現在經驗和教訓都還談不上,我談點體會。我們之所以選擇鄂爾多斯作爲能源的基礎研究成果的落地點,主要鄂爾多斯市比較特殊,經濟實力比較雄厚,願意出錢,人文環境也還不錯,另外和我們的資源、能源轉型息息相關,契合度比較高。
這三年來,我們已經建成了“零碳機場”,把整個機場變成是零碳的。原來是燃氣鍋爐,我們用二氧化碳工質,利用它的相態轉換來實現製冷制熱,綠電做主要的支撐,在機場的周圍建太陽能光伏、建風電。根據中國民航局給我們的意見,這是世界上真正意義的首個“零碳機場”。這套技術的積累,讓我們下一步瞄準零碳產業園建設。海淀區的領導也在這,如果有機會,合作做一些工作,我們還是很願意的,畢竟住在海淀,也應該做點貢獻。
爲什麼成果轉化困難?我早期在石油大學工作,作爲副校長分管過產業化,到了中石化研究院,主要是搞成果轉化,再到北大來。我覺得有一些障礙。第一個障礙,往往需要大資金投入,有人統計過是1:10的關係,甚至更高。假如說基礎研究投入1個億經費產生成果,做成果轉化至少要10個億以上的投資,而這一批風險投資不願意投,政府沒有錢投,所以缺少資金。第二,基礎研究的發明者、教授就像自己生了個孩子抱住不放,自己經營不了,又不願意放手,經常是談不攏、談不成。第三,缺少優秀的項目經理,沒有一個能夠整合資源的項目經理,或者是懂科學的企業家,或者懂企業的科學家,這類人才資源目前在中國是最缺的。
周忠和:最後請教一下張老師,您曾經在微軟、亞馬遜,現在擔任港滬創研院的首席科學家,你怎麼看成果轉化和研究本身的關係?
張崢:我只能站在稍微熟悉一點的工業界研究院的角度來看。假如把所有的科學家都放在一起,其實相當於一個頻譜,產品團隊邊上就有科學家,要解決的問題有很短期的,也有那種很遠期的。
周忠和:我們今天討論了引進人才怎麼培養,怎麼留住,怎麼更好地激發他的創造力,也討論了科研生態,討論了AI時代的科研文化。請各位嘉賓每個人一句話來展望一下,如果中國要繼續保持對頂尖人才和青年人才的吸引力,最需要做什麼?
陳十一:第一點,饒毅對問題的基本看法有建設性,即便有些問題的看法我們不完全一致,但我尊重饒毅,因爲他說的是心裏的話。這表明,北大自由且有思想,也表明了社會的寬容度在提高,實際上學術自由對社會發展非常重要。
第二點,中國經濟要發展,科學技術上還要加大投入。
周忠和:這和饒毅的觀點不一樣了。
陳十一:饒毅跟我的觀點不完全要保持一致,饒毅看見的是北大、清華、哈佛、MIT等優秀的大學,但我國有多少研究人員的科研經費是不夠的。所以科技發展需要國家加大投入,加大教育科技人才的投入,纔是發展之本。
我一句話總結,中國科學崛起就看下一個十年。
金之鈞:剛纔我講了一段自己經歷過的故事,現在把畫外音變直白就是中國要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特別是開放。我們現在在研究日本爲什麼那麼多諾貝爾獎獲得者?大家看看我們的開放程度和日本比,我們還差得多。另外就是寬容,整個社會對學者的寬容,對基礎研究的等待和期待不能急功近利。
在這裏我也想祝賀“知識分子”成立十週年。李開復講過一句話,說要麼你適應環境,要麼你改變環境,要麼你離開環境,沒有其他選擇。用他這個話延伸,作爲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首先你需要適應環境,讓自己能生存下去;更重要的是作爲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還要堅守你的價值觀,想辦法通過你的影響力改造環境,使得中國的環境對科技創新越來越友好。所以大的環境我想就是開放。另外剛纔陳校長和饒毅老師講的選拔幹部也特別重要,對大學來講,一個大學的校長和書記十分關鍵。在座的陳校長,我個人認爲是一位非常好的校長。南方科技大學的發展與你當校長的階段有直接關係,可以說發展非常快,東方理工我們也特別期待。我也特別欽佩饒毅老師作爲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能夠發出不同的聲音,對我們的環境能夠有所改善。
周忠和:他們倆都在誇你,我看你怎麼說?
饒毅:說我引起爭議,當時是叫爭議。不管說美國在衰敗,還是說特朗普有毛病,還是說屠呦呦該得諾貝爾獎,經常我說了之後有一堆人反對,反對完很多人又忘了自己其實錯了。
我認爲中國科學的經費已經足夠多了,要保持這個量,我不認爲要繼續增加。你到全國大部分大學、院系和研究機構裏面實際瞭解,中國的經費到哪裏去了?很多大學的預算是比較接近的,北大不是預算最高的學校,爲什麼會有哪個大學說比北大少很多錢?有些時候是各級領導截流了。所以爲什麼一定要改革,就是這個道理。
如果你所在單位任命了德才兼備的好領導,你是幸運的;如果沒有,你得選這種領導、去這種單位。但我要給大家寄語的是可以操作的,年輕人一定要清楚一個故事,就是40年前、30年前留在體制內工作還是去深圳、去體制外工作,結果有很多人走新的路走下來了。
我建議年輕人不一定都要去參選傑青,去當院士,參選的好處你都知道,你不知道沒參選的好處。沒參選的好處是,需要你的單位一定是看中了你的真正能力,這時候給你的環境就會很好。雖然這種單位是少數,但是中國現在有這樣的單位了。
另外,大家得想清楚,現在很多傑青、長江學者和院士一天到晚說領導部門限制他們,可是他們是自己鑽到那個套子裏去的。你如果不鑽進去,哪有這麼多限制?其實這也是一個選擇,和四十年前一堆人走向體制外去工作,道理是一模一樣的。
張崢:我覺得從人才這個角度來說,應該抓住機會,因爲這幾年是有些跟以前不一樣,要抓住機會。然後是要有定力,中國所有的事情壞就壞在三個字,“急吼吼”,就是做事情都急,然後就走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