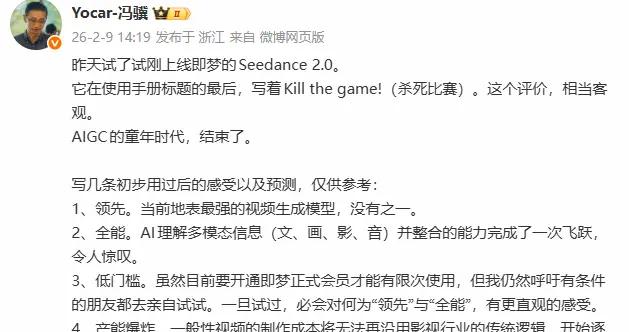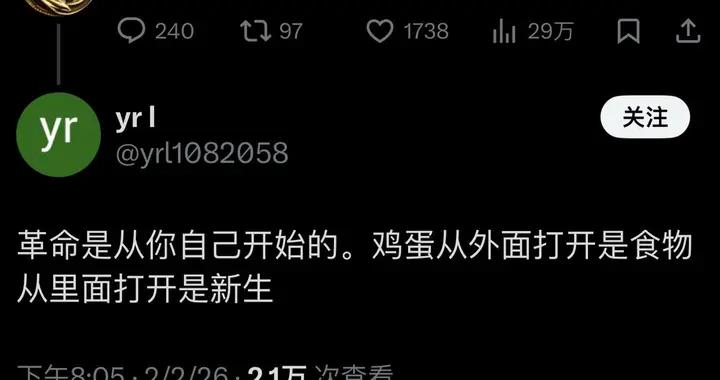中美科技文化交流是怎樣復甦的?

圖源:Pixabay
撰文 | 姚蜀平
中國和太平洋彼岸遙遠的國度——美利堅合衆國的文化往來,應該追溯到19世紀,早期前來的傳教士,他們回國時帶去的中國學生成了最早的留學生。自1872年,首批官費留美幼童始,至20世紀的庚款留美學生,百年來,源源不斷地有中國人到美國,尋求新知識,瞭解新文化。而本世紀來中國的美國人,也不再限於傳教士,在衆多身份中也出現了科學家和各類學者,如地質學家葛利普、生物學家吉等人。
同時,那些歷年留學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們,在回到中國以後,也不斷爲中美科技文化交流拉線搭橋,在把近代西方科學知識傳播到中國,他們無疑是卓有貢獻的。當然,其中由歐洲諸國及日本學成返國的各類科學家也不乏其人。
新中國建國後,由於複雜的國際因素,中國和美國的科技文化交流暫時終止了。就在五、六十年代太平洋兩岸的兩個國家基本沒有往來的時候,美國國內卻逐漸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現象,那就是在她的華裔少數民族中,出現了一支知識大軍,這些中國血統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們改變了昔日華人只能在飯館和洗衣房工作的傳統,出現在名牌大學和大公司的研究所裏。
他們有在二次大戰前後從中國本土赴美留學的,也有五、六十年代來自臺灣、香港或東南亞地區的。由於種種原因,他們沒有能夠和他們的前輩一樣,學成即返國,而是留在了美國;以後他們的多數在不同時期,處於不同的考慮,加入了美籍,成爲華裔美國人。
異國成了本國,他鄉成爲家鄉,但是,民族親情和傳統文化又使他們念念不忘祖國在太平洋彼岸,故鄉是在遙遠的東方。聰慧、勤奮加上良好的機會,他們中的許多人獲得了成就,少數人還成爲科技界的佼佼者。愈是在功成業就、豐衣足食之時,愈是念念不忘養育過他們的鄉土和親人,一種感情迴歸、心理認同的強烈意識默默地在他們的血管深處流動着。
01
七十年代初,一些國家開始注意鬆動與中國的緊張關係,其中也包括美國。中美乒乓球代表團的接觸與互訪就是這種跡象的第一個信號;但是還有一些不爲人知的事情,也在悄然發生。
1971年2月,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意外地接到了一封瑞典皇家科學院常任祕書拉德伯格的來信;更奇怪的是,信中還附有一封美國科學院給瑞典皇家科學院的信。這兩封信的中心議題是:美國全國科學院希望通過與中國保持良好外交關係的瑞典皇家科學院,來改善與中國、特別是與中國科學院的關係。美國科學院執行祕書杜德在信中寫道:“兩國的學術界有着合作的長久歷史,並且有着共同的興趣,儘管過去12年中有着各種阻礙,但是,重要的是他們應尋求恢復這種歷史友誼的方法。”
方法不難尋找,重要的是時機,1971年無論是在中國,或是在美國,這種久已僵化了的兩國關係的鬆動是微妙的、緩慢的、淡而無跡的,它並沒有爲多少人所察覺。但是,就在這若明若暗、撲朔迷離的時刻,卻有人敏銳地洞察了這種可能發展的前景,並且大膽地邁出了開創性的一步。這就是1971年7月20日楊振寧的首次訪華。
楊振寧1922年出生於安徽合肥,父親是知名數學家楊武之,他自己的治學精神不僅對兒子有所影響,而且是最早讓楊振寧瞭解羣論的美妙與應用的人。在西南聯大攻讀時,楊振寧的學士論文是在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的指導下完成的,用羣論分析分子光譜的結果激起了他關於對稱性領域的研究興趣,這決定了他以後研究生涯中的主攻方向。在西南聯大的碩士論文則是在王竹溪先生指導下進行關於統計力學的探討,它形成了楊振寧研究生涯中的另一個重要領域。因此,在中國、在西南聯大,可以說基本上奠定了他畢生從事物理研究的基礎和信念。
1945年,楊振寧赴美留學,在芝加哥大學,他幸運地拜費米和泰勒兩位名家爲師,不僅學到了物理知識,還學會了從物理現象引導出數學表示的歸納方法。在中國紮下的深厚的根基和從美國獲取了豐富的營養,他茁壯地成長了。
四十年代末,他在粒子物理研究中嶄露頭角,隨後又在統計物理方面展現出才華。1954年,他與米爾斯把規範不變的概念從電磁場推廣到所謂“不可對易”的情形,找到了與電磁場相對應的同位旋規範場,即現代物理文獻所稱的“楊——米爾斯”規範場。
這一工作是劃時代的,半個世紀的理論物理發展史表明,楊——米爾斯非阿貝爾規範場論是當代粒子物理中最重要的基本觀念之一。同時還對數學物理和純粹數學的發展發生了重大影響。
1956年,楊振寧和李政道合作,在深入研究了困惑已久的“θ–τ之謎”之後,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的大膽論點。次年,吳健雄等人用實驗證實了這一理論。因此,楊振寧和李政道獲得了該年度的諾貝爾物理學獎。一項物理工作在發表的第二年就獲得了諾貝爾獎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楊振寧的研究工作能獲得如此輝煌成就,是和他的獨特風格——獨立性與創造性分不開的。他的這一特點也反映在他首次訪華的行動上。
楊振寧對養育過他的中國以及年邁多病雙親的深深懷念,使他在中美關係稍有鬆動的時刻就毅然下決心訪華。1971年7月20日,他辭去了IBM公司的顧問一職,冒着當時在政治上、各種輿論歧見上的風險和多方面的阻力,從巴黎中國大使館取得了簽證,懷着渴望與探求的心情,踏上了闊別26年的中國土地,成爲美國華裔知名學者訪問新中國的第一人。
楊振寧在中國度過了四個星期,除了上海、北京,他還返回了誕生地合肥,和26年前抗戰剛剛結束時,瘡痍滿目的舊中國相比,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也給了他深刻的印象。他與親人重逢,與師友會晤,參觀了工廠、農村和科研機構,遊覽了名勝古蹟和名山大川,在實現自己多年夙願的同時,他也在默默地爲中美科技文化交流架橋。
在楊振寧決定訪華時,曾受美國總統尼克松的科學顧問戴維之託,以私人身份探尋中美兩國科學院之間進行有效接觸的可能性及接觸方式。楊振寧在京轉達了這個意願,鑑於兩國當時尚未建交,中國認爲兩國科學院的正式接觸爲時尚早,但是願意考慮美國科學家的個人訪華。
楊振寧在參觀了中國科學院的若干研究所以後,高度評價中國科學家人工合成胰島素的工作,提出願代爲申請諾貝爾化學獎,以使全世界對整個中國的科學進步有新認識和了解。遺憾的是,由於當時的種種原因,楊振寧的這一積極而友好的建議沒有被接受。
在京期間,楊振寧還受到周恩來總理、郭沫若院長等人的接見,在他結束訪問離華返美前,寫給周總理的信表達了他這次歸國的心情:“回國四周來,看到了各種精神與物質方面的偉大建樹,處處都是奇蹟。我要謝謝您,謝謝各有關人員,謝謝中國人民給了我這個教育性的機會,能對新中國所創造的新天地有初步的認識。”
02
楊振寧帶着這個“初步的認識”返回了美國。在那個擁有幾十萬來自中國如今又對新中國所知甚少的地方,他訪華的消息不脛而走,隨即引起了巨大的波瀾。正如他在給其父楊武之的一封信中寫道:“此間各界對新中國的興趣簡直大到無法形容,我把一切記者、電視、無線電請求訪問都推掉了。本校同學、教授要我演講……”
是的,楊振寧無法推掉本校師生的請求,1971年9月21日,他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做了著名的演講,後來這個被題爲“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象”的演講廣爲流傳,被報刊發了通訊,被摘要或全文登載,被華人或美國人廣泛談論。在演講的聽衆中,不僅有華裔美國人,也有許多普通美國人;不僅有紐約人,也有來自華盛頓、波士頓的聽衆,他們來時興致勃勃,去時興奮不已。爲什麼會出現這種熱潮,正如楊振寧在這次演講開始時所說:“這次美國人民方面,對我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旅行,所表示的強烈興趣,正顯示了兩國人民之間有一種真誠的希望和需要彼此互相瞭解。”
猶如投石試水的這次訪問在人文薈萃的華人知識界尤爲引人注目。無數電話打向楊振寧,他們中有陳省身、有林家翹、有任之恭……在中國上海的楊武之和北京的吳文俊和周培源分別收到了著名華裔美籍數學家陳省身的來信,信上的第一句話都是:“振寧談及國內進步情形,十分嚮往(景仰不已)……”
1972年春,尼克松總統訪問了中國,兩國簽署了著名的“上海公報”。兩國關係出現了緩和趨勢,訪華的華裔美籍學者開始增多。
同年6月,以任之恭爲團長的“美籍中國學者參觀團”12人來到中國,他們是王浩、劉子健、林家翹、沈元壤、任之恭、張明覺、易家訓、戴振鐸、葉楷、王憲忠、張捷遷、李祖安等人,這個代表團成員的平均年齡55歲。除了訪親拜友,他們每個人都在自己相關專業的研究所裏作了學術報告,進行了學術交流。
在此還應提及的是,楊振寧在1971年和1972年兩次訪華時,接觸了中國當時的大學及研究機構後,感到基礎理論課程差,研究所的基礎學問不牢的問題,並希望領導能提倡一下。周恩來趁機在會見任之恭所率代表團時,對隨同參加會見的周培源教授提到:“我們今天向這位周博士將一軍,請他提倡一下理論。”不久周培源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題爲“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張文裕、朱光亞等人也乘此之際對高能物理研究及加速器研製問題給周總理寫了信。儘管在哪個特殊時代,他們仍受到了圍攻,但這種提倡,不啻是對理論工作者的一股及時而救命的東風。
03
1972年9月,李政道夫婦訪問了中國。李政道是在中國接受了大學教育又赴美深造,並且取得巨大成就的另一位值得我們驕傲的華裔美籍物理學家。他與楊振寧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原理而獲得1957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李政道,還是楊振寧,在他們領取諾貝爾獎金的時候,都尚未加入美籍。
李政道還在著名的“李模型”中,首次給出了一個可以嚴格求解的場論體系的非相對論的模型,其它如關於場代數的工作,都對理論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根據。
在首次訪華中,李政道就表示出他對中國科技發展的關切之情,他提及基礎科學和培養人才的重要性。他認爲只有建立自己雄厚的基礎科學力量,纔有可能闖出新路,走在世界的最前面。他還提出搞基礎科學的人要少而精,應該從十二、三歲就挑選出這方面的人才進行培養。他的建議在教育制度受到嚴重衝擊與扭曲的1972年當然不可能有所反響。但是卻播下了種子。以後在他堅持不懈的努力和中國變化了的形勢下,這一夙願終於實現。1976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進行了關於招收少年大學生問題的討論,1978年3月該校“少年班”正式開辦,就此開創了一條培養人才的新途徑。
同年九月,國際著名數學家陳省身訪華。陳省身三、四十年代曾任清華、西南聯大教授,1948年受邀赴美后,曾以微分幾何和拓撲學等方面的工作而聞名於國際數學界,特別是他創立的陳示性類,是近代數學中一個極重要的概念,在許多領域中起着作用。1962年,他與楊振寧、李政道、吳健雄和林家翹,同被選爲美國科學院院士。在闊別24年以後,陳省身及夫人回來看望親友和故國,在北京會見郭沫若院長時,他轉交了一封美中科學交流委員會委託攜帶的信,這是一封邀請中國科學家訪美的信,經一位昔日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今天的美國科學院院士之手,完成了在那官方道路尚不通暢、民間迫切希望溝通時代的信息傳遞,這也是陳老先生在顯赫的數學成就之外,對兩國人民的又一貢獻。
1973年,吳健雄和袁家騮訪問了中國,三十年代,他們分別畢業於中央大學和燕京大學,1936年赴美,二次大戰後,進入了核物理的研究領域。吳健雄幾十年的研究生涯是和β衰變發展史密切相關的,她以對物理問題的敏銳和實驗工作的精細著稱,特別是1957年她和幾位同事共同用^60Co在低溫下的實驗,驗證了楊振寧和李政道提出的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假設,從而開闢了弱相互作用的廣闊新天地。她被譽爲“世界上最前列的女實驗物理學家”。1973年,她帶着濃濃吳音回到了闊別37年的中國,10月15日,周恩來總理接見了他們。
在1973年,華裔學者的訪問出現了一個新現象,他們中的少數人和中國學者開始了短時間的科學合作,如張捷遷和科學院大氣物理所,牛滿江和動物研究所都進行了幾個月的合作研究。
1975年11月,一位在實驗粒子物理方面剛做出突出成績的物理學家回國訪問,他是丁肇中。他出生在美國,但是在中國度過的童年,嘉陵江畔的山城和石頭城下的鼓樓曾在他記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雖然大半生涯是在美國度過,但是中國的土地、人民仍使他難以忘懷。1975年,他回來了,在參觀訪問及報告座談中,他集中關心的問題是中國高能物理的發展,他希望能爲此貢獻自己的力量。
1977年,著名華裔美籍天體物理學家黃授書第二次訪華時,心臟病發作,溘然長逝於北京。
04
就在那些年月裏,還有許許多多化學、生物、地學及其他學科的華裔美籍科學家和工程師們絡繹不絕地來中國訪問。他們多是由旅遊局接待,自費閤家來華探親訪友,同時與科學院等有關研究機構的同行們進行學術交流。其中也有不少是以各種團體前來訪問。除了任之恭最早率領的“美籍中國學者參觀團”,同年6月由馮之楨、田長霖率領的“加州中國科學工作者回國訪問團”,由曾安生、譚佔美率領的“美國舊金山美洲工程學會參觀團”,7月由高逢川、陳有平率領的“美籍中國醫生訪問團”。1974年周培基等人的“旅美臺灣同胞及美籍華人回國訪問團”以及以後的“美洲華僑工程學會旅行團”、“旅美東部地區愛國青年參觀團”、“旅美統運積極分子國慶參觀團”、“美國華裔青年團”、“旅美愛國青年和學者參觀團”、“南加州中華科學工學會參觀團”等等。
如果對這數百名回國訪問的華裔美籍學者做一分析,我們會發現他們大致可以分爲這樣三類:
第一類,在七十年代早期回來的多是年齡在50歲上下的人。如任之恭率領的第一個“美籍中國學者參觀團”的平均年齡就是55歲。他們多數是在中國接受的中學及大學教育,然後到美國取得學位,有些人還曾回國做過一段工作;他們屬於50年代初那五千未歸留學生羣體中的一部分。這些人對中國懷有深厚的感情,對新中國的建設成就表示驚訝與讚歎,對中國的前途發展由衷地關切。他們爲幾十年來未能替中國盡力而感到不安,一心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爲曾養育過他們的人民做些貢獻。
第二類是年齡在三、四十歲的人,他們多數生在大陸,長在臺灣或香港,對於中國雖然沒有深刻的印象,但是童年的回憶難以忘懷、令人神往。他們對幾億同胞在一個與他們成長的社會截然不同的環境裏的生活,抱有強烈興趣和美好向往。他們渴望瞭解,勇於探索;而那些有強烈民族感與愛國心的“保釣(釣魚島)運動”的青年積極分子們,更把中國作爲他們思鄉、愛國的奔放感情的最好歸宿地。更有許多人出於對現狀不滿和以學報國的熱忱,一再申請回國定居。根據中央“來去自由”的精神,中國科學院截至1979年,陸續接待了22名回國定居的學者,其中有18名博士,1名碩士。這些人普遍知識新、基礎好,英文流利,又年富力強。他們對中國的科研工作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第三類是出生在美國的那些被稱之爲ABC(在美國出生的中國人)的人。他們是第二代或第三、四代華裔美籍人士,從來沒有到過中國,也不會講中國話(少數人從他們長輩那裏學會一些廣東話、台山話)。如黃添福等人組成的“美洲華僑工程學會旅行團”中的大多數團員就是這樣的人。他們只是從長輩口中和書本上知道一點關於中國的事情,中國對他們來說遙遠而神祕,卻親切又令人嚮往,因爲長輩來自那塊土地。如今,一批批華裔學者越過太平洋上空的轟鳴聲,牽動了他們的心,他們懷着尋根和還願的心情加入了這股潮流。於是,中國土地上出現了只會講英文卻又急於和同胞交流的華人,他們也受到了熱情的接待。第一、二類人的子女們,也應屬於這個行列。
05
1977年,中國結束了十年動亂的局面,人們更多地關注國家的建設與發展。爲了適應科研工作“大幹快上”的需要,並考慮到旅居海外的華裔學者爲祖國服務的迫切願望,中國科學院決定邀請一批具有相當學術水平的旅美學者來華講學和短期工作。1978年第一批被邀請的有陳省身、張明覺、鄧昌黎、吳家瑋等20人。他們在有關研究所裏進行講學與合作研究幾個月以至一年之久。這和他們以往的短期訪問有所不同,他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和了解中國學者及科研機構,因此,在離開中國前,他們中的許多人根據各人不同的感受和可能,向中國政府提出了種種建議。
1977年,陳省身提出了爲使中國數學在本世紀末趕上世界標準的五點建議;王浩提出了“關於促進教育科技發展的幾點意見”;範章雲在南京紫金山天文臺工作三個月後,提出關於中國天體物理發展的萬言建議;伍鴻照在數學所講學一個月後,提出關於中國高等教育制度的建議;吳家瑋在中國停留了四個月,回美后擬成立“中國留美學者服務社”,向國內提供美國主要研究所及大學的有關情況和資料。
1979年初,中美正式建交,隨着兩國關係的正常化,科學文化交流活動也日趨頻繁。
在華裔學者歸國講學中,令人矚目的是1979年李政道進行了爲期七週的講學活動。來自全國23個科研單位和63所高等學校的科研人員、教師近五百人,在科學會堂聽了“粒子物理”和“統計力學”兩門課程。李政道先生夙興夜寐,不辭辛苦,兩學年的課時壓縮在短短七週內完成。
在華裔學者不斷返國的同時,中國學者出國進修求學也被提上了日程。早在1974年,楊振寧開始與復旦大學進行合作研究時,就曾邀請谷超豪赴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講學,但是限於當時的國內外環境,這一邀請一再被婉拒、被推遲。1976年以後,曾有少數科技代表團出國訪問,但時間都比較短暫。到1977年8月,在粉碎“四人幫”一年以後,當丁肇中第二次訪華(此時他已因發現J粒子而成爲榮獲諾貝爾物理獎的第三位華裔美籍學者),鄧小平接見他時,提出“我很想派一個團隊到你那裏工作。”
而丁肇中也表示要爲國內科學技術的發展做些實實在在的事情。起始,鄧小平希望派100個人去西德丁肇中實驗組工作,但丁肇中表示,他們自己團隊僅有30多人,這次會晤最後確定了在德國的丁肇中實驗組爲中國培養10個人。鄧小平就此事爲發端,表示“各行各業都可以派留學生。”自1978年,中國開始再次有計劃地向世界許多國家派送訪問學者和研究生。
10位優秀的中國中年物理學家於1978年1月抵達漢堡,參加了丁肇中實驗組的工作。這是中國與西方國家首次大型合作,在以後的20年中,中國有百餘人蔘加了丁肇中德國實驗組的工作,人數最多時達26人,佔該組當時在西德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在合作研究中,他們共同探討了對極小距離下量子電動力學的正確性,研究帶電輕子的普適性,發現由於非共線硬膠子輻射所產生的三噴注現象等。
1982年始,丁肇中實驗組在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高能量正負電子對撞機上,爲1987年開始的光子、電子和μ介子物理研究做準備。參加這一實驗的有14個國家,34個機構,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硅酸鹽所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成爲這個由丁肇中領導的大型國際合作實驗集體中的一員。中國方面這次除了投入人力外,還參加了實驗的準備工作。如上海硅酸鹽所承擔了電磁量能器所需的全部鍺酸鉍晶體(BGO)的研製和生產,高能物理所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參加了部分探測器的研製工作。40個來自中國(包括臺灣)的研究生將在這一實驗從準備到進行的過程中得到培養。在科學技術其他領域的國際合作日益增多的今天,我們是不會忘記首次合作的範例。
在太平洋彼岸的一列列人馬飛向東方的時候,太平洋此岸也有一團團人流飛向西方,那是赴美參觀訪問的中國各行各界代表團。在陌生的國家和社會里,他們受到的來自遍及美國各大都市華裔學者和同袍的關心與幫助,是難以訴盡的。其中也包括對留學生及早期訪問學者的無私幫助。
華裔學者歸國進行學術交流的高潮可以看作是1980年的廣州粒子物理理論討論會。
鑑於中國理論物理學家早在1966年就提出了層子模型理論,文革期間這一工作雖然受了干擾,有所停頓,但是1978年科學大會以後又有所進展,它爲召開一次理論物理討論會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1980年1月5日至10日,在廣州從化召開了廣州粒子物理理論討論會。到會的一百餘名代表中有海外學者49人,他們是來自7個國家和地區的海外華人、華僑和中國血統的物理學家,佔海外中國血統粒子物理研究者70%以上。這49人中有33人來自美國,其中許多人是第一次回國。他們來華參加討論會受到了他們所在學校、研究機構乃至美國能源部和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支持。會上,有近80人作了報告,其中部分工作達到了國際較高的水平。
廣州粒子物理理論討論會是中國在中斷了與國際學術界多年交往後,首次在國內舉辦的大型國際學術討論會。由於邀請的國外代表皆屬華裔,同語種大大方便了會議的議程,同胞情誼使物理學家在同行的共同語言之外,更多了一層可以互相溝通的根由。這次相逢的海內外物理學家建立起的學術聯繫,在以後的幾年裏,一直髮揮着作用。這次討論會也爲在中國舉行國際學術交流提供了經驗。近幾年來各學科、各門類的國際學術會在中國舉行已愈來愈普遍,參加者也不再僅限於華裔,而是包括廣泛的外籍學者。但在如何選擇被邀請的外籍學者問題上,最早和國內科學家接觸的這批華裔美籍學者,無疑是起着重要的推薦作用。
06
如果稍作統計,我們可以知道在中美建交後的最初幾年裏,科學院和各研究所邀請來華講學或來華探親並訪問的中國科學院的外籍華人數目如下:1979年117人,1980年激增爲170人,1981年100人,1982年123人。
中國在“請進來”的政策的同時,1978年以來,“派出去”也在逐年擴大。華裔學者在這個問題上同樣盡力地發揮他們特殊的作用。1979年,李政道在準備回國講學前,曾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親自與美國27個高能物理方面的機構分別進行了聯繫、商談,爭取了若干願意接受幫助培養中國高能物理實驗人員的名額,爲我國派出留學生提供了方便之門。1980年,李政道發起和組織了美國幾十所大學聯合爲我國招收物理研究生並給予資助,即CUSPEA。第二期CUSPEA從1981年開始,後來一直延續到80年代末期,爲中國培養了九百多名優秀人才。李政道提議建立若干“博士後科研流動站”也爲取得博士學位的優秀青年提供了一個靈活的、又有比較優越工作及生活條件的制度。
在我們對七、八十年代短暫的歷史做了一個概括的回顧以後,我們清楚地看到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在中國人民開始大踏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性時刻,在太平洋彼岸,一支異軍突起的隊伍,把現代科學技術從它的最前沿,迅速地帶到了中國。一百年前,耶魯大學第一個中國畢業生容閎在完成學業時,首先想到的是:“我所享受的教育權利,下一代的同胞也應該同樣地享受。”今天,在耶魯,在哈佛,在普林斯頓……畢業的是成百上千的中國血統的學生,他們和先人容閎一樣,念念不忘自己的同胞。容閎曾率領120個幼童赴美求學,可是在昏庸的清朝,終究半途而廢,成爲歷史悲劇;今天,爲同胞盡力的華裔美籍學者們,卻有幸一展宏圖。
當我們回顧這些年來,在中美科技文化交流中鋪路架橋的華裔學者的時候,勢必會想到這樣的一些問題:是什麼力量使得這些志士仁人們爲一個遙遠的國家不辭辛苦;如何評價他們所做的種種努力;這種現象的前景將會如何。
衆所周知,在美國的移民隊伍中,來自歐洲的科學家,以至來自亞洲和其他地區的學者大有人在。他們之中,除了猶太民族和以色列的千絲萬縷聯繫外,又有多少國家的學者,會像華裔科學家那樣,被他們故國牽動得如此深沉和普遍;又有多少民族的後裔,像這批華裔學者一樣,對他們的同胞如此醉心和盡力。
爲什麼會這樣?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親情所致。中華民族,同爲炎黃子孫,神明遺裔,從膚色外貌到語言文字,從社會習俗到文化傳統,都和西方相去甚遠。在華裔學者和美國社會融合的過程中,甚至在他們加入美籍成爲一個美國公民之後,也會念念不忘他們仍然是一箇中國人,不管爲此他們感到驕傲還是深爲煩惱。一根精神上的、感情裏的、看不見卻又剪不斷的親情線,把他們和那個賦予他們軀體與靈魂的土地和人民暗暗相連,一種內在的溝通慾望本能地潛伏在每個人的心中。五、六十年代,這種溝通的渠道中斷了,時間愈久,潛伏的本能也愈強烈。因此,當1971年7月楊振寧首次訪華後,這種潛能勢不可擋地衝決了出來。
他們是當代中美科技文化交流最早的使者,他們在中國科學研究遭干擾、延誤了若干年後的困難時期,爲故國及時提供了幫助,他們在增進兩國人民的瞭解與友好方面,無疑是卓有貢獻的。但是今天,當我們客觀評價這批迴國學者的歷史功績時,似乎不應該忽略他們這一行動的另一層重要意義,他們可能會使我們對全國人民奮力以求的現代化有更深刻和更正確的理解。
百餘年來,中國人民對於隨着軍艦大炮而來的西方文化,是採取不得已的方式來對待,而對在西方文化面前節節後退的中國傳統文化則大唱輓歌。人們不善於把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和西方文化乃至隨之而來的科學技術區分開。
對待西方文化,常常也是擺出“自衛”的架勢,這是百年來國家虛弱、民族受辱所形成的普遍心理,它使得我們不可能真心實意地去吸取孕育出近代科學技術的西方文化的營養與精華。
當七十年代大批華裔科學家和工程師來到中國的時候,這種狀態意外地有了改變的可能(不是完全改變),因爲來傳授和交流新知識、新技術的是中國血統的人。他們多數人到了這塊土地後都願以其中一員出現;而接受或交流新知識、新技術的人在同種族的學者面前,心理狀態也稍趨平和,因此他們的交流要勝過以往。
另一方面,這批華裔學者在美國幾十年的生活,早已在新與舊、中與西的困惑中數遭錘鍊,在傳統文化與西方價值之間幾經選擇。他們是過來人、是知情者,對於如何由中國文化薰陶的傳統人過渡到工業化的現代人,他們有過痛苦的經歷和深刻的體會;對於像中國向現代化工業國家轉型,可能會遇到的困惑與艱難,他們有無數的建議和忠告。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幾十上百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受體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見解動議,它不是用任何金錢買得來的,也不是教科書上能完全找到的,但卻是中國人民得天獨厚能獲得的,也許只有在這個時候,我們真應該感謝把天涯海角之人結爲一家的傳統文化吧。
我們相信,不管中美關係如何發展和變化,兩國科技文化的交流將會繼續下去,因爲這是兩國人民的共同意願。隨着中美科技文化交流廣泛開展,華裔學者的作用不會像兩國文化交流初期那樣突出,但他們的特殊地位會使他們的某些作用永不可被他人所取代。
我們完全理解也贊同這些華裔學者在唸念不忘自己同胞及故國的同時,更加立足於對所在國地位與權益的爭取,華人科學家吳家瑋當選舊金山州立大學校長和吳仙標出任特拉華州副州長並競選參議員就是值得提倡和慶賀的事。另外,中國派出的數萬名留學生的歸國,將在一定程度上接替和擴大華裔學者的作用,儘管二者地位、作用不盡相同,但是在把近代科技知識傳播到中國,把現代化的價值觀念引入傳統社會來說,確有異曲同工之處。
我們回顧這十幾年發生的事情,在歷史長河中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卻值得大書一筆。當後人回憶起這段短暫時光時,華裔美籍學者返國交流學術的業績會被人們永遠銘記,它也將爲尋求世代友好的中美人民所稱頌。
注:1986年,適逢楊振寧教授首次回國訪問十五週年,爲了紀念在那個沉悶的時代,大批華裔美籍學者從大洋彼岸來到封閉的中國,帶來最新科技知識與信息的熱潮,我自1985年底開始準備寫作此文。爲此我從中國科學院外事局四處(華人處)借了15本檔案,四處當時唯一要求是寫完初稿要拿給他們過目;當我完稿後如約送請他們審讀,不料外事局四處閱後不同意發表——“不許在國內外任何地方發表”。事後我告知楊先生(因撰寫此文,爲了確保事實無誤,我曾經請教過楊先生幾個細節),楊先生回信表示“一時發表不了,也是一項有意義的整理工作。”並感謝我寫了篇一萬多字的長文。現在時過32年,此文部分內容近幾年已陸續在我的某些文章及書籍中採用,今天再將全文存案於此,以紀念那個特殊年代中的特殊歷史事件。
1986年1月13日完成初稿,
1988年12月完成修改稿,
2018年2月22日完成終稿,
首發於《願天下壯士志終酬——姚蜀平論文集》,2018年10月美國美亞出版社,經作者授權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