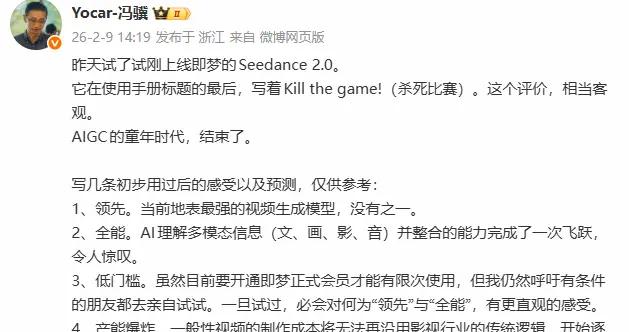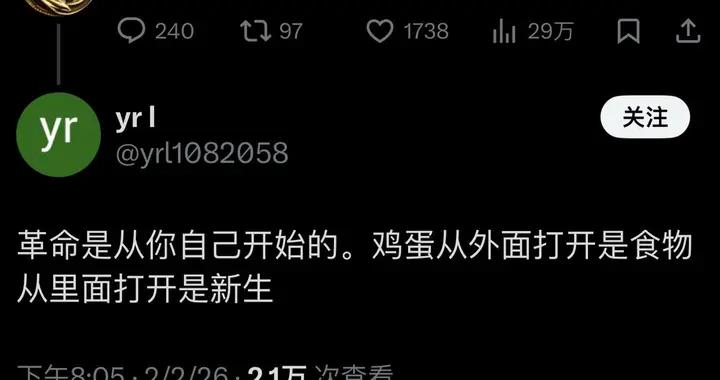汪詰:70 年前,愛因斯坦的大腦被完整取出,它真的異於常人嗎?
紀念愛因斯坦逝世七十週年
70 年前的 1955 年 4 月 18 日凌晨,在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醫院,一陣慌亂的腳步聲把很多病人從睡夢中驚醒。在一間病房中,護士和醫生正在緊張地搶救一位特殊的病人。這位病人有着一頭亂蓬蓬的頭髮和鷹一樣深邃的雙眼,任何人只要看一眼,就能認出他是誰——被全世界公認爲擁有人類最強大腦的愛因斯坦。

不過,再強的大腦也無法改變死神的決定,1 點 15 分 ,愛因斯坦的生命之火悄然熄滅,享年 76 歲。他生前留下遺願,希望將肉身歸於火焰,骨灰撒向風中,不留痕跡,不立碑銘,拒絕成爲後世朝聖的“聖物”。他似乎想以最徹底的方式,將自己這位宇宙的“窺探者”,重新融入宇宙本身。
然而,就像命運總喜歡在劇本上添加意想不到的轉折,就在愛因斯坦溘然長逝僅幾個小時後,負責執行屍檢的病理科醫生,托馬斯·哈維,做出了一個足以讓世界譁然的決定。

(1955 年的托馬斯·哈維醫生)
面對這顆剛剛停止運轉、卻曾容納了整個宇宙圖景的大腦,哈維被一種近乎癡迷的好奇心驅使着。或許是渴望揭開天才智慧的終極祕密,或許只是一念之間的衝動,他做出了一個近乎於瘋狂的舉動。
哈維在沒有通知任何人的情況下,擅自將愛因斯坦的頭骨小心翼翼地鋸開,將這顆人類最強大腦完整地取出,並迅速浸入了福爾馬林的防腐液中,用容器存好後偷偷帶回了家。同時,他還取走了愛因斯坦的兩隻眼球,後來交給了愛因斯坦的眼科醫生。

(托馬斯·哈維醫生和他保存的愛因斯坦大腦切塊)
哈維醫生的“竊腦”行爲很快就被發現,立即上了新聞,普林斯頓醫院當然是震怒不已,要求哈維立即歸還愛因斯坦的大腦。不過,哈維就像是喫了熊心豹子膽,鐵了心不與院方妥協。從法理上來說,愛因斯坦大腦應當屬於他的長子漢斯·阿爾伯特,也只有漢斯有權要求哈維歸還大腦。
但令人意外的是,漢斯在經歷了最初的震驚與複雜的情感掙扎後,不知道怎麼就被哈維說服,居然“追認”了哈維的行爲。當然,這絕非毫無條件的諒解,漢斯與哈維達成的條件是,這顆大腦必須、也只能用於嚴肅的科學研究,研究結果必須公開發表在受人尊敬的科學期刊上,絕不允許成爲滿足低俗好奇心或製造媒體噱頭的工具。
不出意外的是,哈維很快就被普林斯頓醫院解僱,開始了他人生的“另一半”,他就像《魔戒》中的咕嚕一樣,終其一生,守護着愛因斯坦的大腦,並積極推動對大腦的研究。
趁大腦還比較“新鮮”,他與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專家合作,對大腦進行了初步的測量、稱重。結果很令人驚訝,愛因斯坦的大腦重量約爲 1230 克,竟然還略低於成年男性的平均水平。這至少可以說明,腦袋大和聰明之間沒有必然聯繫。

(哈維拍攝的愛因斯坦大腦高清圖片)
然後,哈維遵循當時的解剖學規範,將愛因斯坦的大腦切成了大約 240 塊,用火棉膠包埋起來,方便未來切片研究,並製作了數千張珍貴的組織切片。
然而,哈維並非神經科學領域的權威,他想要組織大規模研究的願望屢屢碰壁。在接下來的漫長歲月裏,這顆本應在世界頂級實驗室接受尖端儀器反覆測量的大腦,卻跟隨着哈維醫生過上了近乎“流浪”的生活。
愛因斯坦生前可能做夢也想不到,他的大腦被分裝在幾個玻璃罐裏,有時藏在簡陋的蘋果酒冷藏箱下,有時塞在不起眼的紙箱中,有時候甚至被長時間放在汽車的後備箱中。
隨着哈維工作和住所的不斷變遷,從新澤西到堪薩斯,再到密蘇里,愛因斯坦,不,愛因斯坦的大腦也隨之在美國大地上輾轉遷徙。哈維本人的生活也因此備受影響,甚至一度被吊銷了行醫執照,付出了巨大的個人代價。
在這個過程中,他零星地將一些大腦樣本,像分發聖物一樣,寄送給少數他信任的研究者。但大部分時間裏,這顆大腦只是靜靜地躺在防腐液中,彷彿一個巨大的祕密,等待着被喚醒的時刻。
幾十年過去了,關於愛因斯坦大腦的研究似乎成了一個遙不可及的傳說。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神經科學研究技術日新月異,那些被哈維醫生小心保存的樣本,終於迎來了被重新審視的機會。全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們,甚至包括來自中國華東師範大學的團隊,紛紛加入到這場探尋人類最強大腦奧祕的隊伍中。他們像極了手持密碼本的譯碼者,試圖從這些沉默的組織切片中,解讀出關於“天才”的蛛絲馬跡。那麼,他們到底發現了什麼呢?
再繼續往下之前,我們有必要先熟悉一下關於人類大腦的各種術語。

腦科學家把我們的大腦分成了四個大區。離我們額頭最近的這塊區域叫前額葉,後腦勺這塊區域叫枕葉,對,就是離枕頭最近的意思。離頭頂最近的那片區域叫頂葉。前額葉、枕葉、頂葉這三個詞取得很通俗,一看就能理解。唯一有點令人費解的就是頂葉下面那片區域,這是我們的大腦藏的最深的區域,這片區域被叫做顳葉。
1985 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瑪麗安·戴蒙德(Marian Diamond)教授,在權威期刊《實驗神經學》(Experimental Neurology)上發表了第一項引起廣泛關注的研究成果。通過對哈維提供的四塊大腦樣本,主要來自與高級認知功能相關的左半球頂葉和額葉區域進行細胞計數。戴蒙德發現,在愛因斯坦大腦的左頂葉下方區域,神經膠質細胞與神經元的比例,顯著高於她所用的對照組——11個年齡在47到80歲之間的普通男性大腦樣本。這裏需要簡單解釋一下,現代腦科學認爲,神經元相當於大腦的計算單元,而神經膠質細胞則相當於大腦的後勤保障單元。換句話說,戴蒙德發現,愛因斯坦大腦中的後勤保障部隊的比例要遠遠高於普通人。
具體高多少呢?不同的解讀略有出入,但普遍認爲這個比例是“異常地高”。戴蒙德由此推測,這可能意味着愛因斯坦大腦的這個特定區域有着更高的代謝需求和更活躍的神經活動,所以得到了更強的“後勤支持”,這或許,請注意,僅僅是或許,與他進行抽象思維和數學推理的超凡能力有關。
這項研究無疑是開創性的,它首次爲“天才大腦”的與衆不同提供了一種可量化的生理學線索。一時間,“愛因斯坦有更多的大腦燃料供應細胞’”這樣的說法不脛而走。
不過,孤證不立,質疑聲隨之而來:這 11 個對照大腦能代表全人類的“普通”嗎?他們的死因、保存方式是否和愛因斯坦大腦一致?更核心的問題是,膠質細胞比例高,真的就直接等於思考能力強嗎?這種相關性距離因果性,中間還隔着多少未知的變量?你看,科學的進步往往伴隨着更多的疑問。
隨後,更多的研究者加入了這場“尋寶遊戲”中。1999 年,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的桑德拉·維特爾森(Sandra Witelson)教授團隊在頂尖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上發表了另一項重磅研究。他們利用更全面的大腦照片和哈維保存的樣本與 35 名男性和 56 名女性的對照大腦進行了比較,將焦點放在了頂葉(Parietal Lobe)的整體形態上——這片區域被公認爲與空間感、數學邏輯和視覺想象力息息相關,正是愛因斯坦天賦的核心地帶。
他們的發現同樣令人驚歎:愛因斯坦的頂葉中有一小片區域,比對照組寬了大約 15%,顯得異常“豐滿”。這使得他的頂下小葉看起來像一個更大、更連續無阻礙的整體。那這會不會像打通了任督二脈一樣,讓這片區域內的神經元能夠更自由、更高效地連接和交流,從而極大地提升了他的空間想象和抽象推理能力呢?維特爾森教授團隊正是提出了這樣的假說。
這個發現同樣極具啓發性,但同樣也無法迴避科學的拷問。這獨特的結構,是天才的專屬配置,還是僅僅像有的人天生手指比別人長一截一樣,只是一種罕見的解剖變異?我們如何能確定這 15% 的寬度就一定能轉化爲認知上的巨大優勢?基於照片的二維分析,能完全替代三維的精細測量嗎?
當然,探索並未止步。後續的研究者們,利用日益精密的成像技術和分析方法,又提出了其他的“不同之處”,比如:
布里特·安德森(Britt Anderson)等人在1996 年的《神經科學快報》(Neuroscience Letters)上報告說,愛因斯坦大腦的前額葉皮層(Area 9)可能比對照組稍薄,但同時,該區域的神經元密度可能更高。這又引出了新的猜想:是不是神經元更密集,處理信息更高效呢?但這同樣是基於有限樣本的推測。
著名的古人類學家迪恩·法爾克(Dean Falk)通過對比愛因斯坦大腦的照片和大量其他大腦的形態,在 2009 年的《大腦結構與功能》(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等期刊上發表文章,指出愛因斯坦大腦皮層,尤其是在前額葉、頂葉和枕葉,擁有異常複雜的溝回模式(folding patterns)。她甚至在負責左手精細運動的區域發現了一個凸起結構,類似希臘字母“Ω”形狀的結構,她把這個結構戲稱爲旋鈕(knob),並推測這可能與他從小學習拉小提琴有關。但這些形態上的獨特性,其功能意義依然是模糊的。
2013 年,來自華東師範大學的門衛偉博士領導的團隊,在權威期刊《大腦》(Brain)雜誌上發表了一項引人注目的研究。他們利用高分辨率的照片分析了連接左右大腦半球的“信息高速公路”——胼胝體(Corpus Callosum)。研究發現,愛因斯坦的胼胝體,尤其是負責傳遞感覺運動和認知信息的中後部區域,似乎比對照組(包括年輕和年老的對照)更厚實,擁有更廣泛的連接纖維。這是否意味着他的左右大腦半球“合作”得更緊密、信息交流更高效呢?這同樣是一個誘人但需要更多證據支持的假說。
你看,圍繞着愛因斯坦大腦的研究,就像是一場永無止境的解謎遊戲。科學家們如同偵探,從有限的“物證”中尋找線索,提出各種各樣的理論和猜想。每一項發現都可能帶來短暫的興奮,但緊隨其後的,總是更多的疑問和科學共同體嚴苛的審視。
那麼,這些研究的價值究竟在哪裏?它們最大的價值,可能並非提供了一個關於“天才密碼”的終極答案——科學本身也從不承諾終極答案——而在於這個過程本身。它極大地激發了我們對於大腦結構如何影響心智功能的思考和探索,推動了神經科學成像技術、解剖學方法和比較研究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它生動地向我們展示了科學是如何運作的:通過觀察,提出假說,尋找證據,接受檢驗,承認侷限,不斷修正。它讓我們深刻體會到,試圖通過解剖一個獨一無二的大腦來完全解碼“天才”這樣複雜的人類現象,本身就可能是一種過於簡化的奢望。智力、創造力、洞察力……這些閃耀的人類品質,是先天基因、後天環境、個人努力、社會機遇,甚至一點點運氣的複雜交織,絕非大腦某幾處形態差異就能完全定義的。
好了,兜兜轉轉,我們終於要回到最初的那個問題了:70 年前被完整取出的愛因斯坦的大腦,它真的異於常人嗎?
我想,在聽完了這段跨越半個多世紀的探索之旅後,我們或許能給出一個更成熟、更符合科學精神的回答:
是的,從解剖學上來看,愛因斯坦的大腦確實在某些方面顯示出了一些與“平均”或“典型”大腦不同的特徵。無論是特定區域更寬的尺寸,還是某些溝回的獨特形態,亦或是神經膠質細胞與神經元的不同比例,以及可能更發達的半球連接……這些客觀存在的差異,讓我們可以說,他的大腦在物理形態上,確實有其“異常”之處。
但是,這絕不等於我們可以草率地宣稱“找到了天才大腦的祕密”。科學思維最重要的一課,就是區分相關性與因果性。我們觀察到的這些結構差異,與愛因斯坦的非凡智慧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聯繫?這一點,目前的科學證據遠不足以給出肯定的答案。這些差異,完全有可能是人類大腦巨大變異譜系中的一個獨特樣本,就像我們每個人的指紋都獨一無二一樣。它們或許對他的思維方式產生了某種影響,但要說這些差異就是他成爲愛因斯坦的決定性因素,那將是對科學嚴謹性的背離,也是對人類智慧複雜性的低估。
科學探索的魅力,就在於它總是在已知和未知之間徘徊。愛因斯坦的大腦,就像一個沉默的謎語,它允許我們觀察,允許我們測量,甚至允許我們猜測,但它從未輕易給出答案。
在哈維醫生取出愛因斯坦大腦 52 年後的 2007 年 4 月 5 日,他自己也在普林斯頓醫院與世長辭,享年 94 歲,此時,他與這家醫院的恩恩怨怨早已成爲古老的傳說。
如今,這顆曾孕育出顛覆性思想的大腦,在經歷了哈維醫生近半個世紀的“私人保管”和顛沛流離後,它的大部分樣本最終又回到了最初它被取出的普林斯頓醫學中心。而其中一部分被精心製作成永久切片的樣本,現在靜靜地躺在美國費城的穆特博物館(Mütter Museum)的展櫃裏,供世人瞻仰。

(穆特博物館展出的愛因斯坦大腦組織切片)
今年恰逢愛因斯坦逝世七十週年和狹義相對論發表 120 週年,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年份,我把愛因斯坦思考狹義相對論的往事拍成了電影——《尋祕自然:時間的形狀》,以紀念這顆非凡大腦迸發出的智慧之光。這顆人類最強大腦,雖然不再能思考宇宙的運行法則,卻以另一種方式激發着我們的思考——關於天才的本質,關於大腦與心智的神祕聯繫,更關於科學探索本身:那就是面對最誘人的謎題,也要永遠保持那份冷靜的質疑、對證據的尊重和對未知的好奇。因爲,真正塑造了世界的,或許不只是大腦的溝回褶皺,更是那褶皺之中,曾經點亮人類文明的思想光芒。
來影院吧,跟隨愛因斯坦,破解時空懸案!
5 月場次安排
福建福州(5 月 3 日,汪詰導演互動場)
第一場 10:00-12:00
第二場 14:00-16:00
廣東廣州(5 月 4 日,汪詰導演互動場)
第一場 10:00-12:00
第二場 14:30-16:30
浙江紹興(5 月10日 ~ 11日 導師互動場)
第一場 5 月10 日 15:30-17:45
第二場 5 月11 日 15:30-17:45
購票請關注公衆號:尋祕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