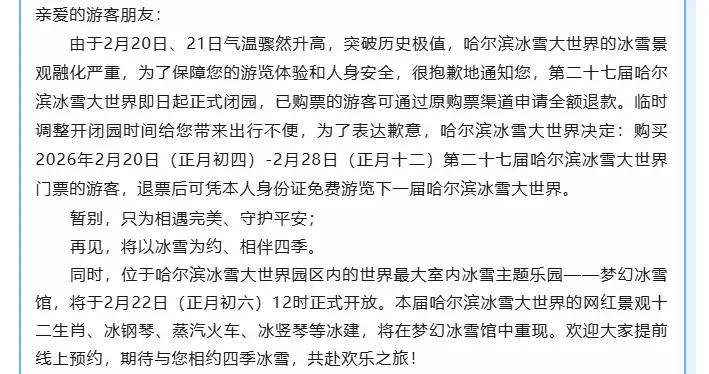吳曉東 | 文學怎樣思想,思想如何文學



文學與思想的關係是歷久彌新的話題,在20世紀人類文學思想史上尤其被賦予了新的闡釋和理解。何謂文學中的思想,思想又如何灌注文學?思想型文學的特徵是什麼?文學作品中過於強大的思想性會不會壓抑文學性?何謂蘊含着豐富思想的“文學性”?從文學中如何進行思想性研究,又如何處理文學史和思想史的關係?……這些議題,在2025年商務印書館推出的、由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張輝、張沛教授主編的“文學×思想”譯叢(第一輯十種)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解答。閱讀這一譯叢,是一個既思考思想,也思考文學,同時也是對文學和思想關係的研究範式進行探究的過程。
在北京大學2025年6月19日舉辦的“意義之美:‘文學×思想譯叢’新書發佈座談會”上,主編張輝這樣介紹譯叢所追求的宗旨:偏重於探索文學和思想的關係,試圖讓文學回歸思想,迴歸與思想的關聯性。第一輯中的大部分都堪稱是思想型著作,幾乎每一部都對西方文學史、思想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有獨特的思考、探索,應對的也是人類一些根本性、終極性的問題,就像陳鬱忠在爲德國理論家布魯諾·斯內爾的《精神的發現:歐洲思想在希臘的興起》所寫的譯後記中所說:該書和奧爾巴赫的《摹仿論》以及庫爾提烏斯的《歐洲文學與拉丁中世紀》,這德國戰後人文學科研究的三大名著“是當時頂級學者因擔憂歐洲文化在兩次大戰之後分崩離析而寫就的‘憂患之書’”,是直麪人類命運的大書,也爲思考現代文學和思想的關係,提供了具有生產性的思想型範式。
而在我看來,所謂的“思想型”也就是能爲思想賦型,或曰給思想以形式;這些著作中的思想也是被賦予了形式,而不僅僅是作爲內容的思想,這就是文學在其中所擔負的結構性功能與核心性使命。而文學和思想的關係也不是單純的疊加,而是乘法的關係,是彼此的相互生髮與放大。在這些書中,文學和思想是水乳交融,不分彼此的,文學是以思想爲底蘊和根基,是滲透了思想的文學;而思想也被文學浸潤和滋養,被文學給詩性化,是被文學的裝置和透鏡過濾和放大的思想。就像納海翻譯的美國學者凱瑟琳·祖克特的《自然權利與美國想象:小說中的政治哲學》所昭示的那樣,雖然作者最終試圖探討施特勞斯式的政治哲學命題,但這本書更想強調的是:美國的“這些小說家的作品中描繪的自然狀態,重新塑造了我們對這個國家整體原則的理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些小說轉變了人們的自我認知,以及美國人民的身份構建……經典的小說家不僅在描述,而且在努力重塑這些道德觀念或習俗,並在這一過程中參與了某種意義重大的政治領導”。這也印證了美國哲學家理查德·羅蒂在《築就我們的國家》一書中的說法:美國曆史上的那些文學類經典,“並不旨在準確地再現現實,而是企圖塑造一種精神認同”,築就的是關於共同體的想象。也正是文學經典把關於國家民族的願景以及關於人類未來的思想給具象化和感性化,才真正在人的情感結構中落地生根。

圖源:視覺中國
因此,這套書中諸如《自然權利與美國想象》以及李雙志翻譯的德國學者克特·漢布格爾的《詩的邏輯》,都有助於認知什麼是文學無法被替代的獨特意義,也從詩學的角度拓展了理解文學性的新視野,甚至重構了文學研究的一些基本範式。恰如《詩的邏輯》封底的介紹語所說:“文學的語言承載着特殊的人類生活經驗,而‘詩的邏輯’是文學的現象學。德語版‘新批評’派核心代表人物克特·漢布格爾以細密的文本分析,描繪文學語言如何有別於日常語言、文學世界如何有別於現實世界,呈現出文學中暗藏的邏輯織網,爲我們理解‘文學之爲文學’的根基提供了深刻洞見。”因此,《詩的邏輯》試圖解決的恰是“文學本體論”問題,作者在“導論”中說:“詩的邏輯更多是出自這一狀況,即語言作爲文學的構型材料,同時也是讓特殊的人類生活得以完成自身的媒介。”這句表述把“詩的邏輯”的體察對象從狹義的“詩”的體式拓展到以語言爲媒介的整個“文學”領域,同時也強調的是“語言”之於文學的本體意義,以及如果沒有詩的邏輯,沒有文學性,那些“特殊”的人類生活,那些人類深廣、博大、蘊藉但也難以捕捉的精神生活就難以找到更好的傳達和表現的材料和媒介。這是我近些年讀到的關於何謂“詩性”以及“文學性”的最合心意的闡釋。商務印書館的副總編輯鄭勇在座談會上稱這套叢書如同“內心豐盈、外表謙和、節制蘊藉、溫潤如玉的君子”,也別緻地概括出了“文學×思想”譯叢所表現出的深閎而溫潤的文學性之美。
我們以往一直受惠於布拉格學派關於“文學性”的陌生化理論,而這套譯叢也展現出詮釋文學性的一些新範式,尤其是文學現象學、語文學以及詩學模式。例如李茜翻譯的美國學者安格斯·弗萊徹的《諷喻:一種象徵模式理論》、張沛翻譯的吉爾伯特·海厄特的《諷刺的解剖》,處理的都是詩學領域最讓研究者感到繁難的經典議題:反諷、諷喻以及諷刺。當弗萊徹把諷喻解釋爲一種“象徵模式”,“諷喻”也就上升到理解文學的“本體論”高度。這套譯叢也有助於我們從近幾十年來深陷其中的“相對主義”泥潭中超拔出來,再度迴歸文學的某種“本體論”框架,迴歸奧爾巴赫既紮紮實實,又睿智淵深的“語文學”視野。
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張輝教授有過一個流傳甚廣的段子:“如果只能帶一本文學理論書去人跡罕至的荒島,而且再也回不來了,我會選擇奧爾巴赫的《摹仿論》。”這個說法堪稱把奧爾巴赫型塑爲20世紀文學理論界的一個難以替代的神話。而這套譯叢中高冀翻譯的奧爾巴赫的《伊斯坦布爾講稿》,相信會爲中國讀者的“奧爾巴赫”熱推波助瀾。在譯者序中,高冀指出:“語文學構成了奧爾巴赫文學史書寫的基礎。”自從薩義德在給《摹仿論》寫的“50週年紀念版導論”中強調奧爾巴赫是一位“語文學家”,其方法的精髓是一種“源自德國闡釋學傳統”的“語文學解釋學”,語文學就成了讓中國讀者“不明覺厲”的一個概念。而在《伊斯坦布爾講稿》的“導論”中,奧爾巴赫給出的是一個關於“語文學”的簡潔明快的較爲親民的定義:“語文學是運用某種方法研究人類語言的各類活動之總和,以及用該語言撰寫的藝術作品。”譯者高冀進一步發揮說:“按照這一定義,語言學研究和文學研究均是語文學的分支。”可見在奧爾巴赫那裏,語文學是基礎中的基礎,由此也可以瞭解爲什麼這種語文學方法同樣系統地貫徹於斯內爾的《精神的發現》一書之中,就像陳鬱忠在譯後記中概括的那樣,語文學考察也是整部《精神的發現》的基石,而斯內爾“對人類思想或者說‘精神’的考察不再是純粹的哲學思辨,而是歷史的,訴諸語文學的研究。這在斯內爾的著作中體現爲從語言轉變看思想轉變、將‘語義學’轉變爲‘思想史’或者說‘精神史’”。《伊斯坦布爾講稿》以及《精神的發現》,都爲中國學界提供了深入認知“語文學”的新視野。
張輝教授在發佈座談會上提及,“文學×思想”譯叢的第二輯也在編輯出版過程中,其中包括兩本奧爾巴赫的著作。這不禁讓包括我在內的中國奧爾巴赫迷們摩拳擦掌翹首以待。

吳曉東,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