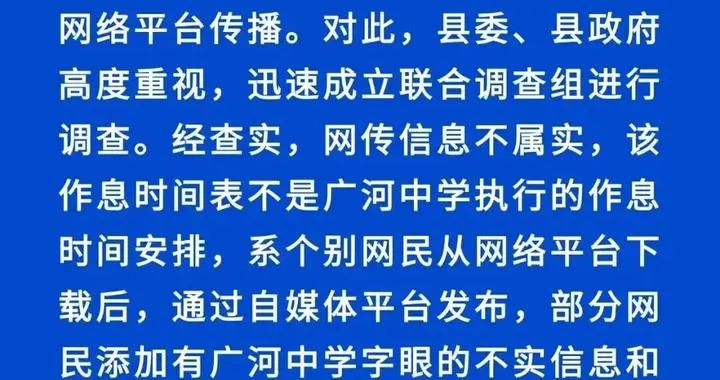從燒烤攤、保潔間與石材廠而來,那些“煙熏火燎”的文字讓無數人“心頭一熱”


近期,隨着花城出版社推出“新大衆文藝叢書”,“清潔女工作家”瑛子、“燒烤詩人”溫雄珍、“石頭詩人”曾爲民、“體育老師作家”章新宏等出現在人們視野中。從《擦亮高樓——清潔女工筆記》《從江右到嶺南》《東莞時間》《趕石頭的人》《有些光不會消失》到《在炭火上安居》,他們的文字裏帶着各地的鄉音與生活的“煙熏火燎”,彰顯着新大衆文藝旺盛而炙熱的生命力。

花城出版社“新大衆文藝叢書”書影。
很多讀者因爲他們的文字心頭一熱。“這個時代最多的是間接經驗”,而新大衆寫作中呈現的“直接經驗”,比人們想象中還要熱氣騰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教授劉大先認爲:“文學的核心功能是跟他人產生同情共感,寫作首先是自我表達的需要,正如有的人喜歡釣魚,有的人喜歡泡桑拿,‘我喜歡寫作,這是我的一種生活方式’——真正意義上對普通民衆的情感發生作用,對他們的認知發生影響,這樣的作品就是新大衆文藝。”
正如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楊慶祥所說:“人人可以把自己的故事,把自己生命的體驗書寫出來,抵達讀者,引起共鳴——這是我們這個時代非常重要的文學現象。”
第一次:深沉的樂觀
瑛子出生在1966年山村,那時沒有看過車,沒有看過橋,連一塊鵝卵石都沒看過。因此她有很多“第一次”,“新鮮”也經常出現在她對生活的感受中。她只上了8年學,但一直沒有放棄閱讀。
退休後,快60歲的瑛子第一次當上了保潔員。2008年,120元火車票,坐了40個小時,她從此在東莞做幼師一直到退休。她不是天生會喫苦,她只是想在經濟上多幫襯兒子。於是,這個新人保潔員第一次走進清潔的樓盤,第一次認識各類保潔用具,第一次連續拖兩個小時的地,她承認“很困難”,但還是決定堅持一下。“生存第一”是她的原則,但她把很多不同處境的人寫下來了,也就成了一本記錄一羣清潔女工的書《擦亮高樓——清潔女工筆記》。

“在樓盤裏看到了很多新鮮的事情。那羣保潔工,很多不識字,比如說要回家,家裏人送他們上火車,他在心裏面一定要記住具體的站名。有一個1.4米高的‘小矮人’,找工作非常困難,經理本來不要她,組長就說‘你摸摸她的手,全是繭,幹活非常能幹’。她穿工服比較長,經理就幫她剪一截,把她安排到人比較少的地方做清潔。我看到了這麼多人,聊他們的生活,很不容易的時候會流眼淚,我就把他們每天講的寫下來。”
這是有生命的寫作。瑛子每天走進這個世界,會欣喜,哪怕是面前的樹、花、草,她說哪怕是看到它們生長在那裏,都覺得值得寫。可“蟲子”在她負責清潔的大堂中就被認爲是垃圾,需要被清除,她選擇用紙巾捏着蟲子放它到窗外去。“當你從生活中感受到哲理,文字是最好的方式。我就把這部分提取出來,這是我的發現。”瑛子說的是那些生活中無法界定的瞬間,她也疑惑,但她的笑容中總有一種柔軟與堅硬,不會因此過度困惑,亦堅定地不放過。

六十歲的瑛子有很多第一次,但寫作早已不是她的第一次。東莞17年,她一直在寫作。“年輕時朋友阿林送我很多《詩歌月刊》,我拿回去讀,我‘燃燒’起來了,我開始寫詩歌。再之後我開始記錄家鄉,完成了13萬字的《翻轉的村莊》。”瑛子知道寫作養活不了自己,“是一種陪伴,陪到你覺得寫出來就暢快了,很多感情找不到人傾訴,寫作會讓生活豐富一些。”
瑛子的“第一次”中還有着很深沉的樂觀。“進到清潔的樓盤裏,因爲它正在建造,帶來很多生命力。”也可能正因爲這樣的視野,她才反覆地、平靜地說:“我不怕往前衝。”那會寫到什麼時候?“寫到我自己能看得到、摸得見、聽得見的那種狀態,我再放手。”
每一天:煙熏火燎的生活裏
正如他們一天天過着生活,他們也一天天寫作着。溫雄珍在菜市場擺攤二十六七年,發表了十萬多字,寫下了可能更多。
詩歌《燒烤架上》的第一句是“沒有人能從那場炙焰中把你解救岀來”,靈感來自溫雄珍凌晨一點多打開的熱水器。“凌晨下班回家,我洗澡時打開熱水器,上面的火焰跳了起來,就想到了這一句。一直寫到四點多,太困了,把手機一放,明天再修改。”

溫雄珍有一家童裝店,同時還是燒烤店的服務員。她的一天“擠”着蔬菜與鼎沸人聲,但重頭戲總是寫作:早上7點開店,下午4點半收檔去燒烤店上班,直到凌晨12點半收工。下班路上就開始寫了,如果有靈感,回到家會寫作到四五點鐘。“我們中年人,有老人,有小孩,每天都在煙熏火燎的生活裏面。但晚上很安靜,適合去思考。”
溫雄珍身兼多職是有原因的。二十年前丈夫發生車禍,她擔起養育兩個幼子的重擔,一度堅持不下去,但“我是一個母親,因爲從小沒有母親,我就不可能讓我的孩子經歷我曾經經歷過的日子”。一種可能代際傳播的痛苦被她強力抵消。她也看見他人生活裏的痛,經常路過她店面的清潔女工,也遭受着家庭的失衡,溫雄珍把她寫進詩裏。“我喜歡看她擰開水瓶蓋的動作,那裏有悲傷,她總是擰得太緊。”溫雄珍噙住淚,“字面上不見悲痛,但寫一種內心的掙扎和悲痛在裏面。”
很多讀者讀完這位“燒烤詩人”的詩,留下了“同一滴眼淚”。“我用最輕快的語言把內心最痛苦的東西表達出來。很幸運能看到,這些能變成我的詩歌,變成我的營養,對我是一種獎賞。”溫雄珍把詩歌看做一片留給自己的乾淨的精神之地,可她沒想到,有更多人因爲她的詩,對冰冷的生活有了溫熱的理解。

出版《在炭火上安居》之後,她表示仍然會“繼續努力,繼續生活”。正如她在《生活》中的詩句:“如果生活只剩下輕盈,那麼日後,我就失去可炫耀的談資。”
一羣人:“他們也在創造生活”
當被問及“從幼教到做清潔,會感受到反差的眼光嗎?”瑛子坦然地說:“他們也在創造生活。他們的生活也是我們的生活。”
《趕石頭的人》出版,曾爲民被稱爲“石頭詩人”。“石材是我寫作的礦場,就像在燒烤攤,在童裝店,都是一樣的。”他是石材廠的銷售,在他的眼中,每一塊石頭有生命且有情。1985年還是高中生時,曾爲民就爲詩歌狂熱。寫詩幾十年,曾爲民看到了石頭的詩性,“一個詩歌愛好者的成熟,是‘格物’,要把物拿出來,把人放進去。一個人的成熟,也從他能替別人着想開始。石頭是出世的,但它被越磨越亮的時候,會跟人發生更多關聯。”

體育老師章新宏的文字還留痕在不同年代的各類媒介——QQ空間、微信朋友圈、分享文字的APP以及學校的報紙。“我要讓大家看一看我們體校的學生是怎樣的,辦了一個《新苗》校報,在我們學校開展全民寫作,從我開始帶頭寫,然後是老師、教練、學生、家長,全部都可以寫,發表在《新苗》校報上。”這些年的積累,慢慢成了章新宏的書《從江右到嶺南》,而現在,章新宏還召集了一個“小南瓜文學社”,慢慢做着文學的工作。

這些新大衆文藝的寫作者,用筆構建了一個世界,打磨文字的時候,也在打磨自己的生活。就如溫雄珍在《畫》中寫下的那句:“在馬路邊,守着菜攤/他不會知道,在這刻/他做的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