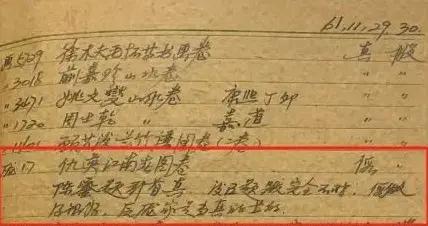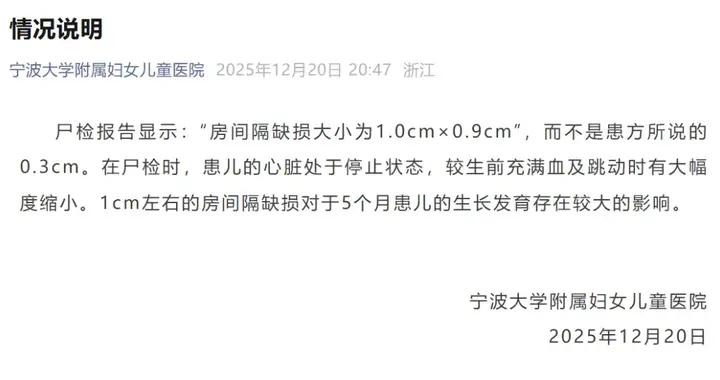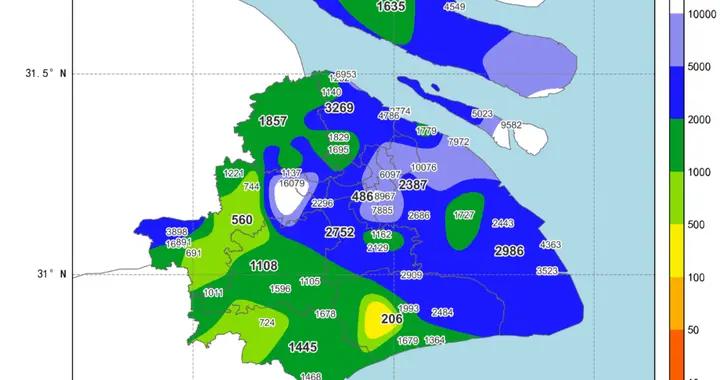【給黎明寫着信】“你這是品種桃,最多活十五年” | 連芷平




本文配圖均由作者提供
一
立秋後,院子裏的爬山虎經歷了一場緩慢的燃燒,日光和露水皆成爲它的燃料,它的每一片葉子都是一朵火苗,從滿牆深淺不一的綠,直燒到黃紅交錯,然後像撕下的日曆那樣隨風飄走。我知道,它日夜都在燃燒,安靜地燃燒。我多麼喜歡這火的意象,卻無法拍攝下整個過程,因爲這火焰只以爬山虎自身的慢速度運作,我的肉眼只窺見它最表層、最平面的顏色。
桃樹開始落葉,一片,兩片,如果一陣風來,便是紛紛飛葉,掛滿桃膠的枝杈瞬間空蕩了起來。這個過程持續了數月,演繹着屬於桃樹自身的時間儀式。半年前,我請果農給這棵桃樹打枝,果農說,它只剩下三年壽命。我大爲驚詫,難以想象它看起來如此青壯,竟已到了耄耋之年?而且,樹木的壽命不都比人的壽命長嗎?果農說:你不懂,野桃活得久一點,你這是品種桃,最多活十五年。我認真數了數,確實,這棵黃桃移到此處時已是一棵大樹,那麼,當時便是個中年人了。這麼看來,我這個真正的中年人送桃樹一程,是不久後必然要發生的事了。

秋天的小院裏,不變的只有枇杷樹(上圖)和橘子樹,它們保持着恆常的綠,像人們說的“情緒穩定者”,以感人的鎮定安慰着我:並不是一切都會變,明年春天,桃樹和爬山虎的每一片葉子都新來乍到,而我們與你仍是故交。
故交一詞,讓我想到最近和曉麗的聯繫。她告訴我她獲得了一項新的能力:用黃荊製作鹼水糉。曉麗詳述她的試驗:如何尋找黃荊,曬至半乾,用小鍋燒成灰,用咖啡壺過濾,最後將制好的鹼水存入冰箱。鹼水糉是我熱愛的食物之一,曉麗的分享讓我躍躍欲試,甚至想赴她而去,一起手作實踐。但曉麗這些年常入駐藏區寺廟,行蹤不定,爲了一鍋鹼水糉讓她從藏區回閩南,未免太過分了,只能等以後再說。我與曉麗相識二十年,起初十年,是我四處亂跑,在世界的各個角落與她郵件往來,然後,換成是她。有時我覺得,曉麗彷彿在替我體驗着我所不能及的某種人生,或許,她同樣覺得我在替她感受另一種生活。這種生命的互文,讓我們的友誼超越了尋常的定義。
二
小院像一塊畫布,節氣、陽光和植物在上面交織出每一天都不盡相同的畫面。這令人着迷的變幻光影,讓我在每個清晨拉開客廳的白色窗簾時,都會湧起一陣深切的感恩。我頻繁地想起梅洛迪·貝蒂的話:“感恩能解鎖生命的豐盈……它將拒絕轉化爲接納,將混亂轉化爲秩序,將困惑轉化爲清晰……它讓我們理解過去,帶來當下的平靜……”
實際上,四個月前,小院經歷了一場自然災害。盛夏時我遠行歸來,發現所有精心栽種的黃瓜、番茄和近十盆香草都在這場與酷暑的對決中全軍覆沒。回想初春種下它們的那一刻,我是何等雄心勃勃,彷彿已預定了一場碩果累累的秋收。
雖然爲它們施肥的技藝是我至今未能參透的玄機,但我曾那麼專注——修剪側枝,將剪下的枝條重新插入土壤,觀察它們生出細弱的根鬚;爲日漸高大的番茄搭起支架,甚至學會了將番茄放倒,並在根部覆上新土,據說這樣能讓植株更健壯、結果更豐碩……但這些努力都付諸流水,烈日將番茄的葉子烤得焦黃,我的一趟遠行,成了擊潰它們最後的稻草。
我安慰自己,我沒有做錯什麼,番茄也沒有,就連酷烈的日頭也只是遵循着自然的本性,但這些緣故的交集,卻造就了不能挽回的殘局。誰說種瓜一定能得瓜,種豆一定能得豆?回望我的前半生,不也常是種什麼而不得什麼嗎?種而不得,相比於種有所得,或更是生命常態?陶淵明都要感慨“草盛豆苗稀”,我亦要坦然接受這一切,放過番茄,放過自己。
進一步說,在某些事情上,人需要一個真正的觸底。正是這樣的觸底,讓另一片更爲遼闊的大地得以浮顯。陶淵明的另一句詩“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如今讀來,彷彿亦是爲我而寫。
三
上週,我備好一個屏息靜氣的下午,將幾個月前不慎摔碎的一尊小佛像黏合修復。這是一尊民國燒製的德化窯白瓷觀音小坐像,並不多麼珍貴,但有着很美的開臉,我一直將它放在書桌上可以直視的地方。摔碎時,懊惱不已,只能小心翼翼地拾起所有碎片,放進抽屜。所幸,修復後的佛像雖然佈滿裂痕,頭部卻是完整無缺的,它的安詳與神性已然迴歸。
我將帶着裂痕的神像重新放到書桌上,伸手就能夠着。從它身上,我感受到一種力量——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信仰支持,而是別的什麼。在拼合它的過程中,我與自己對話:如果這只是一件普通瓷器,我大可以說它是自我的物化,我拼合着它,就像在拼合自身的裂痕。但它是一尊佛像,我便不能簡單地將其視爲自我的投射。那麼,它究竟是什麼?是某種超然存在的命運象徵?這個問題讓我的大腦經歷了一陣短暫的休克,但最終這尊神像因裂痕而呈現出的格外的寧靜與尊嚴,讓我覺得,我似乎領悟到了某些神諭。
我決定明年開始,不再計劃種番茄、黃瓜和香草。放棄種菜領域的“深耕”,並不意味着我深受打擊,相反,是這些觸底的事件讓我對自己有了更深的認識:什麼是我應該持之以恆的,什麼是我應該告別的。我對應該告別的事並無執念。做好力所能及的事並盡力做到極致,放棄無法繼續的事,讓它們從腦海和計劃中消失,乃至與之相關的記憶也可一併刪除。因爲,大腦空間有限,要留給那些“應該做的事”。
——比如,創作圖像。一系列新的圖像朝我湧出來,在我的大腦裏奔流。但我曾經擁有的那些相機,或丟失,或損壞,或贈與了他人。於是我馬上付諸行動,淘來一套瑪米亞RB67。這套相機產於1990年,當時售價高達12800元人民幣。由於那個年代國內影樓業盛行,瑪米亞RB67幾乎成爲影樓專用的“戰鬥機”——其純機械和重機械的設計,讓它少有故障,壽命超長。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影樓業人去樓空,這些身經百戰的瑪米亞流入二手市場,因存量龐大而價格親民。當一套瑪米亞相機因自身的歷史和變故,出現在同樣有着自身歷史和變故的我的生活裏,我們之間想必符合了某種量子糾纏,這讓我捧着重達3公斤的它時,百感交集。
我從儲物架上取下塵封已久的三腳架,爲相機配齊戶外補光燈和快門線,購入一批價格不菲的膠捲,甚至添置了鎂合金拉桿相機箱。我開始嘗試將頭腦裏的草圖一一畫下來,對創作的新構想令我處於幸福的狀態中。
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創作新圖像的衝動了,這是我生活中的不幸事件之一。這種不幸,看似可歸咎於“運氣不好”,實則是命運在向我發出對話邀請。如果我意識不到自身的侷限和弱點,命運就會以各種方式讓我反覆與這些不幸相遇——直到我改變自身,才能真正邁過這些障礙。從這個意義上說,每一種困境,都是命運爲我“量身定製”的。
因此,“運氣不好”的事,實則彌足珍貴。我們習慣於追求舒適,當不幸的事將我們拋入與平日迥異的某種狀態,讓我們與自我無限接近時,這接近總讓人恐懼。於是我們常做的,是爲各種不走運尋找合理化的解釋,而非勇敢地展開不舒適的自我審視。我領悟到,命運不會像交通警察那樣,在我們不合理的前行途中隨時出現,用擴音喇叭向我們高聲喊停。命運的對話邀請像宇宙發來的電波,需要我用心察覺,也只能靠自己努力釐清。
我時常放下手中的事,在電腦前坐下,將湧出的紛繁感受記下來,清理、歸類、挖掘、反思、感悟、規劃。這便是近年來,我在認識自己的方式上持續發生的一種個人變化——類似爬山虎在秋季的自我燃燒。
四
八月後,我一有空閒就上跑步機,將肌肉量提高到了75%。運動是我贈予自身耐力和心肺功能的禮物,並且,它讓我享受到源源不斷的多巴胺——有時,我真想給跑步機寫一封情書……我將跑步機放在次臥窗口,正對着一面碩大的玻璃窗,一個夜晚,我在黑暗的跑步機上爬坡時,客廳的光線從背後投來,將我身着跑步服的輪廓模糊地映在玻璃上,令我一陣疑惑:前方鏡中朝我走來的身影有些眼熟,像在哪裏見過,想了又想,想到了漫威電影,因爲鏡中人的步伐,頗像漫威電影中戰後歸來的主人公——無論她剛經歷了一場勝仗,還是一場敗仗;無論她的兵器是否折翼,鎧甲是否破損,都以從容的姿態歸來。我喜歡這種超越性別的從容。

或許我終於可以說,現在,我找到了與自己同頻共振的居住空間:與樹木爲伴,與飛鳥共處。當我能夠一天10小時坐在書桌邊,凝望院中植物與風、雨、光、飛鳥的互動時,我相信這樣的日常是具有“靈光”的(本雅明所言的“AURA”),它讓我的感官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敏銳。我熱愛這豐沛的孤寂。
吾友常說我晚熟,他們認爲這是某種“幸運”,他們多以令人敬佩的早慧獲得了成就與榮耀,但也承受過聲名的負累,甚至是磨難。我說我晚熟是真的,不過,現在也還沒熟,等熟了再跟你們說,說不定我終身不熟。
“生活的意義不在於抵達,而在於前行”,這些並不驚人的話語,容易讓人過目即忘,但它在某個靜默的時刻重新對我湧現,這又是一個微小的“量子糾纏”,讓我識別到這句話的深處藏着與我的個人生活相關的符碼。此刻,從書桌上抬頭,看着院子裏的桃樹,它正在凋落最後一批葉子;旁邊的枇杷樹,在秋季的濃綠葉間開出了花;而背景裏的那牆爬山虎,依舊在分秒不息地燃燒。植物有自己的時間性,彼此各不相同,人有自己的時間性,亦彼此各不相同。
只要敢於自我承擔,終身不熟,又能如何?
【給黎明寫着信】是連芷平在筆會的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