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不能涵蓋中國所有的邊境“牆”



《從“分治”到“整合”:明清湘黔邊牆歷史演進與結構變遷》是一部研究中國南方邊牆的史學佳作,以明清湘黔邊牆爲研究對象,系統討論了其修築前後的歷史演進與社會變遷。作者運用大量圖、表、實地調查圖片等,具體考訂了明代邊牆的起止路線,分析明清政府修築邊牆的軍事控制,探討明清湘黔邊牆的演進過程、湘黔邊區的社會整合與族羣交融等情況,並將湘黔邊牆與北方長城做對比。書中總結了明清中國在邊疆的治理得失,揭示傳統中國地域民族社會的治理方式與運作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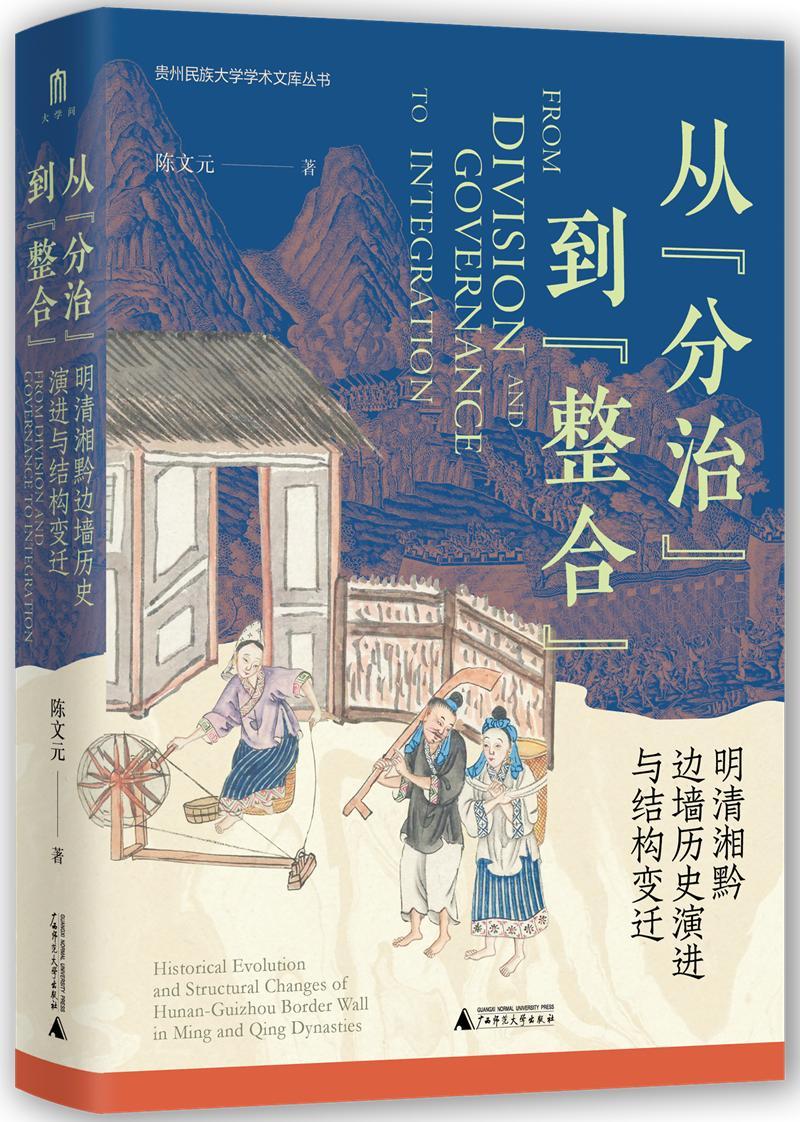
《從“分治”到“整合”:明清湘黔邊牆歷史演進與結構變遷》,陳文元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內文選讀:
治理邊緣與經略腹地——南方邊牆與北方長城之比較
縱觀中國歷史,自先秦至明清,不論南、北,有關“牆”的修築與維護不絕於書。剖析“牆”的歷史敘述,對比南、北“牆”的延續與轉換,或可窺探傳統中國推進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和鞏固過程中統治理念演替與經略思維變遷,從而進一步總結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政治統治脈絡與多元治理方略,爲今日之民族地區社會治理提供經驗教訓。
明代南、北皆築“邊牆”,不能不說是巧合。考慮到明代爲抵禦北元/蒙古勢力,在北方大範圍修築長城,爲解決南方“苗患”又修築邊牆,治理思維或有相應延伸。明代在北方修築長城不遺餘力,於南方修築邊牆同樣耗費甚巨,跨越時間較長。雖然南方邊牆與北方長城在性質與特點上皆有不同,但大致體現了明朝中後期解決地方動亂與調控族羣關係的一種思維借鑑。
南方邊牆與北方長城有着各自的特點。拋開二者的懸殊地位與建築形制差異(譬如建造方式、防衛佈局、工程裏數),彼此在制度實踐、治理內涵、政治屬性、文化形態上有着重要區別。
制度實踐上,明代在北方大規模地修築長城,是在推翻元朝統治後防範北元/蒙古勢力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更與土木堡之變後明朝軍備實力下降,不得不採取守勢有關。其制度實踐是因循歷代中原王朝面對遊牧政權的邊疆經略思路,輔之明代衛所制度和屯邊募兵體系;南方修築邊牆則是明廷針對傳統的“剿、撫”民族政策失效,州縣體系又無法推進,因而沿續衛所/營哨結構佈施邊防,後雖營、哨累加,增堡築牆,但總體思路仍是衛所防衛體系的延伸。

高塘石邊牆
治理內涵上,明廷在南方修築邊牆,秉持對南方民族地區的深入治理與策略改制,雖爲“禦敵”,但主要“治夷”,是對腹地統治區域的強化與控制。但明廷在北方修築長城,打造九邊重鎮,長期與北元/蒙古勢力對峙,兩者的實力轉換與戰和不定,北方軍事重點既是“治夷”,更是“禦敵”。
政治屬性上,北方長城在中國歷史上曾是中原王朝與北方遊牧民族政權的“邊界”,以長城爲界,南北對峙,乃地緣政治與文化結構交織的產物;南方邊牆實爲圍繞“內地的邊緣”隙地的治理與控制,乃直接統治範圍內的治邊、安邊軍政舉措與社會治理,顯然不是由兩類政權體系間的交替引發。二者在政治屬性上有着本質的不同。
文化形態上,南方邊牆所處區域雖在腹地,但又極其邊緣,境內高山深壑,溪流縱橫,多族羣分佈,地域環境複雜;北方長城沿線則處在草原與平原之間,雖也是建在山嶺之上,但總體地勢相對平坦,遊牧與農耕長期交融共生。地域生態並不相同。地理形態對應的地域氣候與經濟文化類型更是有着顯著差異。南方邊牆屹立於湘黔邊區,處在華南漢族與西南少數民族的過渡地帶,區域內文化形態多樣,族羣關係複雜;而長城所處的北方地帶長期以來是中原漢族與北方遊牧民族交互的舞臺,二者關係時常影響到中國歷史發展進程。
更應看到,南方邊牆對應的“西南邊疆”與北方長城對應的“北方邊疆”在中國整體歷史進程中作用的差異性。長期以來,遊牧與農耕兩股政治勢力交互,主導了傳統中國政治統治脈絡演進。相較於西南邊疆,北方邊疆更緊鄰中央王朝統治腹心,政治統治輻射力更強,文化結構更趨穩定,再經由元明清大一統中央王朝經略,北方邊疆整體上呈現出更高的整合度;而西南邊疆族類衆多,地方勢力紛繁複雜,“多國林立”卻又政治影響較小,地處邊緣卻又遠離政治中心,中央王朝很難實現全面的直接治理,更無法有效統籌整齊劃一的政治統治,故而長期羈縻而治、間接控制,也因此缺乏一以貫之的整合力度,此類狀況緩至清代雍正朝改土歸流才得以改觀。換言之,清代湘黔邊區改土歸流後,仍然產生了“邊牆”這一歷史產物,與先前的整合程度和區域差異密切相關。

喜鵲營
如果從傳統中國邊疆治理的政治邏輯上來審視,明代南方邊牆與北方長城又具有一定的共性。歷代中央王朝治理邊疆/邊緣,處理與周邊各族的關係,王朝統治者皆須認真對待,且是無法迴避的政治議題。中國邊疆的最基本特徵就是它的民族性,不論南方邊牆,抑或北方長城,皆爲明廷應對邊疆/邊緣複雜社會形態與多元族羣結構情形下,建立賴以治邊固界的軍政型管理系統,是傳統中國邊疆統治方略的體現,尤其涉及邊防危機,或遇突發事件、重大災害時。也就是說,邊牆抑或長城,乃是中國古代中央王朝基於地理結構與社會形態的“因地制宜”和“因俗而治”之策,修“牆”不是目的,而是一種統治策略、管控手段。邊牆是劃界治理的重要載體,重在區隔而非隔離,況且邊牆內外均有一定的經濟文化交流。明代國家治理體系中,有州縣、衛所、土司等政治管理體制,南方邊牆與北方長城皆體現了傳統中國邊疆治理體系的靈活與彈性,折射出傳統中國邊疆制度的整體結構與區域差異的歷史性因素,是爲“多重型結構”下的“多重型天下”。保持彈性的治理架構與多元的治理方略,是推進傳統中國統治穩固的重要前提。
進入清代,北方長城的角色已然發生轉變,其軍事功能逐漸退化,非軍事功能日益顯現。不過在清初,長城依然具有較爲重要的軍事屏障作用,“禦敵”性質仍存。清廷爲應對漠北蒙古的進攻,還曾予以修繕。隨後長城的功能主要是限制出邊/入邊、管理貿易和朝貢,演變成清朝溝通中原及藩部的交通要道。清中期以後,當北方長城愈加顯現出融合內外的象徵情形時,清廷又在南方重修邊牆。清代邊牆與邊防體系是對明代邊牆防禦體系的繼承與深化,但卻不是簡單的“歷史複製”,二者有着不同的歷史語境和建構策略。與明代修築邊牆有所不同的是,清代基於“治苗安邊”宗旨,將邊牆作爲治理湘黔邊區重要舉措,並以軍事防衛與治安保障體系經營,區隔苗漢、分而治之,形成了邊牆治理,重構了族羣關係,引發了湘黔邊區社會變遷。此時,與北方長城相比,清代邊牆的軍事功能與非軍事功能均比較突出。
與此同時,明清中央王朝在南方修築邊牆,亦體現出傳統中國統治思維缺陷。在傳統中國的統治邏輯裏,當動亂髮生或族際衝突時,中央王朝多偏向於“壓”的解決手段,隨後纔是“撫”與“疏”。基於這一點審視,亦不難解釋爲何至清代,當北方長城已失去其防衛功能時,南方依然會有“邊牆”這一產物。“牆”的“廢棄”與“重修”,是傳統中國在南、北地域政治統治脈絡的演變。歷代中原王朝於北方不遺餘力地修築長城,但清代大漠南北一統,北方不再需要長城御邊,統治者較爲得意於此,卻又在南方不得不按照明代的方式再築邊牆。湘黔邊區不同於北方草原地區,其對應的是南方民族地區複雜的地理環境與多樣的族羣交互,且長時期以來統治基礎較爲薄弱。修築邊牆,釐清民、苗界址,重在“因俗而治”“民苗相安”,彼此尊重,天下一統,既突顯了傳統中國統一性的整體維持與差別化治理方式的延續,更反映了中央王朝將“夷民”向“編民”整體轉化的政治結構轉型。
更應看到,中國歷史上從來不缺乏“牆”的存在,修築“牆”以及圍繞“牆”的經營與維護可視爲傳統中國的一種統治模式。然而,學界目前尚未重視這一問題,且多集中於北方長城的討論。其實,中國古代有關“牆”的含義極爲豐富。筆者粗略認爲,如要理解傳統中國的政治統治,一是不能談“牆”色變,更不能把“牆”統統固定理解爲“軍事防衛”“隔離”“鎮壓”等。事實上,圍繞“牆”的修築與維持,往往是衝突與和睦並存,牆內外人口、道路與聚落交互,界內外人羣開展各類形式的經濟文化交流,交融互嵌無時無刻地不在發生着;二是要看到中國古代“牆”的多樣結構與內涵。北方長城從遊牧與農耕的政治脈絡演化至中華文明的象徵,但其不能籠統概括中國所有“牆”的政治內涵與文化細部。比如,南方即有“楚長城”“滇東古長城”以及本書探討的位於湘黔邊區的邊牆,有些“牆”的歷史甚至要比北方長城的歷史更爲久遠。簡言之,對這些“牆”的闡釋都不應大而化之地貼上“長城”的標籤,或者說不應該被北方長城的內涵覆蓋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