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與肉體的遷徙中尋求人的依止——楊獻平散文集《成都煙火日常》芻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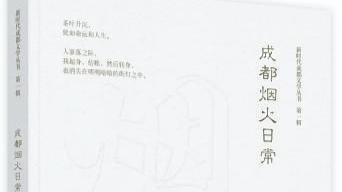

蕭勁廷
從時常“舉着腦袋向外張望”的南太行故鄉,到曠極遼遠的巴丹吉林沙漠軍營,再到“富麗沃饒、幽祕深藏”的天府之國。作家楊獻平用匍匐在地的審慎態度,解剖着自身對環境變異所引起的情感遷徙。作爲一個寓居成都十餘載的文學創作者,楊獻平始終以遷徙者、異鄉人自待,在最新散文集《成都煙火日常》中,他以洋洋灑灑15萬字篇幅,展示出一個“外來者”,在與蜀地環境融合過程中遺留下的雙重創痕——精神創痕與肉體創痕,同時也展示了這兩重創痕在蜀地物產、風俗、氣候、植被等要素的治癒下,自身的療養過程。
一直以來,我們習慣以“土著者”的心態與視角,參與到這片土地以及建立其上的文化符號的討論之中,並理所當然地得出“煙火”與“脂粉”氣息濃厚的成都市井景象的結論。誠然,在對《成都煙火日常》的冷靜閱讀之前,我如德國接受美學代表姚斯所言,大腦中並非一片空白,而是以慣常的經驗與感知方式去開展我的“成都日常”接受旅程。然而,楊獻平雖自嘲爲“俗世中人”,卻在漂泊與安居的彷徨遲疑中,在接受與反叛的情感拉扯中,將筆觸深入到成都的公共生活與微觀世界,並以家庭的重構作爲新的情感錨點,在自我身份的轉向中參與到這塊地域及其文化的討論與靈性思索之中。我以爲,這比文本內容本身,更加優雅、玄妙。
楊獻平繼《故鄉慢慢明亮》之後,再一次將自己的肉體同遙遠的“南太行”相連接,只不過這一次承託其思維與記憶的載體,變成了“內斂、獨我”的成都市井。文本簡潔練達,絲毫不露雕琢之痕,既是對以成都爲中心的蜀地名跡史脈、風物習俗、價值意識等的宏觀把握,也是對隱伏在表層現象之下的“漂泊者”的微觀探索。楊獻平正是以與鄉音、鄉俗、鄉人的疏遠,來反窺自身從鄉土剝離以後的矛盾情感,這在《入蜀記》《最初的成都——兩句詩和個人內心生活》《自我的安居與引渡》中可見一斑,其以這片陌生的地理單元作爲情感的發生原點,淡定且從容地講述着自己從一個“異鄉人”逐漸向着“被同化”靠攏,在思想情感的無休止波動中,在與陌生場域的殘酷搏鬥中,楊獻平找到了新的依止之所。於精神而言,他以真誠的方式去緊貼這塊土地,感受浮於其上的溫與涼,同時,也得到了這塊土地給予的包容、熱情的反饋。於肉體而言,他在潛移默化地被影響中,完成了家庭的重構,同時也爲自身建築起了新的“避難所”,從而裨補了精神遷移過程中所受到的無形戕害。此外,楊獻平還是一個善於“貼着大地行走”的創作者,在隱、避於喧鬧之外的文殊院,在“寬”與“窄”兩種人生尺度間穿梭的寬窄巷子,在歷史與現實交疊的武侯祠,楊獻平不止一次將客觀地理物象上升爲自身的情感慾望表達,在聲勢浩大的實錄式書寫中,鐫刻出普羅大衆最容易被忽視的微觀羣像。例如《文殊院內外》《寬窄之間,支磯石焉》《錦官城中武侯祠》《大慈寺與春熙路》等,均是其由微小而見宏大的真誠書寫。
寓居成都的楊獻平是矛盾的,他一面叮囑自己看清與成都地域的“天然隔閡”,又不得不在潛意識中承認這種地域對人的同化之力;他一面厭棄對自身個體差異性的消磨,又不得不在陌生場域產生如古斯塔夫·勒龐所說的“趨同”。他的這種矛盾,或自於身體上的病痛折磨,或自於精神上的無所依附。如浙江大學教授王紀武在其《人居環境地域文化論》一書中所言,作爲依附地域與地域文化之上的“活載體”——“人”的流動在規模與範圍上將是空前巨大的,在這樣一種流動中,去討論文學創作者的恆定歸屬,顯然如鏡中花、水中月一樣難以確指。王蒙曾就冰心的地方歸屬談到,冰心祖籍福建,幼居齊魯,學於美國,而後長居北京。在諸如此類的地理流動上,創作者本身與其所創作的文本,難以在特定的地理單元中標定其所攜帶的精神符號與文化皈依。
人文主義地理學大師段義孚曾言,絕大多數被我們感知到的事物都有其價值,或是爲了生存,或是爲了獲得“某種文化中衍生出的滿足感”,從山鄉到曠野,從荒漠到人海、車馬,楊獻平在《成都煙火日常》中,遊心騁目,恣肆不羈,既表達了對時下熱門話題——“遷移”的深度探索和情感共鳴,也在這場“遷移”中,以一個“外來人”的身份持續強化着自身對陌生地域的體認。他的立場是明確的,他的表述是直觀的,以此呈現出對成都持久和難以言說的“戀地情結”,並從中導源出了一場“極爲深刻的人生經驗總結”。
(作者系西南科技大學文藝學碩士在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