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作爲對世界苦難的質詢——託芙·迪特萊弗森長篇小說《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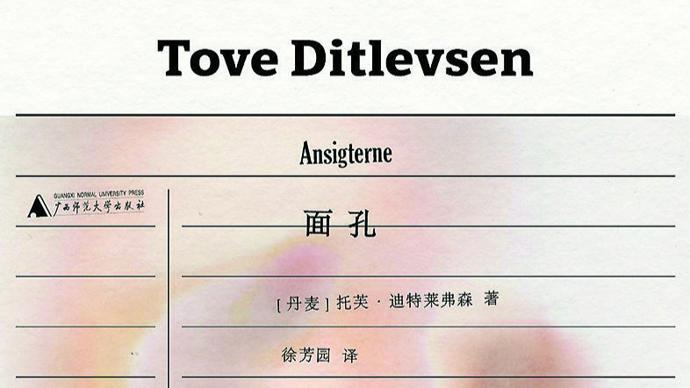

在邁克爾·坎寧安的長篇小說《時時刻刻》(The Hours)中,坎寧安設置了處於三種時間線索中的三位不同女性,其中對於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刻畫生動而深刻。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關於“兩個世界”的一段劇情。那日,伍爾夫的妹妹來到她的家裏,此前伍爾夫因爲要準備接待客人而陷入慌亂,此時她正受到精神症狀的折磨,幾乎無法駕馭諸如讓傭人做什麼飯菜這樣的小事。妹妹和她的三個孩子的到來讓伍爾夫很開心,但同時她有無數次滑入到情緒的漩渦當中無法自拔的風險相伴。她依然沉浸在如何構思自己的小說《達洛維夫人》的困惑與焦灼中……在與妹妹交談的時候,她想到如何處理她小說中的女主人公的命運,因此她陷入到全然忘我而失神的狀態裏,以至於根本沒有聽見眼前她妹妹跟她說的話。這招來了兩個男孩的嘲笑,她們顯然認爲他們的姨母異於常人,感覺到異常和滑稽。此時,她妹妹對兩個孩子說,你姨母跟我們不同,她生活在兩個世界,而我們只生活在一個世界。這一場景刺痛了我,其中的滋味難以明瞭,這是一種極大的對沖,關於一個以精神生活爲生的人如何能夠同時理智地生活在兩個相互撕扯的平行世界,並面對現實生活對於精神生活那古老的敵意。
也許,你會說,這算什麼問題?!但是,一旦你認識到了這是一個多麼重大甚至古老的母題,你纔會明白那種強烈的分裂感和無力感的來源。“兩個世界”對於一些人來說的的確確是一種精神境況和靈魂處境。當“兩個世界”尚且可以和睦相處時,一切都還不算太糟;但當有一天這“兩個世界”已經無法分出邊界,變爲一灘渾水,繼而分不清哪一個是現實,哪一個是想象世界之時,處於現實世界當中的人無可避免地陷入癲狂與分裂,這將是怎樣的一個艱難時刻呢?
丹麥小說家、詩人託芙·迪特萊弗森的長篇小說《面孔》正是聚焦於這一時刻。託芙·迪特萊弗森是20世紀丹麥國寶級作家,她生於丹麥的哥本哈根,在那裏她度過了灰暗的童年。她少年成名,婚姻之路卻屢遭坎坷,經歷四段婚姻並深受酗酒和藥物成癮的困擾,多次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療。小說《面孔》聚焦於一位備受讚譽的作家莉塞·蒙杜斯在精神病院前後的一段故事。此時,這位女作家陷入寫作危機,兩年沒有新作品的她身心處於極度焦灼的狀態,而與此同時,她的丈夫格特和女傭人吉特之間又出現了婚外情感,三個兒女與作家的關係也出現了問題。在這樣的巨大壓力下,莉塞出現了幻覺,她堅信丈夫和情人正在密謀殺害自己,一時之間各種恐懼猜疑構成了一堵她無法穿越的牆,與周圍人的疏離讓莉塞愈加陷入瘋狂,幻視幻聽隨即出現,真實和虛幻的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不清……最終,莉塞因爲失去理智而胡亂吞服了過量的安眠藥被判定爲有自殺傾向而被送進了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治療期間,莉塞的整個世界都處於一種分裂與混沌的狀態中,無論是醫生、護士、病友,還是現實生活中的丈夫、孩子、母親這些面孔接二連三地以錯亂的方式出現,面孔生髮出原本沒有的形態,說話方式,以及情節,進行着錯誤的安置,並不受控制隨機出現,有時在病房的格柵後面,有時從枕頭裏升出來……這讓莉塞應接不暇,因此產生的錯置也讓她更加受到瘋狂的入侵。她的腦中世界就像是一個紛亂的幻影之城,而她已經無法分辨究竟何爲真實何爲虛構了……
脫序:作爲掙脫社會對應物的面孔
小說的重點落在對於面孔的描繪上,面孔不僅僅代表着現實世界當中對莉塞構成威脅與壓力的人,也代表着在分裂出來的幻想世界中屢次出現的幽靈般的存在。小說開端就指出:“她一直避免上街,因爲成羣的面孔令她害怕。她不敢接受任何新面孔,又害怕在此遇見那些老面孔。”而在精神病醫院治療期間,“格柵”作爲一個莉塞與外部世界之間隔絕的象徵性存在,屢次出現在她的幻覺世界。每當這個時候,總有面孔出現在這裏,這些面孔有時候是吉特,有時候是格特,這些面孔帶着現實生活中他們的身份,有時帶有着對於莉塞所不能完全認知的目的和語言。“高處格柵”裏有時還會有兇殘的酷刑,這是莉塞內心當中最殘酷的經驗的象徵。面孔的錯位不但顯示了莉塞混亂的現實與幻想世界。面孔作爲象徵物代表着一種秩序,面孔的移位代表着秩序的混亂,而面孔迴歸到自身原有位置則代表着秩序的迴歸。這既是現實中每個人的位置和秩序,同時也是莉塞內心理性的秩序。
面孔作爲莉塞瘋狂的表徵,彰顯了她瘋狂的源頭。瘋癲作爲這本小說的核心擁有了全新的意義。在《閣樓上的瘋女人》中,女性主義批評家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芭利用女性主義的視角歸納了19世紀文學中的“瘋女人”形象。“當簡·愛與羅切斯特跨越身份地位的差異,終於要宣誓結合時,一個瘋女人的出現粉碎了簡·愛的一切夢想。”“瘋女人”作爲一個秩序的破壞者,作爲一個人們身體裏蘊藏的企圖打破一切秩序的象徵形象,正是現實當中女性長期被壓抑的那個非理性自我的鏡像。莉塞們正是在生活和地位被全面壓抑,在愛慾當中無法全然滿足的長期折磨當中一步步變得瘋狂的。而在《面孔》當中,我們說,“瘋女人”這一19世紀以來的典型文學形象已經從“閣樓”走了下來,她步履蹣跚,宛如杜尚畫中《下樓梯的裸女》,在日漸分崩離析中成爲一個諸如莉塞一樣的普通的家庭主婦,同時慢慢走向瘋狂的邊緣。如果小說中,莉塞對於丈夫衆多情人表現出的默許被視爲卑微之舉的話,我更願意將莉塞的無動於衷甚至麻木看作一種她對於打破男性崇拜的有意識的冷漠化,即她以此種方式來反抗甚至告別她作爲妻子的身份規約,而長期以來,對於性權利的佔有是夫妻關係的唯一表徵。正如法國女性主義者埃萊娜·西蘇所說:“一旦有一天人們發現,邏各斯中心主義從來都是以不可告人的方式建立在陽具中心主義之上,從來都爲維護男性秩序提供等同於歷史本身的理由,一切又會如何?”由此,我甚至可以說,莉塞的瘋狂是對於這一中心主義的反抗。
面孔作爲莉塞瘋狂的表徵在小說的結尾處得到了疏解——當莉塞成功回到家中時,面孔以這樣的方式迴歸到了秩序中,“孩子們的面孔掛回了原位,就像牆上的畫一樣。”至此,莉塞獲得了病理學上康復的判定,重新迴歸到了日常秩序中。
瘋狂與幻覺:被壓抑的女性
小說雖然集中在莉塞變成瘋人整個過程的塑造,可是其背後的零星滲透卻暗含着莉塞變瘋狂的蛛絲馬跡。其中橫亙着一個痛苦的詞彙:壓抑。莉塞的丈夫格特是一個大男子主義的典型,他認爲莉塞作爲作家的名聲對於他個人是一種侮辱,而他十分熱衷於讓莉塞瞭解自己浪漫的征服史。而他的情人格蕾特自殺也不能讓他感覺到慚愧。處於這種婚姻中的莉塞卻被醫生告知格特那些在婚姻中的越軌行爲是替她做出的。“那是一種泄憤行爲,就像兩歲孩子把麥片粥弄灑一樣。”……格特和莉塞都有複雜的神經症問題,這是醫生給莉塞的診斷。莉塞對醫生的看法不置可否,一方面表現出她對於醫生看法的權威性依賴,另一方面也體現出她似乎對此並沒有波濤洶湧的反抗,而這些似乎都讓一股邪惡的泉水滲透進她的內部——那就是壓抑。壓抑成爲了莉塞病症的源頭。“她總是重複格特或阿斯格的看法,彷彿她從未擁有過獨立的思想。……只有在寫作時,她才能表達自我,而她沒有其他天賦。”格特是莉塞的現任丈夫,而阿斯格是她的前任,很顯然,莉塞在一種被壓抑的狀態當中無法真正表達自己。這種被壓抑正是女性歇斯底里症的成因。在此我們說莉塞的瘋狂的主要成因來自於丈夫所代表的男性權利社會對於女性價值的壓榨。雖然,莉塞已經是知名的兒童文學作家,但是她的丈夫依然認爲這件事無足輕重,而莉塞因爲醫生的診斷也陷入到對於丈夫偷情行爲的合理化解釋當中,無意中將自我當成了丈夫偷情的原因。是因爲“我”的神經症問題纔會導致丈夫偷情的。這似乎是莉塞給丈夫偷情尋找的合理化藉口。接下來是莉塞聽到格特和吉特在廚房公開密謀如何除掉她……但是這些情節因爲後來莉塞幻化自己世界的情形變得越來越難以確認究竟哪些是她的幻覺,哪些是真實。在此,小說家的筆觸刻意將讀者引入到莉塞一樣的境地,即無法分辨真實與虛幻,這是這本小說的玄妙之處。即作者不知不覺間已經將讀者裹挾進自己的病態時空,一時之間真實和虛幻的邊界越來越模糊。這樣,我們感覺到,從小說的一開始,所有的情節都可能是幻覺,我們不禁要問的是,什麼纔是真實?
我們陷入了一種泥塘,我們和莉塞一樣想要像剃掉牛骨上的牛肉和筋膜一樣分清眼前的這一切。但是我們隨即會陷入到和主人公同樣的無力感當中,因爲我們早已經在還沒有準備好,或者認爲自己尚能把握一切的時候悄然滑入幻覺的深淵。正如莉塞的發問:“面孔究竟是在什麼時刻分崩離析的呢?”
有關於他人的痛苦
迪特萊弗森這樣的作家能夠有能力絕不僅僅是讓我們窺見一個曾經在精神分裂漩渦裏掙扎的人的全部生存狀態。不同於完全的虛構情節,迪特萊弗森因爲自身所受到的病痛折磨因此可以勇毅地表現其經驗世界。她的小說的深刻之處在於,她小說中的女性不但處於一個在家庭和婚姻當中身份撕裂的地位,同時也處於一個在廣泛的社會當中撕裂的地位。暫且不說遍佈於小說前後的對於社會政治議題的關注與討論,單從小說最後一章中的一段對話中,我們就可以看出這一更加寬廣的視角(而這一視角絕不是點綴):最後一章中,因爲被宣判爲康復而返回到家庭秩序中的莉塞終於可以“開始寫作,開始照顧孩子們”了,她說:“我經歷了一場危機,我意識到一個人不能無視那些在世上受苦的人。”這讓我想起瑞典電影導演英格瑪·伯格曼的一部電影《假面》。《假面》中以女演員伊麗莎白拒絕說話這一反常行爲爲起點,而伊麗莎白拒絕說話是因爲在電視上看到一個發生在遙遠國度的殘忍的自殺場面而出現的,《面孔》中莉塞的瘋癲也有在“這一對人類普遍遭受的痛苦”的意義上發生的情節。這體現在小說中,莉塞對於他人的痛苦甚至越南戰爭的討論當中。在此,“瘋狂”不應當被單純看作女性被壓抑的結果,而應當在一個更加廣泛的視角上去考察瘋狂這一人類的異化形式。瘋狂是對日常秩序的瓦解和消除,即用一種失序和脫序的狀態去反抗日常當中的不合理秩序。“我經歷了一場危機,我意識到一個人不能無視那些在世上受苦的人。”小說中作家借主人公莉塞之口反覆說出此種議題。而有關於這個維度的觀察和發現有助於我們避免將莉塞的瘋癲變爲一種私人性質的問題或者單純女性主義的問題,找到那根更加隱形的線索……
而佔據全書的另外一個令人印象深刻且發人深省之處是作者對於“寫作”的強調,即當寫作運動展開,莉塞的生活就處於一種可控制的理性範疇,而當寫作這一運動受到阻滯,理性就無法建立它自己的秩序了。這裏,迪特萊弗森藉助莉塞之口,幾乎將寫作作爲一種超越性手段(已經不僅僅是治癒這個被用爲濫俗的意義上)成爲女性獲得自由的一道暗渠。這一點,正好暗合了,埃蓮娜·西蘇對於女性寫作的定義。在《美杜莎的微笑》中,西蘇強調了女性寫作的重要性和作用,她說:“她必須寫她自己,因爲這是開創一種新的反叛的寫作,當她的解放之時到來,這寫作將使她實現她歷史上必不可少的決裂和變革。”
(作者系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