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子,一隻野兔,一段不太可能發生的故事



《野兔知道回家的路》,[英]克洛伊·道爾頓 著,張蕾 譯,花山文藝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出版
想象一下,一隻小野兔住進了你家。當你呼喚它時,它就從野地裏跑出來,到家裏眯上幾小時。
病毒肆虐期間,英國職業女性克洛伊離開城市,移居鄉間。一天,她意外發現了一隻小野兔。如果不出手相救,野兔一定活不下去;但身爲野生動物,野兔無法被家養……
《野兔知道回家的路》記錄了一位女性與一隻野生動物之間不可思議的友誼。這是一場人類心靈與野性深度連接的非凡見證,是一部優美動人的自然書寫,也是一次對自由、信任、失去以及人與自然和動物關係的深刻反思。
>>內文選讀
那天,我站在後門,正準備出門散步,突然聽見一陣狗吠,緊接着是一個男人的叫喊聲。我胡亂把腳塞進靴子裏,穿過鋪滿碎石的院子來到木製的院門旁一探究竟。這附近通常沒有狗。我居住的農舍是由穀倉改建的,四周是一大片耕地。幾條縱橫交錯的小溪和樹籬將耕地一分爲四,其間點綴着幾片樹林。我從小就聽說偷獵者會破門而入,把車開進農民的地裏,再鑽進林子裏去獵鹿和兔子,或是放狗去追野兔。往好了猜,也可能是那些活潑好動的狗在陪主人遛彎時開了小差,去追趕一隻兔子,或單純想在開闊的地裏撒歡兒,一路上不是驅散了羊羣,就是驚擾了築巢的鳥兒。去年就有一隻這樣的狗躍過圍牆,闖進我的院子。它一邊喘着粗氣,一邊漫無目的地撲來撲去,尾巴俏皮地擺個不停,不一會兒就又跳過院牆,一溜煙兒地跑走了。然而,這種情況並不多見,我不禁好奇外面究竟發生了什麼。
我倚在門邊,察看門外的田野,看着它朝遠處的地平線緩緩攀升,直到漫出我的視野。此時的天空是灰藍色的。我的目光順着那幾排矮樹籬,越過一大片光禿禿的茬地和幾塊遲遲不化的積雪,望向不遠處那片樹林的剪影。先前闖入的那隻小狗,此刻已不見蹤影。寒風如刀割般吹打在臉上,呼出的白霧也瞬間被刮跑了。我在口袋裏摸索了半天,終於戴上手套,裹緊大衣,出發去散步。
我走的是一條沒有鋪砌的小路。小路沿玉米地的邊緣延伸,直到併入另一條狹窄的鄉間小道。小道的兩側是高高的樹籬,枝頭掛滿了黑莓與雪果。小路由兩條壓實了的硬土帶構成,結實得足以讓汽車通過,只是路面凹凸不平,坑坑窪窪。我一邊走一邊陷入沉思,不知不覺登上了坡頂,順着斜坡往下走便是那條小道了。就在這時,我突然發現兩條硬土帶中間的草地上有一隻小傢伙正面對着我。我停下腳步,湊近一看,腦海裏頓時浮現出三個字——“小野兔”,儘管從未見過真正的小野兔長什麼樣子。
這只不及我巴掌寬的小傢伙此時正趴在地上,睜着雙眼,一對柔軟的小耳朵緊貼在背上。它的毛是深褐色的,長得又厚又亂,在蜷縮的脊背上形成若干個隱隱約約的小螺旋。長長的淺色針毛和鬍鬚向外支棱着,在微弱的晨光中閃閃發亮,同時在尾部和口鼻周圍各留下一圈不易察覺的光暈。它身下就是光禿禿的地面和枯黃的草地,乍一看根本分不清皮毛與地面的分界。這隻小傢伙與這死氣沉沉的冬日景色完全融爲了一體,若不是身體兩側有明顯的起伏,差點兒就被我當成一塊石頭了。它的兩隻前爪緊緊交疊在一起,爪子邊緣的皮毛呈骨色,這樣的姿勢似乎更令它感到安全與舒適。烏黑的眼睛周圍鑲嵌着一圈濃密但寬窄不一的奶油色細毛。前額有一塊明顯的白色印記,與周圍的毛色形成鮮明的對比,就像被點上了一小滴油漆。它並沒有被突然出現的我嚇跑,而是一動不動地端詳着眼前的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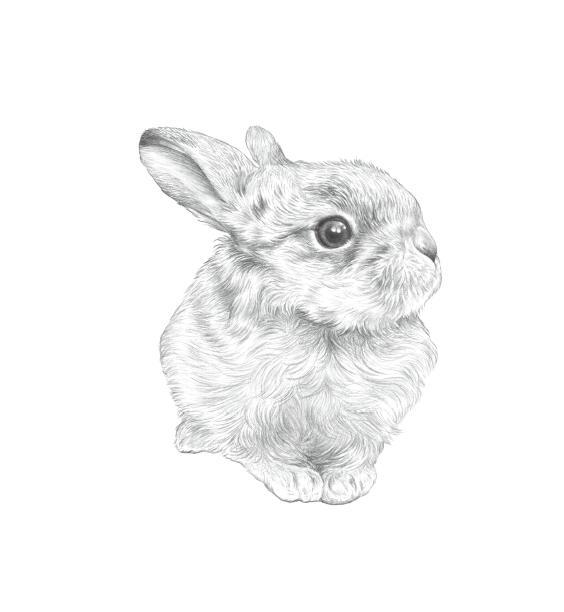
樹下和河堤上豁然敞開的兔子洞口,以及洞內一閃而過的白棉花球般的兔子尾巴,構成了我童年熟悉的景象。野兔卻格外罕見與神祕,只能遠遠地瞥見它們飛奔的身影。在任何地方邂逅一隻小野兔都出人意料,更何況此刻它正乖乖地趴在你面前。至於它爲何會出現在這裏,最合理的解釋莫過於:它被剛纔那隻狗追趕或叼到了這裏,結果在小道上迷失了方向。
關於如何處置這隻小野兔,我考慮了若干種選擇:可以把它留在原地,希望它能順利返回藏身處,在被捕食者發現或被路過的汽車軋到之前就被兔媽媽找到;也可以將它抱起來,藏進高高的草叢裏。然而這麼做有一定的風險——它很可能被追趕了許久,或是被狗從很遠的地方叼過來,早已遠離最初的藏身之地。兔媽媽也許會找不到它,或者乾脆不認它。
小時候,我很喜歡產羔的季節,經常跑到附近的農場去看小羊羔。我見過一隻母羊,一隻雌性綿羊,單憑氣味就能從一羣羔羊中辨認出自己的孩子。除非是自己的孩子,否則任何一隻靠近她或試圖吮吸她羊奶的羔羊都會被堅決地推開。我親眼見過一位農場主爲了讓一隻喪子的母羊爲另一隻失去母親的孤羊餵奶,不得不剝下那隻夭折小羊的皮裹住孤羊——因爲只有在羔羊身上聞到熟悉的氣味,母羊才肯餵養它。可想而知,一旦我把這隻小野兔抱起來,就算只把它挪到幾米外的地方,也會在它身上留下陌生的氣味,這一小小的善舉反而會害了它。
然而,我腳下這個脆弱的小生命似乎不可能在充滿危險的環境中獨自生存。這一帶不僅有狐狸,還時常見到老鷹在盤旋,它們會冷不丁地朝地面俯衝,像石頭一般砸向瞄準的獵物。這隻小野兔正毫無保護地暴露在這些陸地或空中“殺手”面前。然而,一想到人爲干預往往弊大於利,我還是決定順其自然,不去碰它。但願我前腳剛走,它下一秒就鑽進高高的草叢,早日與媽媽團聚。我對着圍欄數了數這是第幾根柱子,以便牢記這個地點,然後繼續上路。
四小時後,我再度回到這裏,幾乎忘了剛纔與小野兔的邂逅。然而,它竟還在原地,在那條開闊的小道上,和我離開時的情景一模一樣。它就這麼毫無遮掩地暴露在天敵面前,頭頂上方就有幾隻鵟在盤旋,丟了魂似的發出陣陣哀號。我猶豫了,畢竟現在離天黑還有好幾個小時。我納悶母兔爲何遲遲不來尋回她的寶寶——按理說,它們母子早該團圓了。我掂量了一下小兔被狗咬傷,或者母兔遭遇不測的可能性。然而無論怎樣,只要它一分鐘不離開那條小道,遭遇各種風險的可能性就會不斷增加,比如車禍、淪爲其他動物的盤中餐。
儘管我仍不確定應該採取什麼行動,卻本能地決定先將小兔帶回家,待到夜幕降臨,再將它送回我發現它的地方。爲了避免直接接觸,我特地採了幾把路旁的枯草。我心情複雜地蹲下身去,既希望它立刻逃走,又不放心它獨自離開。它絲毫不退縮。我用枯草將小兔輕輕包裹,將雙手放在它身體兩側,小心翼翼地托起,捧在胸前。我一路保持這個姿勢,走了幾百米,終於回到我家後門。
一進家門,我便焦急地把小野兔放到檯面上,仔細檢查它是否受傷,又立即用一塊嶄新的黃色抹布將它裹住,以防直接接觸它的皮毛。直到確認它身上沒有任何傷口或出血的跡象,我才鬆了一口氣。只見它顫抖着用那對鉛筆般粗細、長度還不及我小指一半的前爪支撐起自己的身軀,又晃晃悠悠地把重心轉到兩條後腿上,然後眨着眼睛,張大鼻孔,彷彿在仔細打量陌生的環境。比起在剛纔那條小道上,此時的小兔顯得更小了,因爲四周都是爲人類設計的物品。
然而它並不膽怯,絲毫沒有要逃走的意思。它的小嘴呈一條烏黑的短線,鑲嵌在圓圓的小腦袋下方,嘴角向下耷拉着,彷彿已經對生活有了些許不滿。一雙烏黑的眼睛微微泛着一種初生小動物獨有的柔和紫光。鬍鬚又短又硬。當它把後腿彎曲成銳角時,兩隻後爪的長度幾乎佔了身體的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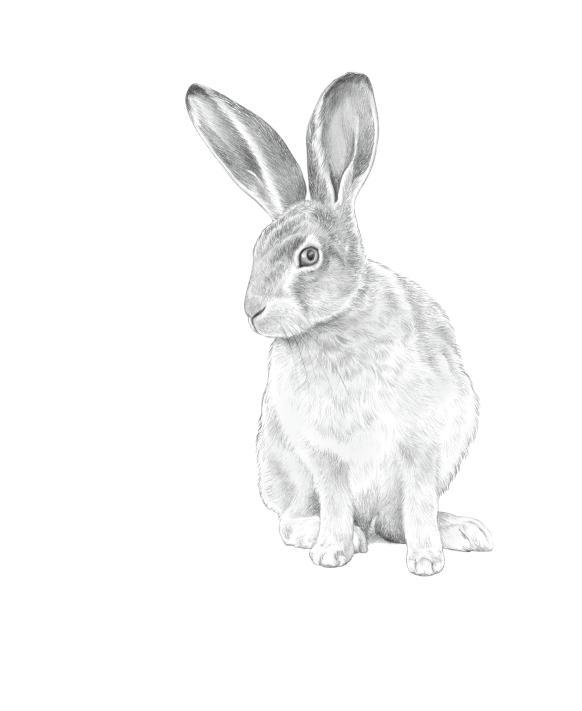
我給一位當地的自然資源保護者打電話,向他解釋了事情的經過並尋求建議。憑藉多年管理獵場的經驗,他很快就打消了我將小兔放歸野地的念頭。他告訴我,即便小兔最終找到了母親,母兔也不可能接納它,因爲無論我採取什麼預防措施,它都會沾染上人類的味道。他說自己在這片土地上工作了幾十年,還從未聽說過有人能成功養大一隻小野兔。“要知道,它很可能會餓死,或是被嚇死,”他態度溫和卻又直言不諱地提醒道,“我知道有人飼養獾和狐狸,但野兔是無法家養的。”
我感到既尷尬又擔憂。事實上,我並沒有打算馴養這隻野兔,只想爲它提供一個臨時的避難所,但目前看來,我做了一個極其錯誤的決定。我擅自把一隻小動物從野外帶了回來,此舉非但沒有必要,還很可能會害死它,因爲我根本沒考慮自己究竟有沒有能力照顧它。我的心頓時沉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