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風的行囊》:一場關於存在、記憶與文明的精神漫遊


將足跡化作墨痕,從市井煙火到遠山曠野,每一處風景都在與內心對話。人生最遠的旅行,並非抵達某個地理的終點,而是歷經跋涉之後,最終走回自己內心深處的那段歸途:從童年記憶中夜間田野的螢火蟲到故土油菜花金黃色的光影,從克萊蒙費朗的火山石教堂到布拉格的哥特尖塔,從康河的柔波到直布羅陀海峽的濤聲……“行囊”裏有“旅途”中的孤獨與溫暖、相遇與別離。它既裝盛過往,也面向未來。
《逆風的行囊》以中國和歐洲行旅爲經,以細膩的筆觸與深邃的哲思爲緯,編織出一幅跨越時空的文化長卷。它不僅是旅行的記錄,更是一場關於存在、記憶與文明的精神漫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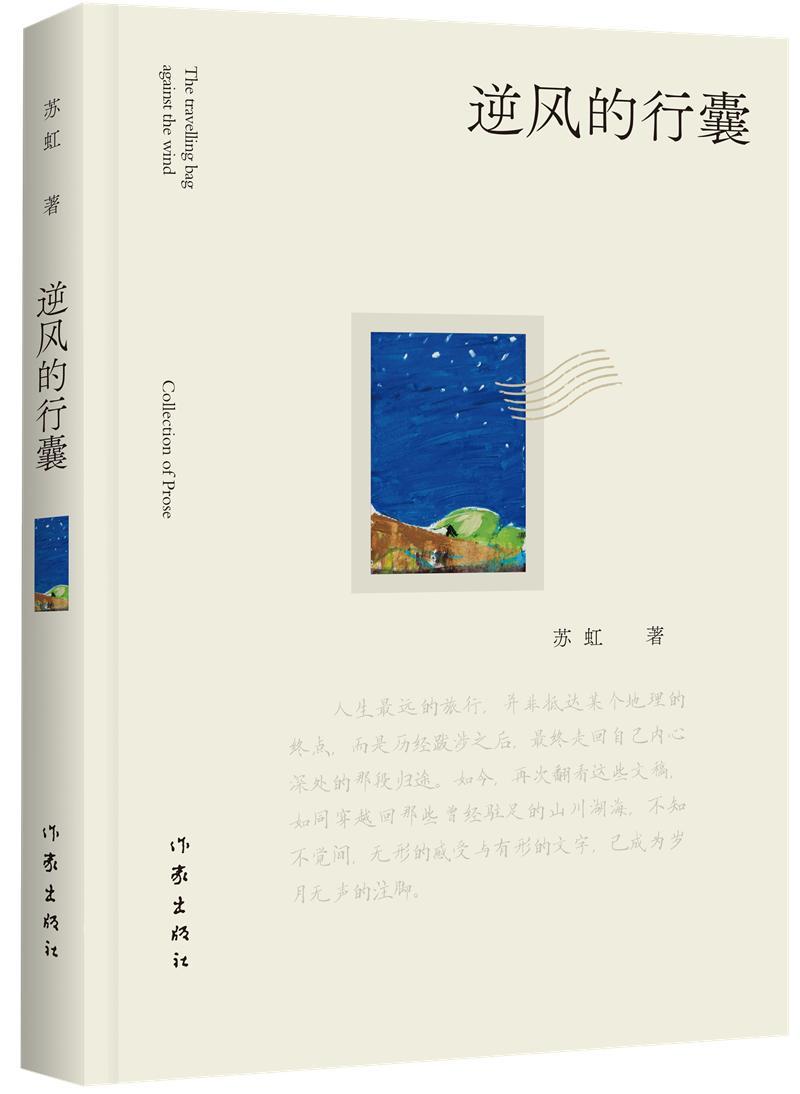
《逆風的行囊》,蘇 虹 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內文選讀
從“人民廣場”到“文學原野”
陳歆耕
我與蘇虹先生堪稱“三友”:戰友、鄉友、文友,而戰友、鄉友,都因“文友”而“友”。此話怎麼講?需要從近10年前的一次“我心中的海安”徵文大賽說起。
那次大賽由江蘇作家協會等單位主辦,由我主持的上海大學文化工作室受委託承擔具體事務的籌劃,面向全國徵稿。此前,我與蘇虹雖在同城工作,但並無交集,更甭說有什麼深度交往。有一篇題爲《“教書匠”父親》的文章,在海量的來稿中脫穎而出,榮獲大獎。由此,我才知道了蘇虹的大名,也才知道了他與我有類似的經歷,同爲海安人,曾有過軍旅生涯,轉業到上海市政府,幹着一份爲“稻粱謀”的職業,內心揣着兒時就有的文學夢。他服役的部隊駐地,與我曾服役的部隊機關,僅隔一條馬路;而他在上海上班的地方,與我上班的地方,就在一條馬路的兩端——君在“威海”東,愚在“威海”西,都在人民廣場附近。
說戰友、鄉友,皆因“文”而“友”,此之謂也。
此後與蘇虹有了頻繁交往,也開始關注他在繁忙公務之餘撰寫的時評、散文,也才瞭解到他此前已經出版過多部作品,如寫二戰的長篇紀實作品《天昏海暗》、寫老子的隨筆《無爲而治》等。尤其是近數年,他從行政崗位上卸任後,有了大把時間閱讀寫作,文學創造力如井噴一般,接連推出兩部長篇小說,令我也令師友們刮目相看。
近日捧讀他的散文集,我是從“後記”開始讀起的。因爲有不少文章此前已經在發表的報紙副刊讀過。從“後記”中我驚詫地發現,蘇虹在短短數年間,已完成了從“職業狀態”向“文學狀態”的轉型和躍升。兩者有區別麼?當然有。而且不同狀態也必然對文學創作構成潛在的不自覺的制約和影響。“職業”要求效率,文學的靈感無法限時限刻地迸發;“職業”要求奉命行事,而文學則必須聽從內心的召喚;“職業”的話語系統通常是格式化的,而文學追求個性化表達;“職業”通常直奔某個功利目標而去,而文學則需要超越功利,將審美視作至上圭臬……在完成這樣的轉型和躍升後,作品的質地會呈現什麼不同的樣貌呢?——於是,作者童年記憶中,夜間田野的螢火蟲舞成了漫天星辰(《螢火蟲》);眼前浮現出那個肩挑溼漉漉稻把的鄉村少年如何艱難跋涉(《鄉間的小路》);耳畔環繞着水車軲轆踩踏時發出的吱吱聲(《流經童年的河》);故土油菜花金黃色的光影里居然閃現范仲淹、魏建功的身姿(《家鄉的油菜花》);睡夢中老祖母津津有味地講述起“挑草”與“石頭”的傳說(《星輝裏的祖母》)……超然、寧靜、神思,那些原本沉睡的精微而美好的記憶,纔會被激活,從腦海深處浮現。而伴隨之的則是精緻、精美的文字呈現。
中國是一個散文大國,歷史上稱之爲“文章”。在古今中國文學的大家族中,詩文的歷史最悠久,創作者的人數也最多,而流傳於世的精品佳作也多得如連綿的羣山。說文化自信,這無疑是一大亮點。一部《古文觀止》實在是滄海一粟,即便編個十卷八卷,也免不了有遺珠之憾。散文寫作的路徑,無非是兩大類別:一是視文章爲“經國之大業,不朽之聖事”,以憂樂天下的宏大敘事爲主要抒寫內容;二是“吟詠性情”,“爲情造文”,內容多以寫身邊瑣事爲基點,而上升至“志思蓄憤”的境界。而這兩者也並不是截然對峙,而是常常交融,難分彼此。據我觀察,當代有影響的散文家和研究者們,既有人提倡散文寫“大事、大情、大理”,如梁衡;也有人認爲,“沒有身邊瑣事,就沒有真正好的散文”,如季羨林。這種看似對立的觀念,都可以從歷史散文中例舉出經典案例。而在我看來,散文是一個極具開放性包容性的文體,可以大,也可以小;可以長,也可以短;可以金戈鐵馬,也可以小橋流水;可以富國強兵,也可以油米柴鹽……它浸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其表現方式,也兼容幷包。翻開唐宋八大家的文集,從分類可見駁雜,也可說豐贍:表狀、書啓、序跋、記傳、論說、碑銘、祭文、雜著等,還有什麼不可涉筆成文呢?
在散文的兩大門類中,蘇虹散文偏重於後者,多記錄身邊“瑣事”——憶親族、記師友、繪花鳥、抒鄉情、錄旅跡……愚以爲,散文品質的高下,並不在於寫“大事”或“瑣事”,最核心的關鍵因素在是否“修辭立其誠”,寫出真性情。它拒絕鼻孔上插大蔥,拒絕塗脂抹粉依門招手,拒絕無感叫牀……而蘇氏散文言之於誠,發乎於情,這正是每每讓我爲之心動的可貴之處。在他的筆下,你既可以感受到綿長的而又熾熱的情愫,又可領悟到透過表象抵達生活、人性本質的深刻;既能欣賞到這位軍中漢子曠達灑脫,也能觸摸到如江南女子穿針引線鉤織衣衫的細膩柔韌……
與之相應的是“高言大句、擲地有聲”來得,“輕言軟語、精摩細畫”也來得。
這位充滿文學情懷的軍中漢子,正處於創作的盛年。小說、話劇、時評、散文——似乎沒有他不敢涉足的文體,如同拿着水槍四處噴灑“戲耍”的少年,會讓人想象不出他還會“噴”出什麼樣的水花來?
讓我們繼續期待。(本文系《逆光的行囊》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