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瘋癲癲”的亞里士多德? | 顧枝鷹



“亞里士多德就會跳出來,瘋瘋癲癲地喋喋不休。”
從古至今的亞里士多德和西塞羅的衆多讀者——還有二人的魂靈——想必都不會相信,古羅馬第一哲人會如此描述亞氏。然而,這個句子卻真真切切地以白紙黑字的形式見於崔延強主編、主譯的“西塞羅哲學文集”中的《論學園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第125頁);而在此之前的梁中和、魏奕昕的譯文作“亞里士多德就會出現,發瘋似地說一連串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第127頁):西塞羅筆下的亞里士多德竟然是個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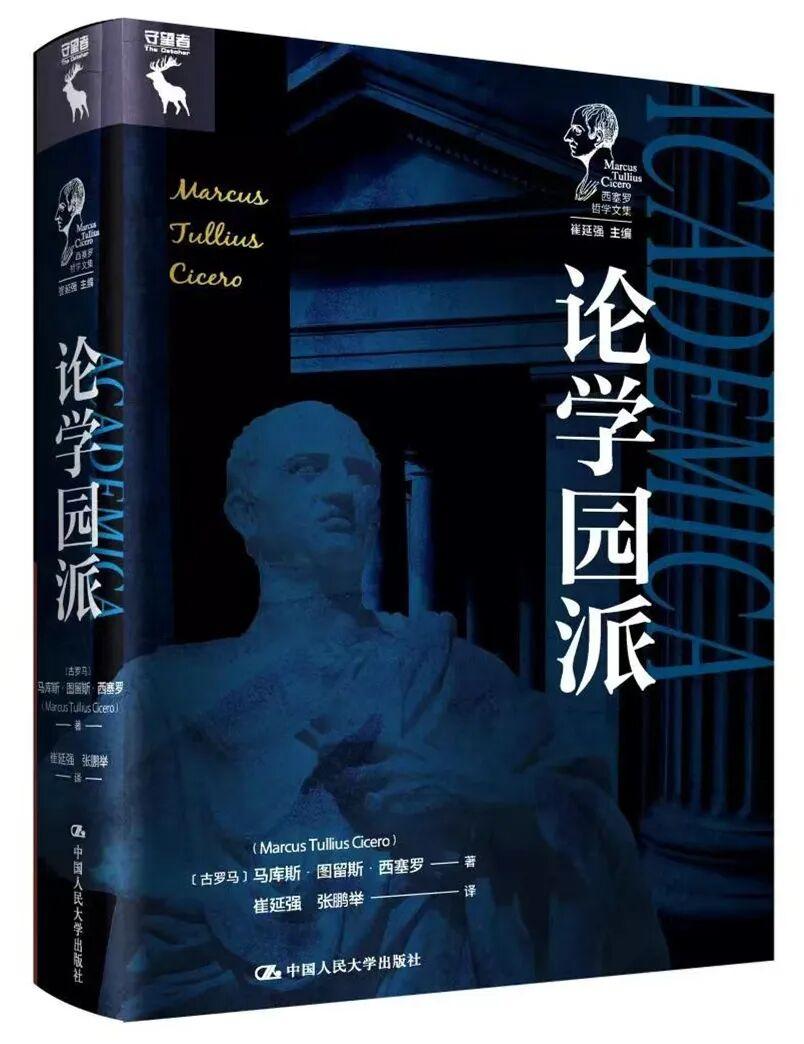
心存疑惑的讀者自然會問:西塞羅的原文是什麼?萊因哈特(T. Reinhardt)的《學園派之書》(準確的書名宜如是)牛津版校勘本(2023;《路庫珥路斯》119)作ueniet flumen orationis aureum fundens Aristoteles qui illum desipere dicat(崔本所據之洛布本[1933]同,僅有正字法差異),較爲準確的譯文可作“亞里士多德會傾瀉着言辭組成的黃金之河前來,以宣稱那個人失了智”。
誤譯本身往往並非值得考究和批判的對象——我們好奇的是,這個錯誤是如何產生的?既然這是崔本“主要從拉丁語譯出”(“翻譯說明”第1頁)的例外,我們就不得不從較常見的三種英譯中尋找線索。萊因哈特逾千頁的譯註本(2023)作Aristotle will appear, pouring forth a golden river of a speech—to say the Stoic is out of his mind;布里頓(C.Brittain)的英譯本(2006)作Aristotle will turn up, pouring out a golden flood of words to the effect that he’s crazy;洛布本英譯作at a time, in will come Aristotle, pouring forth a golden stream of eloquence, to declare that he is doting。與布里頓英譯和洛布本英譯不同的是,萊因哈特的譯文爲讀者明確點出了原文中的代詞illum[那個]具體所指的人(前文提到的一名廊下派,而非亞里士多德本人)。可惜的是,崔本出版於萊氏的譯註本(和校勘本)之前,客觀上無法參考。
在“西塞羅哲學文集”中,西塞羅不止一次地被迫開罪於亞里士多德。崔本《論諸神的本性》(2023)中還說“亞里士多德……觀點混亂”(第15頁)。晚近的奧夫雷-阿薩亞(C.Auvray-Assayas)的法拉對照校譯註本(2019)作multa turbat[造成了許多混亂](1.33;崔本所據之洛布本[1933]同),譯爲introduit beaucoup de confusion[引發了許多混亂]:顯然,沃爾什(P.G.Walsh)譯本(1997)的creates a hotch-potch of many ideas或洛布本英譯has a great many confused notions對中譯者產生了不必要的干擾。
崔本《論目的》(2024;較妥帖的標題中譯或許是“論善惡之極”)稱:“而亞里士多德則認爲它(指財富——引者按)只是一種善,但是一種與正直和德性的事物相比更該被鄙視和瞧不起的事物。”(第189頁)“正直的”何以修飾“事物”?“德性的”何以成爲形容詞?拗口的後半句更促使我們加以審視。雷諾茲(L.D.Reynolds)的牛津版校勘本(1998)作qui bonum essedivitiasfateretur,sed neque magnum bonum et prae rectis honestisque contemnendum ac despiciendum[他承認財富是善的,但並非巨大的善,而且,相較於正當的事物和高尚的事物,它應受輕蔑且遭鄙視](4.73;崔本所據之洛布本[1914]同,僅有可忽略的標點差異)。假設把具有讓步色彩的“承認”(fateretur)改作“認爲”的做法已然不很妥當,那麼,因爲漏譯neque magnum bonum而對讀者造成的障礙就更不能忽視了;何況,伍爾夫(R.Woolf)譯本(2004)和洛布本分別以though/yet not a great good來翻譯,而且bonum[善]這個詞還見於全書的標題: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論諸善和諸惡之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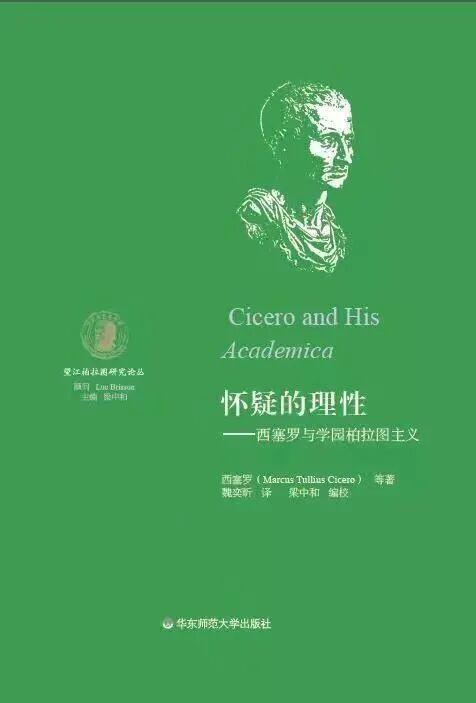
崔本之漏譯的原因是什麼呢?中國臺灣學者徐學庸的譯文(2016)作:“亞里斯多德宣稱財富是善,但與正當及道德之事比較不是重要的善,它應受鄙視與蔑視。”(第259頁)不能排除的一種可能性是,徐本擅自且無甚必要地改動了西塞羅原文的語序和結構,將“不是重要的善”夾在“與……之比較”和“它應受鄙視與蔑視”之間,有意無意地淡化了西塞羅原文中以轉折連詞引出的分句,進而,這一表達就在崔本中遭到了徹底的抹除——實際上,但凡崔本在這裏遵循伍爾夫英譯(且不說忠實於西塞羅的原文)而不過度參考徐本,原本就不會影響讀者的正常理解。
崔本的“總序”中說:“本文集堅持從西塞羅的拉丁語原文翻譯,以保證譯文的原汁原味,但同時也不避諱相關的英譯本,這有助於查漏補缺。”(第6或7頁)如若西塞羅的魂靈閱讀了徐譯和崔譯,不知會有何感想?筆者——如果可稱作西塞羅之譯者的話——捉摸不透。但是,西塞羅和亞里士多德的屬己讀者想必都不會懷疑,大約三十年前曾經參與翻譯苗力田主編的“亞里士多德全集”的學者,無論是對西塞羅還是亞里士多德,自然心存欽慕和敬畏而有充分的潛能擺脫中文舊譯和西文譯本的誤導;也正是因爲如此,我們在“努斯”(nous)中滿懷着對邏各斯的熱忱和誠篤而期待崔本“西塞羅哲學文集”中的後續三種譯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