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朱自清激賞“蒼蠅搓着他的手”說起



有次聽一位作家的講座,他提到小林一茶的俳句:“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腳呢。”他笑着表示難以理解,蒼蠅搓着腳,不是在傳播病菌嗎?怎麼能入詩呢?
沒錯,我要是見到蒼蠅在那裏搓手搓腳,就算不去找個蒼蠅拍子,也不大可能像這位詩人那樣被它萌到。
但是朱自清就能欣賞這句詩——
“這種情境真是幽美。你懂得這一句詩就懂得我所謂靜趣。中國詩人到這種境界的也很多。現在姑且就一時所想到的寫幾句給你看:
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煙。
像這一類描寫靜趣的詩,唐人五言絕句中最多。你只要仔細玩味,你便可以見到這個宇宙又有一種景象,爲你平時所未見到的。”

是不是看得一腦門問號?蒼蠅搓腳還能跟“採菊東籬下”“臨風聽暮蟬”放在一起歸類?但“仔細玩味”,也不是不可以。
“靜趣”的關鍵在於“觀者之心”,而不是“被觀之物”。它不是要求場景必須寂靜無聲,你像“臨風聽暮蟬”本身就有聲音,是要求觀者內心摒棄一切功利、好惡、成見的紛擾,達到一種高度的專注與空明。
在這種狀態下,心靈就像一面擦拭乾淨的鏡子,能映照出事物本身的存在之美,而不去判斷它是“美”是“醜”,是“有益”還是“有害”。
另外,它也是從“人類本位”轉換爲“宇宙天真”,暫時懸置了人類中心的價值觀,看到一個生命體在全神貫注地進行它的日常活動——“搓他的手,搓他的腳”。當這個動作,被純粹靜觀,就呈現出一種微小生命的專注、自得,甚至有一種笨拙的趣味。詩人瞬間捕捉並共鳴了這種生命自在的狀態。
我們的審美里太容易有價值判斷,幾乎時刻都根據各種既定觀念給萬物排序。《枕草子》裏說:“高雅的東西是,淡紫色的衵衣,外面着了白襲的汗衫的人。小鴨子。刨冰放進甘葛,盛在新的金椀裏。水晶的數珠。藤花。梅花上落雪積滿了。非常美麗的小兒在喫着覆盆子,這些都是高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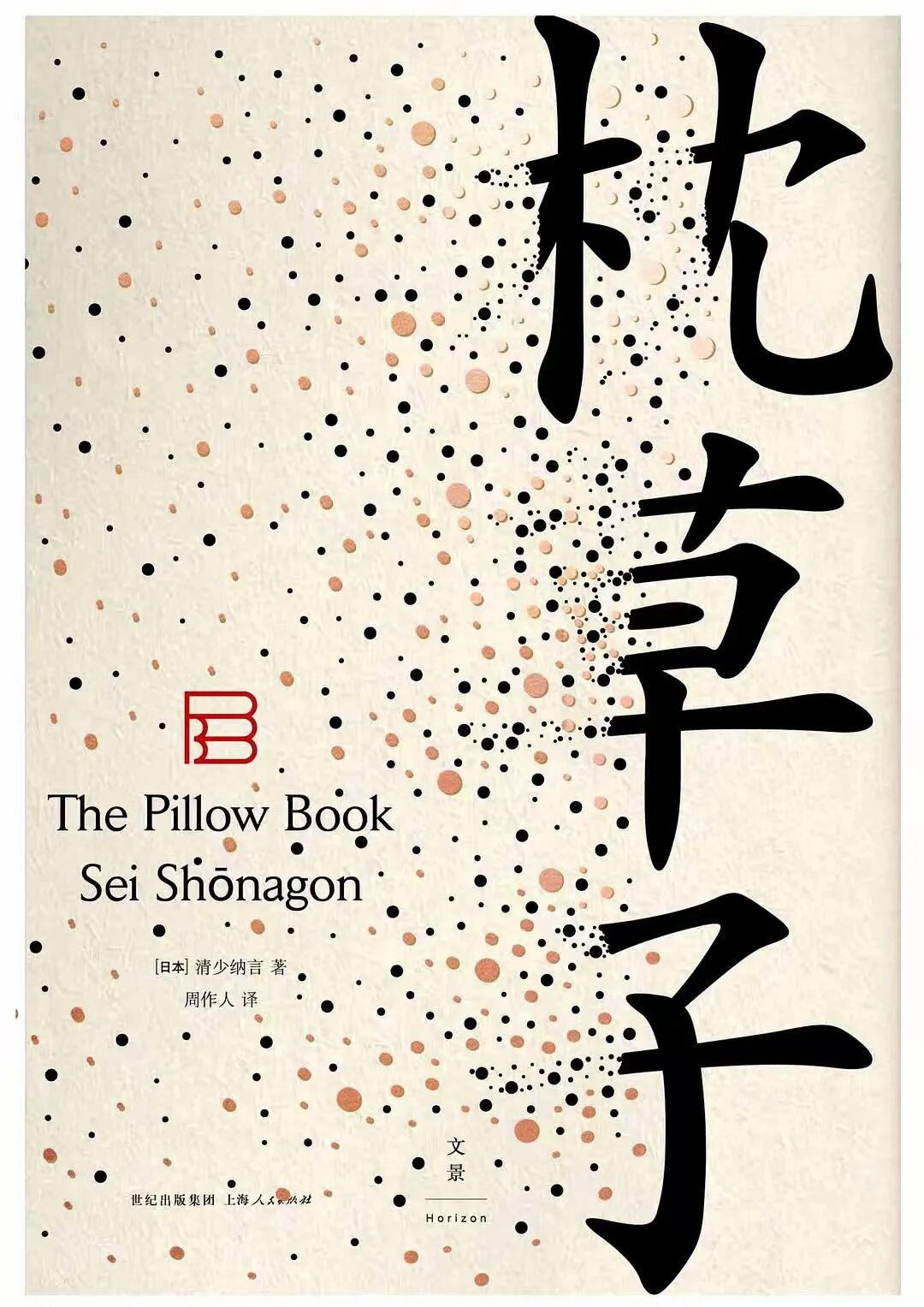
別的倒也罷了,冒出個“小鴨子”是什麼意思?也有譯者解釋爲鴨蛋,但鴨蛋也很難說“高雅”啊?且慢,真的不可以嗎?清灰色的鴨蛋,有着優美的弧度,怎麼就不能言“高雅”?爲什麼我們會覺得一隻梨子可以美得很高雅,鴨蛋就不能?也許因爲在畫作上,在古典詩詞中,梨子會被一再呈現、歌詠,“梨子”在我們的文化記憶裏,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水果,而是一個承載了詩意與美感的符號。
鴨蛋被鎖定在“功能”與“世俗”的語境中:鴨蛋的背景通常是廚房、餐桌、市場。它的首要聯想是“食物”——是鹹鴨蛋、皮蛋,是早餐。它被牢牢地框定在日常的、實用的、甚至有些油膩的煙火氣裏。我們極少有機會脫離這個語境,去純粹地凝視它作爲“物”的形式本身。
“高雅”不再是事物與生俱來的屬性,而是一套由特定文化(通常是文人士大夫或宮廷趣味)所定義和傳授的分類標準與情感反應。我們通過學習知道梅花、白雪、水晶是高雅的,這種認知成爲本能。鴨蛋從未被納入這個“高雅”的經典名錄,於是我們的第一反應是困惑。
所以,問題不在於鴨蛋能否高雅,而在於我們是否願意以及能否關閉腦中那套喧囂的“意義兌換器”,關掉它,創造力就能迸發出來。
張愛玲曾說她每天的必經之路上風景很美,她看了兩三年,仍然不能對之熟視無睹。在《公寓生活記趣》裏,她寫道:“把菠菜洗過了,倒在油鍋裏,每每有一兩片碎葉子粘在蔑簍底上,抖也抖不下來;迎着亮,翠生生的枝葉在竹片編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使人聯想到籬上的扁豆花。其實又何必‘聯想’呢?篾簍子的的美不就夠了麼?”

很有意思的一問,爲何讚美一隻普通篾簍會顯得底氣不足,而一旦將它比作“籬上的扁豆花”,引向自然和田園,審美便獲得許可?張愛玲從根本上質疑了那種只有“遠方”和“非凡”才值得書寫的審美霸權,把目光平等地給予常見的、都市的、瑣碎的、甚至有些“俗氣”的事物。
如果你也有過張愛玲這樣的質疑,就比較容易理解杜尚對現成品的熱衷了。1917年,杜尚給“獨立藝術家展”送去了一個小便池,題名爲《泉》。
這個後來成爲杜尚代表作的作品,在當時看上去極爲冒犯——放現在應該也會。它平平無奇,就是杜尚順手從店裏買來的,還沒有署名,很像一個不懷好意的惡作劇。

有人咆哮着拒絕接受它,但這個展覽的原則是自由,就是給錢就能參加。杜尚的好友阿倫斯伯格爲其辯護:“這東西從它的實用功能解放出來,把一個動人的形式披露出來,因此人家提供的其實是一個美學的貢獻。”據說當時杜尚就在場,並在一邊竊笑不已。
我將這番話理解爲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是這位好友對於世俗的戲仿與嘲諷。所謂“動人的形式”“美學的貢獻”的說法,這些世人終於能接受的詞彙,恰恰杜尚所摒棄的,他曾經說:“我們一旦把自己的思想放進詞或句子中,事情就全都會走樣。”他要通過《泉》這類現成品,倡導的是”沒有美,沒有醜,沒有任何美學性”的現代藝術。
杜尚還創作過一些“現成品”,我敲下“創作”這兩個字時有點猶豫,把一個自行車輪用螺絲固定在一張高凳面上算創作嗎,另外一些作品,瓶架子、掛帽子和衣服鉤子乾脆沒有經過任何加工。
《杜尚傳》的作者王瑞芸這樣解讀:他看得出,所謂藝術活動,不過就是人類的無數種行爲之一,它的出現是由於需要,跟我們烹飪或者製作實用器皿一般無二。但我們人類的心思卻喜歡對事物起分別心,給自己的行爲作區別分類,這樣的結果就產生了等級。
不要總覺得詩在遠方,創作的根基是凝視當下。我是一個副刊編輯,像錢玄同那樣喜歡鼓動別人寫作。有時候聽到別人說話生動有趣,就會建議人家寫下來。但當我看到成稿,發現光彩全無。
那些毛糙而獨特的細節完全被捨棄,作者入鄉隨俗般轉換成各種套路,比如若是寫父母,一定會寫背影。但是《背影》所以動人,是因爲寫出父親攀爬鐵軌的背影是“肥胖”而“笨拙”的,還寫出“我”自以爲長大成熟時,那種對於老父親的輕藐與不耐煩,這些不足爲外人道的情感,恰恰讓讀者有一種隱祕的會心。模仿者沒用勇氣書寫這些,只能寫那種光明的,可以輕易袒露的,以爲應該被讚揚的細節,這種取捨就是買櫝還珠去菁存蕪。
我認識的一位女作家連諫,小說寫得極好,但她更熱衷在朋友圈分享包餃子、蒸饅頭、趕集、健身等瑣屑日常。她說人家很難猜出她是個作家,她看上去就是一個再尋常不過的中年婦女。她的語氣裏有一種自得,我將這種自得,視爲有意識的對於某種等級制度的警惕。
“中年”與“婦女”都是客觀描述,但在世人的評價體系裏,等級不夠高,作家原本是一種職業,卻被投射了很多幻影。“作家”聽起來好像更高級,更風雅,但是,當一個人過於認同“作家”這個身份所附帶的文化想象——那種應當“與衆不同”、應當“深刻風雅”的期待——TA的目光便可能從活生生的人與事上飄離,轉而投向一個由概念和姿態構成的虛空。
這位朋友沉浸於尋常,正是爲了對抗這種抽離。在菜市場跟人討價還價、在廚房裏雙手沾滿面粉時,她作爲“作家”的自我意識被最大限度地稀釋,而作爲“人”的感官卻被充分地打開。她將自己錨定在塵世,保持對生活的開放性,這是一種更深刻的創作準備。
創作不是另造一個別處,恰恰能否欣賞“偉大的日常”,並非指事物本身偉大,而是“如其所是”的凝視,讓存在得以毫無遮蔽地顯現。它不是逃離喧囂,是在內心騰出一片“林中空地”,讓萬物如其本然地降臨、矗立、生輝。這片空地上映照出的,既是事物毫無僞飾的真容,也是我們未被概念纏繞的、因而自由而清醒的心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