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史視野下的個人、社會和時代




AI生成合成
書籍史研究是當下學界關注的一個熱點。西方書籍史名著,尤其是海外中國書籍史論著的譯本已有不少,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也頗具規模。所謂書籍史研究,嚴格地講,是上個世紀中後期興起的新書籍史研究,不同於傳統的文獻學、版本學,也有別於以往的出版史、印刷史,而是轉向更廣闊的社會文化領域,研究書籍創作、生產、流通、接受、流傳等各個環節及其參與者的全面歷史。將這種新的視角和方法應用於以書籍爲中心的歷史研究,無疑會帶來一番別開生面的景象。
作爲一種新的學術範式,書籍史研究具有交叉性和開放性,正如1998年《書籍史》雜誌創刊辭所說:“我們將忽略學科界限。雜誌對學者和非學者開放,對歷史、文學、社會學、經濟史學、藝術、教育、古典文學、傳播學、新聞學、宗教和人類學學者開放,也對出版專業人士、藏書家和圖書館管理員開放。”瀏覽2025年出版的幾部中國書籍史專著,也會發現作者都是在各自學術領域找到與書籍史的交叉之處,藉助書籍史研究的路徑而有所創穫。
書籍命運與個人命運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一書寫的是鄭振鐸——“一個手無寸鐵的書生留守淪陷區上海的文化抗戰史”。在漫長的八年間,許多遷往內地的友人都曾責怪他爲什麼不離開。面對日軍的侵略暴行,鄭振鐸選擇了一條與衆不同的報國途徑:“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作者吳真通過解讀當事人的回憶、不斷公開的私人書信日記以及敵我雙方的檔案,展現了當年身處黑暗之中的鄭振鐸與各方周旋、打鬥,搶救保護文物古籍的戲劇性經歷。這是一場文化保衛戰,也是一部書籍劫難史。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吳 真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5年出版
作者原是研究古代戲曲文獻的專家,自然熟悉將說唱戲曲納入文學史、開創中國俗文學研究的鄭振鐸,但從書籍史和抗戰史的角度“深描”鄭振鐸,進而闡述“一個人與一羣書以及一個時代”,卻是源自她偶然翻到的一本日本隨軍記者所寫《廣東戰後報告》。書中記錄了廣州各大學圖書被劫的情形。於是,追查戰時中國大學包括其母校中山大學被劫圖書,成了作者訪學日本時的“業餘愛好”。一邊從事古代戲曲文獻研究,一邊追查中國被劫圖書的相關資料,這兩條線索最終聚焦在鄭振鐸的身上。
鄭振鐸寫過《劫中得書記》以及《燒書記》《售書記》《失書記》《求書日錄》《“廢紙”劫》等文章,留下衆多的書目、題跋、日記、書信,詳細記錄了侵略戰爭對於書籍的傷害。“一部書就是一個受害者”。鄭振鐸將“劫中書籍”作爲主角,同時也呈現了個人在戰爭中的命運掙扎。燒書以逃死,售書以求生,搶救書籍以抗日,保全書籍以延續文化血脈。書籍的苦難也是人類的苦難,書籍命運與個人命運共沉浮。
鄭振鐸留守上海時期的書籍事業,正是書籍史和抗戰史交叉領域的珍貴素材,最能反映個人、書籍、戰爭三者之間的緊張關係。作者在掌握大量“有意史料”和“無意史料”的基礎上,將鄭振鐸抗戰八年的“生命史”作爲重點,採用一年一章的結構安排,依次八章,每章講述當年發生的一個核心事件,揭示“書籍流轉”背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合作與博弈。
除了鄭振鐸當時的記錄、事後的回憶,作者還參照了同時代人的日記、年譜和中國臺北“國家圖書館”保存的檔案,查閱日本戰時檔案圖書,最終拼接出這場文化保衛戰的完整拼圖。這裏有許多過去不爲人知,甚至當時也不爲當事人所知的隱祕歷史。如鄭振鐸周圍的友人、抗日救亡團體的“聚餐會”“文獻保護同志會”、上海和北平的書商以及日本文化間諜的種種活動。各方勢力之間明爭暗鬥,明槍暗箭,有時甚至分不清是敵是友,正如京劇《三岔口》中所表演的“黑暗中的打鬥”。古籍文物的搶救、守護、祕密運送、遇難被劫、追索舉證的離奇經歷,簡直可以拍攝一部驚心動魄的諜戰連續劇。
借鑑書籍史研究的視角,關注書籍背後的個人生命狀態,作者闡幽發微,不僅詳細描述了鄭振鐸留守上海時期的書籍事業,也生動再現了戰爭年代各色人等的羣像,完成了一部書籍世界裏的文化抗戰史。
焚書之人與好讀之人
書籍的劫難,也即作爲歷史事件的書厄,除戰亂之外就要數焚書了。秦始皇“焚書坑儒”衆所周知,鎮壓儒生、拒絕法家之外諸子百家之書的專制帝王形象,已在後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始皇好讀:帝業與人生的書籍史》一書則意在考察秦始皇在人生的各個階段接觸到的書籍,並在其實施的種種政策中找到某些書籍的影響,從而糾正長期以來形成的偏見和誤解,重新認識這位頗受爭議的帝王。焚書之人也是好讀之人,中外古今皆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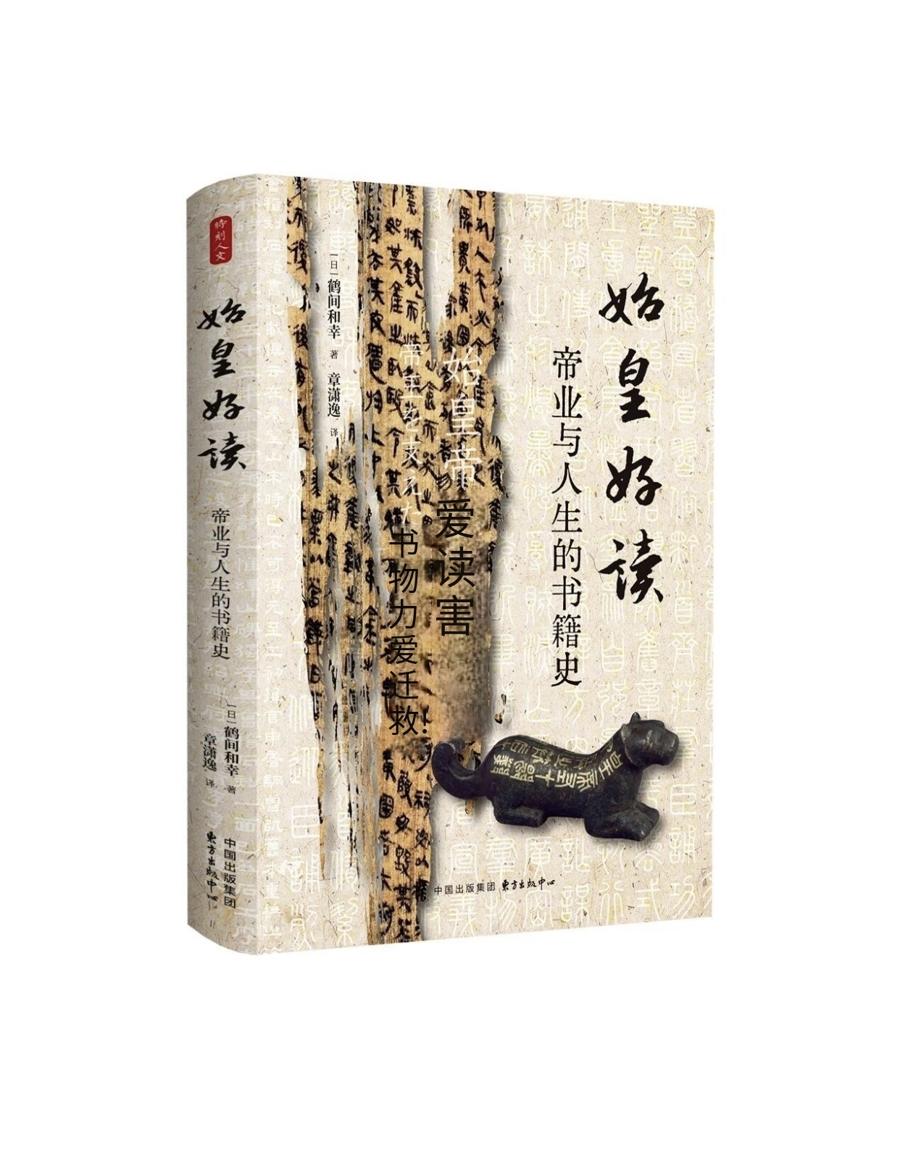
《始皇好讀:帝業與人生的書籍史》,[日]鶴間和幸 著,章瀟逸 譯,東方出版中心2025年出版
本書作者鶴間和幸的研究方向是秦漢帝國史,已出版的專著有《始皇帝:秦始皇和他的時代》《始皇帝的遺產:秦漢帝國》和《始皇的地下宮殿:隱祕的埋葬品之真相》。在後一部書裏,他推測秦始皇陵地宮隨葬品中,除了行政文書,也應該有許多書籍。《始皇好讀》一書,可謂由此猜想衍生出的續作。從書籍史的角度回顧秦始皇的一生,本書爲理解這位千古一帝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藉助《史記》的記載,作者首先區別了司馬遷的“讀書”與秦始皇的“見書”。所謂“見書”,相當於現代漢語的“看書”。而“觀看書本”,不僅是指採用默讀的方式,也包括觀看書籍的外觀。始皇時代的書籍統稱“簡牘”,有的是多枚單行書寫的竹簡或木簡編綴而成的,有的是在較寬的木片(牘)上多行書寫的。每枚簡上不會超過25個字,每枚牘上不會超過五行、每行不會超過22個字。當時的書籍是以“篇”(編綴成束的竹簡)爲單位的,體量較大,字數卻不多。《史記》上說“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孤憤》大約57枚竹簡,《五蠹》大約160枚竹簡。無論是司馬遷還是秦始皇,讀的都不是後人整理的《韓非子》全本,而是這些由一束或多束竹簡構成的“單篇”之書。
秦始皇的一生可能接觸到哪些書籍,又是以何種方式閱讀它們呢?本書正文四章,按照其人生的不同階段,逐次予以考察。在青年秦王時期,他開始閱讀《商君書》《韓非子》,也熱心傾聽李斯之言,從中學習帝王之術。呂不韋死後,秦王親政,他熱衷閱讀《呂氏春秋》,尤其是《十二紀》,鑽研其中的軍事和外交策略。統一天下之後,他再次閱讀呂不韋之書,專注於帝國秩序的建構,並閱讀鄒衍《五德始終》之書,採納其“五行”和“大九州”學說,讓大一統的天下觀爲己所用。步入晚年,他閱讀方士之書、卜筮之書,追求長生不老,同時也接觸老莊之書,意識到難免一死而關心陵墓的建造。秦始皇的閱讀傾向,隨着年齡增長而不斷變化。他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從書籍中獲得知識並應用到自己的政治實踐與人生之中。“好讀之書”的深刻影響,顯而易見。
本書的原名,直譯爲《始皇帝愛讀的書:支持帝王的書籍之變遷》。正標題改爲“始皇好讀”,據說是仿照“君子好逑”。而副標題改爲“帝業與人生的書籍史”,則是因爲在譯者看來:“書籍不僅支持了作爲帝王的始皇成就帝業,也伴隨他作爲個體的人走完了一生。而始皇所接觸、閱讀過的書籍,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他所處時代的知識體系。”在書名上直接出現“書籍史”三字,確實較原文更加突出了本書的主題和研究方法。
書籍之交與書香社會
“書籍之交”也稱“書籍社交”,指的是書籍的社交屬性及相關活動。幾年前,有一部譯著《以書會友:十八世紀的書籍社交》([英]阿比蓋爾·威廉姆斯著,何芊譯,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頗受國內讀書界的重視。那本書中所講述的,其實是在家庭聚會等活動中朗讀書籍成爲流行的社交方式,以及這種“社交性閱讀”催生的書籍文本和形態的變化。《明清士大夫的“書籍之交”》一書所關注的“書籍之交”,則是所謂“非商業性的書籍交流”。相對於將書籍視爲商品,中國傳統士大夫更願意將其視爲文化身份的象徵,用於閱讀、收藏,也用於贈送、借閱、傳抄、交換。當年文人之間,這種社交性的書籍往還頗爲常見。作者正是由此作爲切入點,展開了明清書籍史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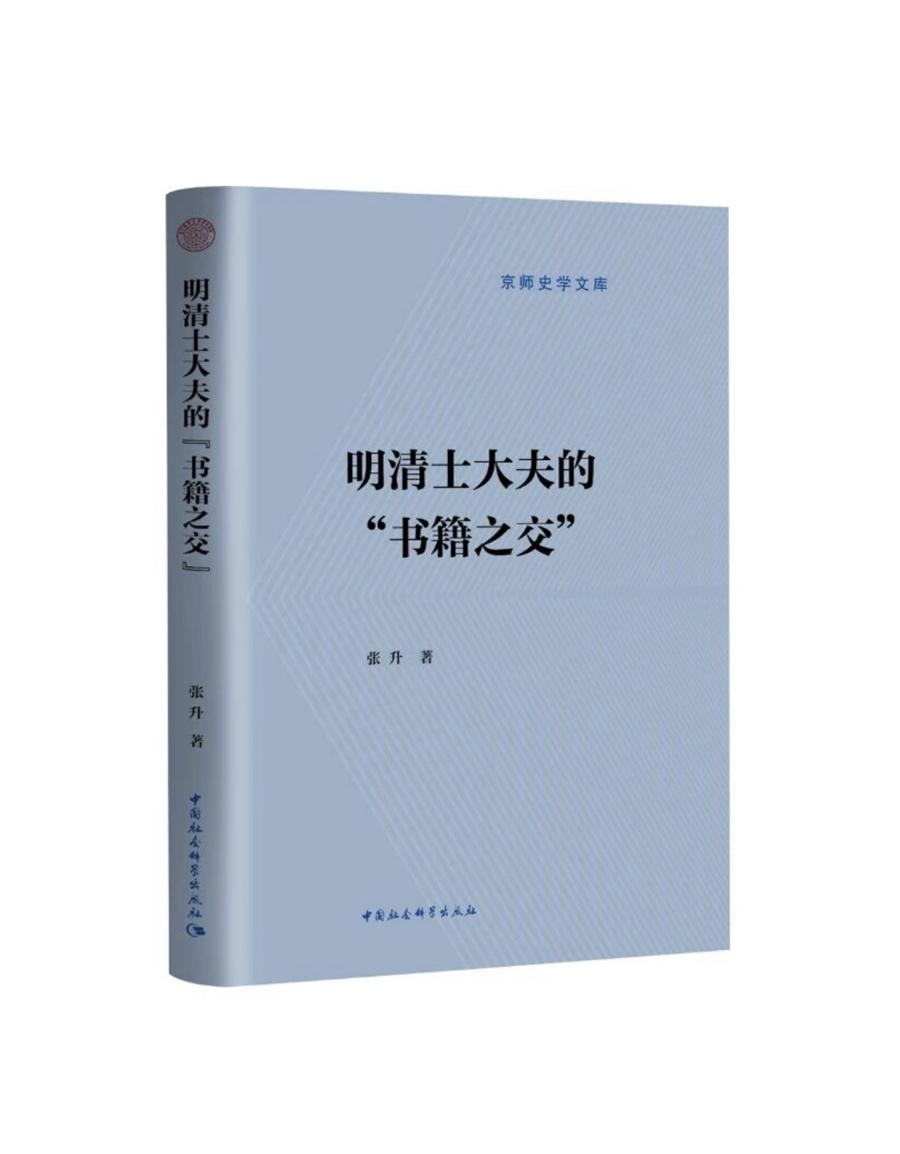
《明清士大夫的“書籍之交”》,張 升 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5年出版
從書籍史的角度入手,本書作者更新了既往的文獻學觀念,重新梳理和解讀了出版史、藏書史的原始資料,更加全面、準確地考量了明清書籍傳播的方式,進而探討了書籍交流對士大夫日常生活、治學傾向以及地方文化等方面的影響。
“書籍之交”的一個重要前提是私家刻書的普及。私家刻書的普及帶來了私家藏板之普遍。傳統文獻學往往只關注藏書,而私家藏板、隨時印刷,爲搜書之道提供了多種可能性:以成書相贈、出工本費索贈、自備紙張來印刷、賃板印刷,甚至出售板片等等。在作者看來,賃板印刷無疑展示了“書籍之交”的一個面向。
明清時期“書籍之交”最主要的方式是“以書爲禮”。書籍不是作爲商品,而是作爲禮物在士大夫間相互贈送,以獲取名聲、增進交遊。就大多數私家著述和刻書而言,書籍就是爲了贈送而出版的。當然,士大夫在贈書時會考慮到收益和成本的平衡,也即好名與好利的平衡。求名的贈書者有時十分慷慨,有時也會婉拒不合情理的索贈。如何才能做到既合理又合情呢?《流通古書約》以及《古歡社約》等提供了一種互通有無的示範,即在對等的條件下可以互抄各自所缺的書籍。這些“流通之約”,明確顯示了藏書家之間“書籍之交”的通用途徑。
除了贈送和互抄,明清士大夫的“書籍之交”還有多種方式,包括購買、受贈、借閱、知見(臨時展示)等。本書作者藉助大量書目、題跋、日記、書信、筆記、雜著,說明當年書籍流通的渠道還是比較通暢的。儘管我們經常讀到有關中國古代私家藏書多“藏而不借”的記載,“書籍之交”在一定範圍內仍是相當活躍與發達的。在熟悉的圈子內,書籍不但可以借閱,還可以贈送。再說,“書籍之交”並不只是針對藏書家而言,而是存在於社會的各個角落。“藏而不借”與“書籍之交”這一對矛盾,始終相伴着貫穿整個中國書籍流通史。
“書籍之交”自然是書籍背後人與人的交流。書籍的流通,拓展了士大夫的社交圈。社交圈有多大,獲取書籍的範圍就有多大。一個人的學問,往往取決於他能看到多少書;而他能看到多少書,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的“書籍之交”。此外,在士大夫的書籍社交圈中,由於閱讀經歷和範圍相近,大家很容易產生共同的學術興趣、治學傾向,以至於聚衆修書、結社聯詠,甚至形成“學術共同體”,導致某個學派的誕生。明清江南文化學術的區域化特點,乃至江南書香社會的構建,或許都可以從“書籍之交”的角度獲得新的闡釋。由此觀之,一部書籍史,確實就是一部“書籍的社會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