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箇中國人在悉尼開出租車,會遇到怎樣的人怎樣的事?



《我在悉尼開出租》的作者張立雄在悉尼開出租車近20年,自2019年起開始書寫出租車裏的故事。本書收錄他近五年來的文章,大多取材於出租車內真實發生的故事。通過出租車這一流動而短暫的空間,作者試圖捕捉人際相遇的微妙狀態:那些萍水相逢的人們,會交談什麼、碰撞出怎樣的火花?在沒有利害關係的車廂裏,人與人之間是更坦誠友善,還是疏離防備?本書借個人敘事反映時代的變遷,字裏行間也流露出對祖國、對家鄉的熱愛與眷戀。
在車廂這個移動而私密的空間裏,張立雄既是司機,也是聽衆,更是記錄者。他用敏銳的洞察力,去感受方向盤前流動的萬般人生。文字細膩而不矯飾,幽默裏帶着哲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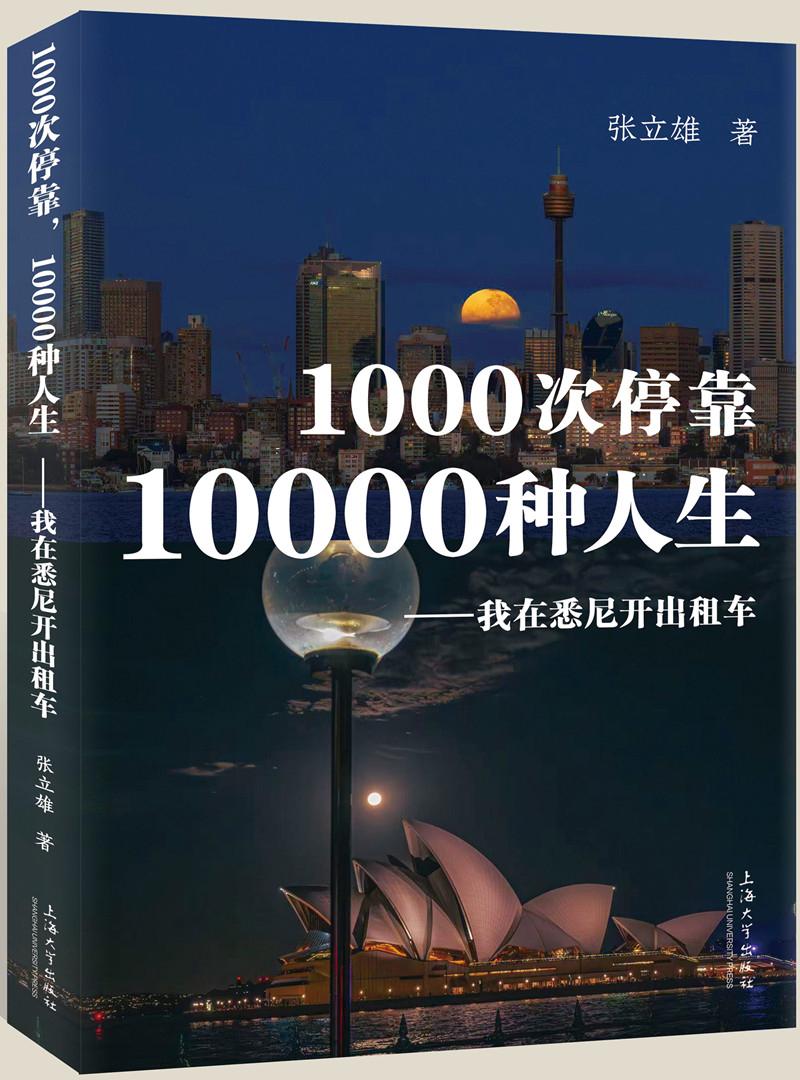
《我在悉尼開出租》,張立雄 著,上海大學出版社出版
>>內文選讀:
隱私和孤獨:出租車上的澳大利亞社會學
一天晚上,一個白人白領女孩上了車就掩面而泣。我問她去哪裏?她反問我:“可以去哪裏?未來在哪裏?”原來今晚她和男朋友“崩”了,她受不了,感到無望。我狠狠地說:“什麼未來?我們每一個人的未來都是被設定好的,那就是墳墓。”她被我說得一愣一愣的,悽悽楚楚地說:“那生活不是就沒了意義了嗎?”我說:“當然有意義,因爲我們擁有現在。我們不能改變過去,其實也不能躲過最後的‘未來’,但是我們能把握現在。或者說,擁有現在的人才擁有未來。”
她有點懂了,也明顯好受些了。最後給了我5元錢小費下了車。
有許多one off(一次性)男女乘客向我訴說隱私,傾吐衷腸。一開始,我覺得自己或許有一種特殊的魅力,能誘人敞開心扉,曬出底褲或底牌,直到遇上了他。
他大概20歲出頭,有點髒裏髒氣、破破爛爛的,散發着一股深重的憂鬱。一個潦倒的人卻神情嚴肅、專注,讓人覺得好奇。當前面兩輛出租車不理他的招手呼嘯而過時,我則停下了。
他上車後,我發覺他談吐很正常,比他的外表要整潔得多。他說他是從鄉下來的,要去內西區的Marrickville(馬利克維爾)找朋友。我問:在哪條路上?他說他不知道地址,開到那裏,他會認出來的。
Marrickville地方大了,又該從“辣”條路開過去?我又問:他朋友知道他來嗎?打個電話問一下。他說:朋友不知道他要來,也沒有他們的電話。我有點焦躁,覺得不對勁,哪有風塵僕僕、大老遠趕過來找一個“三無”朋友-—無地址、無電話、無預約?看來這趟差會有麻煩,但也只有開過去再說了。
一路上他仍然憂鬱、嚴肅。我就一點一點地誘他開口。我問:“你有什麼要緊事嗎?”他說:“沒有。”我又問:“你和這個朋友關係很近嗎?”他說:“不近,只見過一次,他是鄰居的親戚。”我忍不住說:“那你找他幹什麼,還要冒着找不到他的風險。”
他沒回答,也沒因我的“衝”而不快,仍然一如既往地憂鬱。
“怪人。”我心想。
他卻嘆了口氣,幽幽地說:“我只想找一個人說話。”
我問:“你在家裏沒有朋友、親戚?”
他說:“有。”
“那你到這裏找他幹什麼?”
“因爲我要找一個不相干的人說說胡話、廢話。”他清晰而堅定地說。
噢?這個理由倒從來沒有聽說過,他是有個性,還是非理喻?我立即來了興趣,我對與衆不同的人總懷有一種敬意,因爲自己從不敢逆鱗惹衆怒的。
“我的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就和你談職業、金錢、愛情,這個太沉重了。人需要說些胡話、廢話,各說各話,笑個不明所以,快樂不知何來,然後,一個晚上就過去了,稀裏糊塗,過去的一天就忘記了。然後,明天才能是一個新鮮的人。Starting from 0,then can be 10,20,30; Starting from 1.1,1.2,then could be 1.11,1.22.(從零開始,有可能馬上十進位,而從滴滴答答的殘屑開始,弄不好只有個進位。)”
這些倒不是胡話、廢話,雖然不嚴謹,但也不無道理,還有點煽動力。
“所以,我寧願找不到,也要找一個不相干的人說話。”他有點不憂鬱了,或許因爲我也是個不相干的人。我猜測他有點“獨頭獨腦”,或許還懷有周邊的人不可理解的野心,所以在那裏不受待見。
最後我在一個小路口放下了他,我估計他是找不到他的朋友的,但他會在遠離家鄉的悉尼找到一個可以說胡話、廢話的人。
我從中醒悟:這裏的人更願意和不相干的人說真心話。這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是違反常理的,但卻自有它的道理:與陌生人說隱私,沒有泄露的風險;隱私有很大部分是防自己人、防熟悉的人的。另一方面,從陌生人那裏獲得的回答,卻是最直白的沒有顧忌的第三者的“元”見解。
又一天晚上,在經過市區的百老匯大街時,我看到一個瘦高個青年站在公交站等車,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爲他不僅瘦,而且弱,亭亭欲顫的樣子,好像隨時會隨風起舞。當我就要擦身而去時,他突然伸出了手,我就一個急剎車停住了。他朝前走了兩步,打開了後車門。我發覺他的腿有點問題。
他說了一個地名後就不說話了,我感到一種特別的沉悶,好像他帶進了一股壓抑。過一會,他卻嘆了口氣,又嘆了口氣。我就順勢問:“工作很累?”他“唉——”了一聲後才說:“我一出生就生了一種骨癌,今年22歲了,一根股骨全蝕壞了,明天進醫院手術。”我聽了很震驚,怪不得他有點“蹺”。我不知道如何勸解,就說了些禮貌的廢話,我的確一籌莫展、無能爲力。
他下車後,望着他被路燈拖得又長又細的身影,我有點想不通,不是他與生俱來的不幸,而是他現在的孤獨。對於我來說,手術之夕仍然孤身夜歸,是第二種不幸。他沒朋友嗎?沒親人嗎?只能對一個萍水相逢的出租車司機一吐哀怨和擔憂?
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五六年前,我在市中心的一幢住宅樓包清潔活。一天早上去上班,大樓女保安喬艾神祕兮兮地對我說:“有人凌晨4點跳樓自殺,黛比知道,你快去見她。”
黛比是大樓的物業經理,比我小5歲,和我關係很好。她住在10樓,我就上去看她了。推開門,看見黛比眼淚汪汪地坐在窗邊,她示意我坐下,就絮絮叨叨說了起來:“是我害死了他。他是18樓的一個租客,他住1810室,我住1010室,正好在我的樓上。他是個空軍軍官,以前只是見面點頭,昨天傍晚,正好和他乘同一部電梯,就聊了幾句,大家都很高興。他還問我住在哪一單元。”黛比擦了下滲出的眼淚,“昨夜2點,我在電話裏和男朋友吵架,突然有人敲門,我問誰?回答的是他,他說想和我聊聊。我當時正煩,情緒失控,就說:滾開,我自己都顧不過來了。他說了聲對不起,就走了。到了4點,我還在電話上和男友吵,突然生出一種強烈的不祥的預感,這時就見一個身影從上面飄落,劃過我的窗戶。我對着電話驚叫起來……”她顫抖起來,不得不停住說話。
“都是我不好,如果當時我開門讓他進來,他就不會跳樓。”我無言以對。至今不知道那個空軍軍官爲何要跳樓,情感?職途?政治?
黛比帶點惡意地說:“真不明白,好好的,爲什麼要跳樓?照我說,要跳樓的,該是那些九個人、十個人住兩房一廳、像個雞窩的人。”一些亞裔青年,持學生或旅遊簽證,在市中心的餐館沒日沒夜地打工,爲方便、爲省錢就湊人合租一套公寓,聽說最多的有十二個人住兩房一廳的。我們剛來時,也羣租,雖說沒那麼多人,但我對他們的處境是理解和同情的。黛比的話,表現出了一種本能的歧視。我冷冷地說:“他們既沒有想死的時間,也沒有跨窗跳樓的空間。”
跳樓的話題在我離開黛比的房間時,便永遠地結束了,再也沒人提起那個空軍軍官,也至今不知道他從哪裏來?爲什麼要到“那裏”去?如在中國,那肯定是一個熱門話題,要“燒”一陣子。這當中有多少成分是搬弄口舌,有多少是關切、是遺憾,難以分清,但他絕不會是走得這樣的無聲無息。
看來,澳大利亞人要比中國人孤獨,當然也有更多的個人自由,這兩者是成正比的。首先,澳大利亞人對個人隱私有着極端的護衛傾向,許多事情他們寧願找陌生人,如律師、心理醫生或出租車司機(哈哈)傾訴,也不願和親友分享。其實,許多個人的煩惱只要與親友侃一通就會減輕,甚至了無。當然,套用哲學家魯道夫·卡爾納普的話說:“問題不是解決了,而是消失了。”其次,個人的獨立性、自主性的強調和堅守,使得家庭成員間的關係並不處於一種“生命共同體”的“互聯網”中。我們中國人,無論愛、怨,家人之間有着毫無道理但不可推卸的責任,至少在我們這一代人是這樣的。有時,無論情況多麼糟糕、多麼無望,你總有一條退路,總會有一碗飯喫——家人、摯友是你無須再退的退路。
當然中國人的親近,也有親近的麻煩。我的一個朋友,早幾年接到家裏電話,說父親病危,他就匆匆地趕回去了。那時他來了沒多久,經濟狀況不太好,孩子又都小,回國一次是件大事,他只能請兩週的假。回去兩週,父親轉危爲安。臨別時,父親不好意思地說:“讓你白跑了一趟。”言外之意是:怪我不爭氣,沒能走掉。
過了一年,父親又病危了,他又回去兩週,兩週過後,父親仍然處於病危之中。臨別時,父親又說:“唉,又讓你白跑一趟,但估計不會要你跑第三次了。”他走後沒幾天,父親真的走了。朋友很難過,爲沒能送終盡孝而遺憾,但他說出來的話卻讓人忍俊不禁:“××,我在他伐西(死),我走了他就西了,就差一口氣。”
他父親是世家子弟,是同濟大學的名教授,病危通知一出,國內外親戚、故舊、學生都來探訪,等着告別,很隆重,這對病者的壓力也很大。照我朋友的話說:“太多人來也不好,人家大老遠來告別,你不走都覺得不好意思,讓人家白跑了一趟。我老了決不這樣。”
中、西方文化各有優劣,哪一種更好,其實是看各人的性格和境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