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培訓費用、學習話術套路:起底親密關係中的PUA羣體



“騙色社羣”承諾讓男人學會“拿捏”女人的知識。男性支付高昂的費用,在培訓師的指導下,習得與女性建立親密關係的套路。如今我們熟知的PUA一詞,便起源於此,最初指 “搭訕藝術家”(pick-up artist),後衍生爲情感操縱與精神控制的統稱。
《親密陷阱》是首部關於“騙色社羣”的長篇研究,一部起底PUA羣體的社會調查。作者進行了一年多的行業調查,採訪了30多位業內受訪者,親身記錄形形色色的培訓課堂,在近60萬字的資料基礎上完成本書。PUA產業建構出一整套話語邏輯,強化刻板印象和性別對立,將女性物化爲性資源,把親密關係視作可以被管理的項目。作者描述了英國的騙色產業以及背後的文化脈絡,呼籲人們抵制騙色,探索更爲健康、真誠的親密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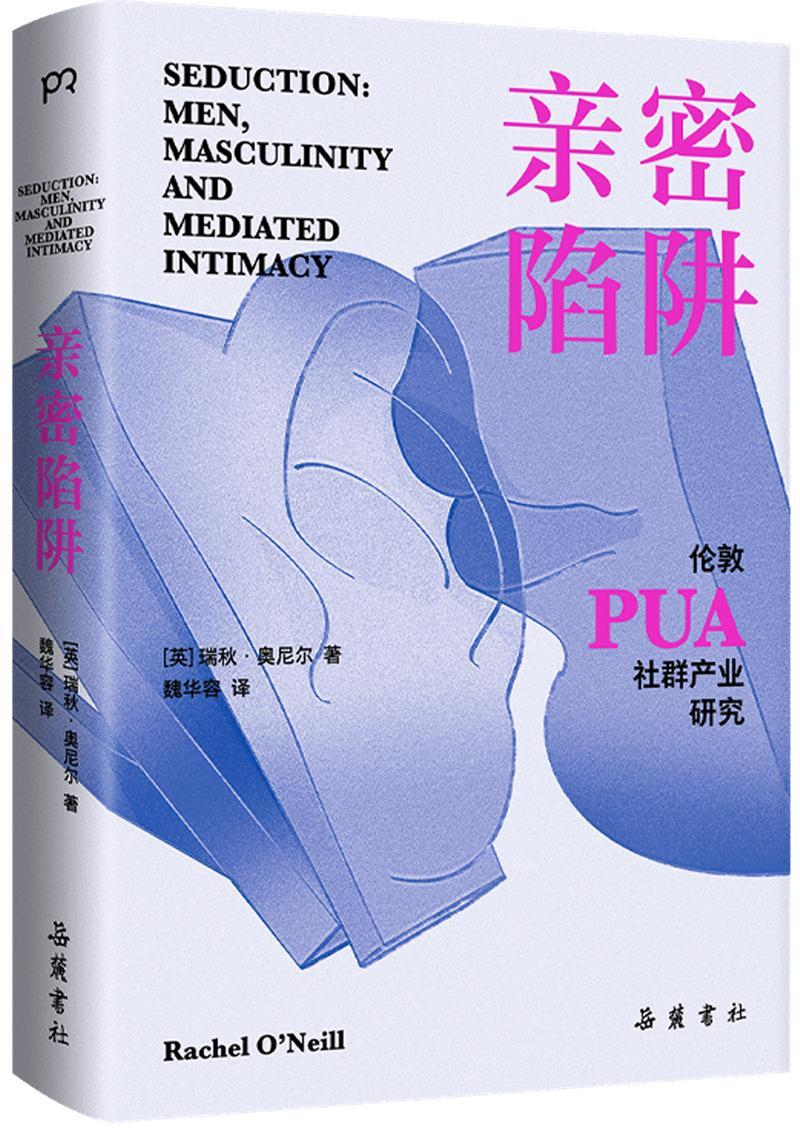
《親密陷阱》,[英]瑞秋·奧尼爾 著,魏華容 譯,嶽麓書社出版
>>內文選讀:
以跨國的視角看待PUA
周可笛:我第一次在中文語境中接觸到PUA這個表達是在好幾年前。當時PUA已經是一個很流行的網絡用語,通常表示男性爲了誘騙和控制女性採用的情感操控手段。那時並不知道PUA其實是“搭訕藝術師”(pick‑up artist)的縮寫,更不知道它背後牽連着更廣闊的跨國產業,這個產業專門訓練男性誘騙女性。我在攻讀碩士期間讀到這本書,才瞭解到這一切。我鮮少讀過如此有力而令人歎服的作品——不僅是選題本身吸引人,更是在於您如何從經驗、理論和方法的維度拆解這個問題。所以我想先提問:您是否瞭解PUA這個詞在中國廣泛流傳的情況,以及它特別的使用語境?如果是,那麼這和您目前對騙色產業(seduction industry)的瞭解有什麼契合的地方呢?
瑞秋:我也是最近才瞭解到PUA在中文世界裏經歷了怎樣的傳播才成爲大衆用語。整個過程非常值得關注,尤其是PUA的中文用法和它本身在騙色產業中的含義(搭訕藝術師的簡稱)顯著相關,卻又有很獨特的區別。我很早就知道騙色產業在中國乃至世界各地的存在,但PUA在中國的語言學發展現象對我來說是新的發現。某種意義上,我恰好能借此闡述它如何能印證本書的一個核心觀點。
異性戀男性可以且應當將親密生活視爲需要學習、投資、“優化”的項目。爲此,他們當然可以採取各種策略來打壓女性,這樣才能“平衡競爭環境”。這種思考模式雖然可能最初出現在騙色產業中,但若進一步反思,我們不難發現它其實也能“完美契合”更廣義的社會圖景。簡單來說,這些邏輯十分符合一些現存的理解,關於做人應該如何(積極進取、有企業精神、有野心),關於男性在關係中如何對待女性(自信、強勢、主導、“像個男子漢”)。
在我看來,PUA一詞在中國的流行更有力地佐證了這一觀點。很多人使用PUA這個詞的時候不是特指騙色產業,反而讓這個詞擁有了常識的地位。它成爲便捷的標籤,用來描述男性試圖操縱、打壓,最終控制女性的那些可辨識的交際模式。就像很多女性觀察到的那樣,這種行爲在騙色產業出現之前早已存在,更不是所謂搭訕藝術師的專利。所以從根本上講,PUA並不是一個新現象,在中國不是,在世界各地也不是。新出現的是騙色產業在多大程度上有技術地系統化這些行爲,創造了一個兜售這些技巧的新市場,很明顯地吸引越來越多的男性前來買單。
周可笛:全書通篇我很欣賞的是,它不是把騙色文化視爲英國獨有的現象,而是以跨國的視角展開討論。雖然它的研究對象是英國的騙色產業,整個研究卻帶有一種全球性的感知。它試圖解讀話語、資本與慾望的跨國流動如何塑造親密關係、男性氣質與自我認同。
作爲中國的讀者,我感到這種視角和中國當下息息相關。很多時候,圍繞親密關係的討論是我們思考權力、關懷、能動性與自由這些更大命題的入口。
瑞秋:在英語世界,“異性戀悲觀主義”的話語也反映出許多年輕女性對與男性的親密關係感到失望。這還不包括全球範圍內反對性騷擾與性暴力的各種運動,比如全球性的“米兔”運動,以及拉美的“一個都不能少”。在回答《親密陷阱》這本書能爲這些討論(尤其是中國的語境)帶來什麼之前,我想先說說我不希望它帶來什麼。
我尤其不希望任何地方的女性將這本書當作“預警手冊”來讀,用它來更好地保護自己、提高警惕。年輕女性已經有太多需要擔心和應對的事情了,我不希望我的書再給她們增加負擔!
如果要說我對這本書的中譯本有什麼特別的期望,那我希望它能觸及更廣泛的討論,關於如何在世間生活、如何與他人建立關係,尤其是在異性戀親密關係的語境中,但也不限於此。
本書的結論章叫“抵制騙色”。它的確是要批判騙色產業,但它更呼籲大家反思這個產業對異性戀關係的理解,以及它推崇的異性戀理性。騙色產業的親密關係模式要求大家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更充滿了敵意和對立。在我看來,這是一種非常貧瘠的親密想象。不論從心理或生理層面來看,我都不覺得男女之間必然或生來就要以這種方式相處。
我相信,在我的研究中,有一些男性其實是意識到了這一點的。有一位非常坦誠的騙色培訓師就曾在採訪中承認,他教的技巧雖然在表面上“奏效”,但並不能真正解決那些驅使男性來求教的深層困境。他也承認這個產業對男性可能是有害的(但同時他對騙色產業可能帶給女性的傷害就不那麼敏感)。
還有一些男性則陶醉在“PUA明星”的角色光環中,享受着自己高超騙色技巧帶來的聲名,又因騙色帶來的糟糕後果而名譽掃地。我完成研究後不久,就有這樣一位男士從圈子裏消失了。後來我得知他自殺了。他曾經表現得那麼自信,到底是怎樣的絕望才迫使他結束生命?兩者之間的落差實在難以想象。
我並不想從個案中做過多推論,但基於我做的所有研究,我可以有把握地說:騙色文化並不真正服務於男性。操控女性、有策略地謀算她們、控制她們、堅持主導地位——這些行爲並不能緩解大部分男性在親密關係乃至生活中的普遍不滿。相反,嘗試用這些手段實現男性氣質的自我,可能還會加深他們被異化的感覺。
因此,我認爲年輕女性和男性需要共同參與更廣泛的討論:我們希望與彼此建立怎樣的關係?我們希望如何交往、如何溝通?親密關係應該是什麼樣子的?應該帶來怎樣的感受?這不是一個容易展開的對話,也不是女性或女性主義者可以單獨完成的。男性也需要參與進來,並且要以真誠的態度參與,願意承擔暴露脆弱的風險,才能探索新的可能性。
這就是我對這本書中譯本的最大期望。再次感謝你們給予我這個機會,我感到非常榮幸。(摘自《親密陷阱》中文版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