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擁聽簫樓:從隋煬帝到《花間集》



《坐擁聽簫樓——隋唐五代文苑雜譚》是揚州大學顧農教授的一部文學史隨筆集,從隋煬帝談到《花間集》。而以唐詩爲重點,涉及王績、上官婉兒、駱賓王、王昌齡、孟浩然、王維、王之渙、高適、杜甫、劉禹錫、白居易、柳宗元、李賀、李商隱以及若干知名度不甚高的詩人,談他們生平作品中有疑點有趣味的問題,多有新見。文字通俗流暢。書中涉及一些唐人文章的名篇和傳奇小說,也保持其要言不煩、講究興味的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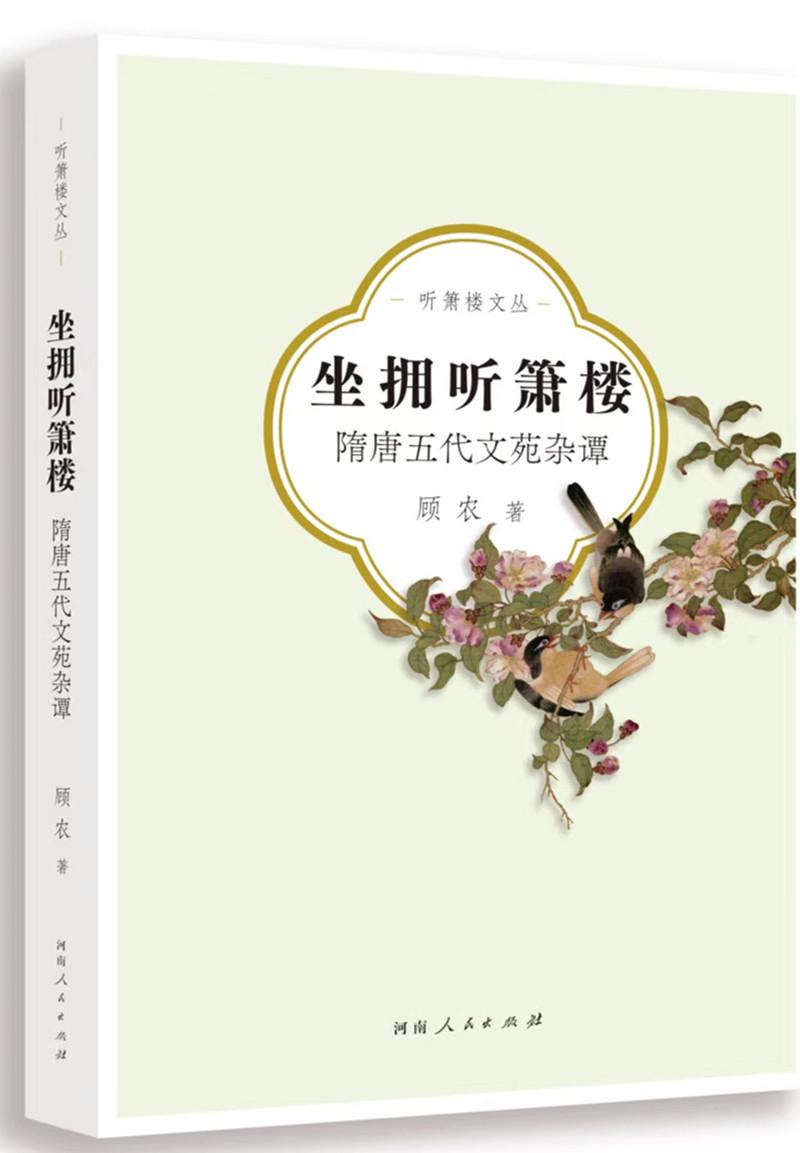
《坐擁聽簫樓——隋唐五代文苑雜譚》,顧 農 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內文選讀:
後記
中國古代詩歌一向有四大題材:民生政治、風景靜物、歷史人物、友情愛情,唐詩中這四個方面都有大量的作品,名篇很多,杜甫道德高尚,憂國憂民,關於民生政治的傑作尤多,於是成了“詩聖”,只寫後三項,水平再高,也成不了“聖”。其他幾種題材杜甫也寫,水平同樣很高。主流搞好了,又能兼及其餘,這是“大家”氣象;如果主旋律不強,其他方面再好,最多也只能稱爲“名家”;而如果僅以大寫愛情著稱,則可能被正人君子瞧不起,甚至要挨批評。此前在蕭梁時代,以太子蕭綱爲首的一批宮體詩人雖然在藝術上多有探索和貢獻,但後來的評價始終不佳,根子就在這裏。
隋煬帝楊廣中年以後也多寫宮體詩,同樣挨批,可是晚唐五代的詞人幾乎全是大寫愛情以至於豔情的,倒並不怎麼挨批,他們的社會地位沒有蕭綱、楊廣那麼高,他們的那些小詞原是爲應歌而作,安排歌女們在酒會上唱唱的。家妓或商業性歌妓們的演出無非是提供娛樂,本無所謂大雅,如果讓她們忽然大唱憂國憂民的高調,倒反而顯得有點怪怪的。
所以後來就把曲子詞稱爲“詩餘”,安排這種樣式老老實實地呆在文學和音樂的邊緣;古人又一再強調“詩莊詞媚”,不讓小詞有什麼力度。美國漢學家艾朗諾說:“無論關注何種主題,詞往往偏重於情感方面,或是偏重於感知身邊事物。詞中常用的語言,通常被描述爲‘女性化’或曰‘陰柔’,相應地,其呈現模式也以幽微、精緻的美學風格爲中心。這樣一來,在思考詞、詩之間的異同時,‘詩莊詞媚’成了習慣性的說法。”“甚至當詞已經成爲一種重要的文人形式之後,它還一直以自己的商人階級出身、因精英對它的‘市井氣’的認知而苦苦掙扎。當時常用來指稱這一形式的幾種貶義詞,如‘小詞’、‘詩餘’,也證明了這一揮之不去的偏見。”(《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冊,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486-487頁)。歷來的偏見一方面使得詞的地位不甚高,同時也讓它無須承擔多少社會責任。人們常常看到,同一位作者寫詞時的心理狀態同寫詩時往往不同,典型的例子如北宋文壇領袖歐陽修,他的詩文都是比較嚴肅的,而小詞則相當風流瀟灑,不大像個大雅君子的樣子,以致曾經被誤以爲不是他的作品。曾慥《樂府雅詞·序》說,歐公不可能寫那種低俗的小曲,“乃小人或作豔曲,謬爲公詞”;至今也還有學者採信諸如此類的看法。這其實乃是隔膜之論,浦江清先生說得好:“在歐陽修當時,晏殊以剛峻見稱,但詞極柔弱纖媚;司馬光和寇準那麼耿介,他們的詞也婉約而澹遠。歐陽修寫作這樣的詞自是不足爲怪的。”(《浦江清中國文學史講義(宋元部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頁)。北宋文壇上這種帶有規律性的差別大可注意。當時《花間集》的影響如日中天,詞壇上的氣氛非常輕鬆。
最近收拾隋唐五代這一段文學的舊時雜稿,始於楊廣,終於《花間》,文章和小說方面的札記隨筆也有一點,而其大宗則是談論詩詞的,其間不禁浮想聯翩,有些小感慨就順手記在這裏。後記的寫法可以自由一點。《西遊記》裏的孫悟空搖身一變,化爲一座廟宇,把尾巴變作一根旗杆安插於廟後,形成一道別致的風景——正規的廟從來未見有這樣來安排的。
我初步將手頭這些舊稿選編爲一疊的時候,恰逢河南人民出版社的老朋友前來約稿,於是將這些存稿進一步收拾一番,且驚且喜地捧出來請他們並通過他們轉請讀者批評指教。唐朝的詩人大約有一小半是河南人,杜甫、韓愈、李賀、李商隱等一流人物更全都是河南老鄉,拙著榮幸地能在河南面世,這是何等的緣分和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