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意人》:“生意經”的三重辨證邏輯



商業傳奇曾是電視劇一個重要的類型分支,往往以“老字號”的興衰史爲敘事主線,通過一家一業的成敗折射民族工業、文化在近代歷史夾縫中的掙扎與自強。張挺的《大生意人》則跳出了傳統的敘事思路,不侷限於某一樁生意、某一個家族,而是以“生意”爲觸角,勾勒流犯古平原從以商謀生、以商立身,最終以商濟世的傳奇軌跡。該劇的成功不在於構建誇張的商業神話,而在於通過對大與小、傳奇與日常、術與道之間關係的探索,讓“生意”成爲一門經世致用的學問,更賦予了這段傳奇敘事深厚的家國情懷。
以小入大:小生意的時代大尺度
《大生意人》之“大”,皆是積“小”而成的因果。故事以一個犯人的出逃爲開篇,以一個大生意人的退隱爲結局。一個不斷被歷史拋擲的小人物,在與時代、秩序、價值的碰撞中自然生長出了“大”的尺度。
小人物撬動大版圖。古平原的經商之路並非源自個人的內心驅動,而是在一次次交易中不斷地被推向更大的生意場。以寧古塔爲分水嶺,古平原的身份與生意性質經歷了兩次關鍵轉變。第一次交易是協助蘇紫軒偷運戰馬,並藉此換取了人身自由。此時的生意還只是私人領域的利益交換,從流犯到行商,目的只爲自保與脫身;第二次則是在與徐管帶的周旋中,從邊境購入朝廷急需的槍支,隨後因被清廷賞識而逐漸有了“半官半商”的中間身份。在這一過程中,古平原不斷地於商海浮沉中悟道。隨着生意所託之物的放大,做生意不再只是個人選擇,而是開始牽動制度與秩序。當他接觸了堅船利炮,遇見了匯豐洋行、東印度公司等跨國資本對手,他開始意識到傳統商業邏輯同新的時代格局之間的錯位,其行商目標也隨之發生轉變,由單純的“爲己謀路”轉向以商應世、以商報國。最終,在以鹽場歸屬爲核心的矛盾中,他與洋商展開了一場涵蓋茶葉、絲綢等多宗商品的系統性商戰。可以說,“大生意”不以錢帛多寡爲標準,而指向能否濟民、安國,這一被時代不斷放大的經商路徑,最終塑造了古平原作爲“大生意人”的氣象與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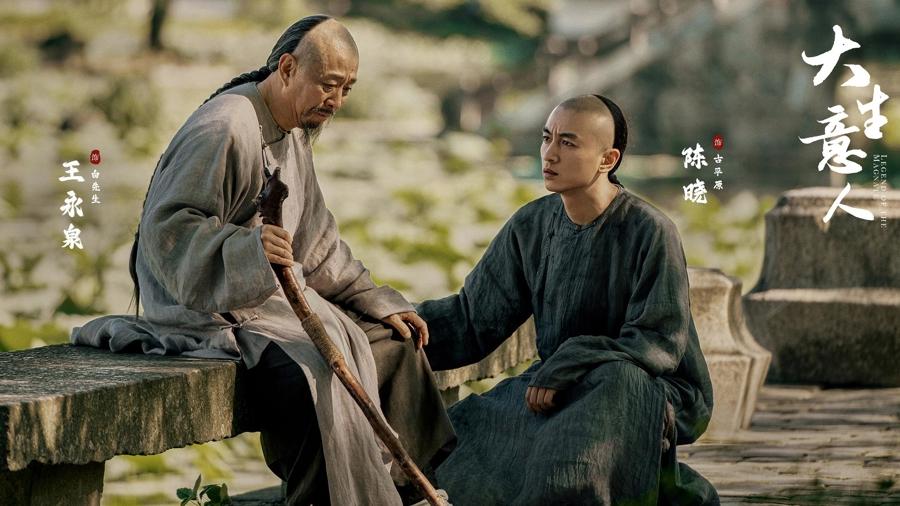
小往來織就大網絡。商人既行商送貨,就勢必要跟地面上的所有人打交道。從早期單線的交易關係,到後期多方博弈的生意網絡,利益的不同不斷驅動着人物關係的變化,《大生意人》以層層遞進的方式,爲觀衆展開了一幅涵蓋商人、官員與百姓的羣像圖。在此種關係網絡中,生意人是商業流通的主體,把握着商品資源的運轉;各級官員則是影響商業環境的外部變量,其決策能夠直接左右生意的走向;而平民百姓的生活生計,則是檢驗“大生意”成敗的現實標尺。具體而言,晉商八大家、馬幫商隊共同呈現了以“信義”爲本的傳統商道精神;遊走於灰色地帶的李家父子、蘇紫軒,則讓生意場的風險、權謀與人性的張力不斷浮現;因貪婪而覆滅的王天貴、借饑荒牟利的米商楊千萬、橫行霸道的英國商人等形象則反向說明了“生意無道”的代價。更爲重要的是,劇集通過刻畫兩江總督瑞麟、六王爺、慈禧以及義軍首領李成等人物,讓做生意這一商業行爲成了透視晚清腐朽體制的切口。

小故事跨越大空間。複雜的人物網絡,還對應着不斷外擴的空間版圖。《大生意人》呈現了一條橫跨大半個中國的商業軌跡。以極北之地寧古塔爲起點,隨後深入山西的縱橫商道、科爾沁草原腹地,又轉入白牆綠瓦的徽州古城,最終抵達風雲激盪的江寧重鎮。每一處地理座標對應着特定的生意形態,不同的商幫模式,也反映了不同的民生民情。從窮途末路的流犯苦役,到因戰亂而失去生計的茶農,再到饑荒中橫屍街頭的貧民,都在生意之外反覆暗示着時代的危機,並召喚着“大生意人”的出場。
以傳奇融日常:類型敘事中的文化底色
《大生意人》在敘事上採用了經典的傳奇劇架構,並以遊戲化的方式將古平原的成長路徑拆分成了五個敘事單元,爲觀衆提供了一種“闖關升級”的快感。同時,在大開大合的戲劇衝突之外,該劇亦對各地的民間風物、生活細節有所考究,共同構建起了一個鮮活可信的商業江湖。
在傳奇性的打造上,《大生意人》通過高風險、高密度、高反轉的敘事策略,牢牢抓住了觀衆的注意力。高風險的情節設置意味着將商業競爭提升到了生死存亡的維度,從逃離寧古塔開始,古平原不斷地面臨生死考驗,先是藏於水桶躲過徐管帶追捕,隨後差點命喪草原,在山西數次下獄,回鄉後又身陷義軍營地。各種外部勢力的疊加形成了巨大的生存壓力,不斷地迫使他在緊急情況下做出判斷。與此同時,劇情又常以“最後一分鐘營救”的方式巧設援手,常玉兒放箭、蘇紫軒上場都數次使危局得以扭轉。險中求生的情節設置不僅調動了觀衆的情緒,也在高壓處境中進一步凸顯了角色的人格魅力。高密度的敘事節奏讓劇情環環相扣,使困局到破局在上下數集間便見分曉。以江寧篇爲例,古平原大婚後,立馬接到了前往江寧振興經濟的差事。圍繞古、李兩方爭奪鹽場地契這一核心衝突,修海塘、穩糧價、散俘虜、鬥漕幫等事件次第鋪陳、彼此牽動,形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鏈式反應。與快節奏相伴的還有“高反轉”。《大生意人》通過人物身份與立場的不斷重組,爲觀衆製造持續的情緒震盪。從古平原與李萬堂的父子相認,到白依梅的意外迴歸,再到小虎以革命人士的身份在劇尾亮相,劇情不斷推翻觀衆的心理預設,直至最後一刻,完整的故事圖景方纔顯現。

傳奇故事既要有一路過關斬將的爽感,也要有日常生活細節作爲託底,故事纔不至於“懸浮”。在徽州篇中,《大生意人》不惜筆墨地描摹了粉牆黛瓦的呈坎古民居、靜謐的石橋流水與錯落有致的茶山,這些寧靜古樸的視覺元素除了能予觀衆以獨特的地域審美感受,更與劇中刀光劍影、生死攸關的商戰情節形成了強烈對照,也暗示着兩軍交戰對普通百姓生計的無情侵擾。同時,“茶”在徽州不僅代表着生意,還意味着一種生活方式。茶農口中悠揚的採茶調,廖師傅祖傳的炒茶技藝以及融雪煮茶的風雅意趣,這些細節精準傳達了當地的文化特色。至於徽商,除了以劇情展現他們“誠信爲本、義利兼顧”的經營哲學,商人們集中議事時鄉音雜陳的方言細節更爲原本嚴肅的生意場平添了幾分生活氣。
以道馭術:“富天下”與“救天下”的價值座標
《大生意人》並未止步於對“生意之術”的精彩演繹,而是在多方勢力的博弈中指向商業何爲的終極命題。“術”是方法,“道”是方向,通過不斷讓“術”接受“道”的檢驗,商業傳奇找到了清晰的價值座標。
在古平原初涉商海的階段,他習得的是“誠信”與“流通”在生意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漢隆大管家的失信與王天貴的出爾反爾,從反面揭示了缺乏契約精神的交易註定難以長久;另一方面,以信用爲擔保的匯票在關鍵時刻助他化解困局,讓他切身體會到“以誠爲本”並非是空談的道德口號。隨後,在李萬堂策劃擠兌老八家票號時,古平原反其道而行之,讓銀車在平遙城持續進出,以一場看似冒險的“空城計”穩住了人心、盤活了市場。所以,生意的根本不在算計,而在信用;銀兩的價值不在於囤積,而在於流通。此時的古平原,確立的是作爲一個“生意人”的職業底線。

將“天下第一茶”的祕方向商會同行公開,反映的是他“共生”的商業境界。古平原回鄉後,先後看到的是茶山被毀、商會壓價、茶農困窘的現實。即便他掌握茶葉品質的優勢,也在自立門戶、尋找銷路的過程中屢屢受阻。在這樣的處境中,古平原並未以個人利益得失爲判斷,而是理性地審視商業本身,意識到了生意不是勝敗輸贏,而是合作共榮的本質。一家獨大的“蘭雪茶”或許能成就一個富商,但只有全行業共享技藝,才能從根源上驅逐劣幣,保住徽州萬千茶農的飯碗。這不僅展現了古平原“計利當計天下利”的儒商胸懷,也昭示着他成爲大生意人的真正轉折。
隨着故事的推進,古平原所面對的已不再是單一行業或局部市場的問題,而是一個內外交困的時代。朝堂之上黨爭不休,國門之外列強環伺,洋人正覬覦着中國內耗的間隙,意圖攫取經濟命脈以坐收漁利。“讀書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財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古平原既具商人的膽識與謀略,也懷有讀書人的責任與抱負,他此時開始意識到,也許商人的能力、資源與網絡,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可以回應時代危機的力量。因此,在與李欽、洋商理查德的博弈中,古平原敢於以個人身家甚至性命爲籌碼,換取兩淮鹽務這一經濟命脈的主導權;在生命的後段,他又以更隱祕的方式支持民族革命事業,踐行了從“富天下”到“救天下”的宏願。可見,“道”並非先驗的存在,而是通過一樁樁具體的生意逐步顯影。古平原正是在經世濟民的實踐中,完成了對“術”的超越和“道”的求索,終成“大生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