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四書》中的城市記憶



2025年12月21日,《海上四書》新書分享會在上海徐家彙書院舉行。兩位主講人——文化學者、作家、資深媒體出版人潘大明,與同濟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國偉,進行了一場關於海派文脈、城市記憶與人文精神的深度對話。

王:爲什麼叫《海上四書》?
潘:用這四個字純粹巧合,我生在長在滬上大自鳴鐘一帶,石庫門擁擠的居住環境,提供了豐富的人與人之間的故事和衆多鮮活的細節。在20歲以前,生活半徑未曾超過出生地五公里,出生的婦產科醫院在家斜對面,就讀的學校臨近,即使後來換了好幾種工作,也離家不遠。這樣,導致耳聞目睹的人與事大都集中在這一方寸之間,家門口的那一條大街上的行人,職業、住家,都能知曉個一二。這片土地,爲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蝸居”成了一種機緣巧合,使筆下的人和事自然而然有了聚焦。
而40多年的碼字,形成的作品文章,編書時只能根據不同文體進行分類,歸類成四種文體。故順理成章地用了“海上四書”作爲文集名稱。
王:海上是上海?還是一個虛擬的空間?
潘:上海的土地由江河泥沙長期淤積而成的,海岸線一直向東推移,古人認爲上海是從海上生長出來的;漢語中的“上”有“江河的邊側”之意,“海上”指的是海邊。近代以來,“海上”逐漸成爲上海的別稱。在清代文人中廣泛使用,頻率高於“滬”或“申”。晚清,上海的文人云集,常用“海上”稱上海,有的人就號稱自己爲海上某某人,有的書名定爲《海上花列傳》《海上梨園志》《海上名醫》等。所以,書稱中的海上並非虛擬空間。
王:請談談你書中歷史的上海,比如七君子,這些人物大部分輝煌時期都發生在上海,他們跟上海構成怎樣的關係?
潘:七君子事件是上世紀30年代中期,全面抗戰前夕爆發在上海震驚中外的事件,也是國民時期一個典型的司法案例。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史良、沙千里七個著名的知識分子在同一個深夜被捕,被捕的原因是他們鼓動國內一切力量聯合起來抵禦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國民黨在日本人要挾下逮捕了他們。共產黨人、宋慶齡、國民黨左翼人士、愛因斯坦、杜威、羅素等發出聲援並營救,直接引發西安事變。
他們是一批怎樣的人呢?老上海里的“新上海人”。他們有的留學歸來定居上海;有的大學畢業留在上海;有的移居上海。圖謀發展後,成爲業界翹楚,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經濟上,他們又是那個時代的中產階級,擁有信徵所、律師行、書店、學校、圖書館等,處在當時中產階級的中上端水平,豐裕的物質保障了他們從事社會活動的物質基礎。上海成就了他們,他們成就了上海。在歷史關鍵時刻,他們挺身而出,使得上海成了宣傳、推動全民抗戰的中心。他們的所作所爲可說是驚天動地。
多個側面、深淺不同地寫這些人物,爲讀者提供這些歷史人物的細節,比如魯迅臨終前對記者說了什麼;沈鈞儒大律師有怎樣的癖好,爲什麼喪妻後不再續絃;史良爲什麼愛上比她年齡小的丈夫;王造時爲什麼慘死獄中……這些不是爲了獵奇,而是對歷史細節的補充。
王:現在的知識階層跟那段歷史相比,有哪些不同?應該如何處事?
潘:時代不同了,要求也不同。那一代知識分子受到的教育與現在不同,格局比較大。我們今天變得精緻起來,更注重技術技能的培養,講究自身利益的實現。
但是,無論時代怎樣變化,說真話、辦實事;在大義面前敢於取義,削弱甚至放棄個人利益,都是有價值的,構成了上海的城市精神內涵,這內涵一直在延續。
王:你近幾年研究的重點好像是淮河文明以及明朝那些事,爲什麼會特別關注這件事?對中國歷史而言,這有什麼意義和價值?
潘:淮河文化與上海的文化有着密切的關係,上海文化受到淮河文化的影響,春申君黃歇、上海城隍老爺秦裕伯,還有現代史上的顧正紅和當代近七百萬淮河流域的人到上海工作生活。我去淮河尋訪近20次,發表過文章、出版過書,也有一些關於那裏的文章收入《海上四書》中。這項研究目的是搞清我們怎麼來的,才能弄清楚我們要去哪裏:解決歷史的誤讀問題,比如華夏族存在時,還有其他族羣存在嗎?東夷淮夷是同一個族羣嗎?他們與華夏族、苗蠻的關係?又比如寫《淮南子》、發明豆腐的劉安真是守舊叛亂分子?淮河流域萬年以來形成的文化堆積層,與文化傳承創新的關係。
王:如果說,《海上四書》反映的是你個人心目中的上海,那麼在你的人生過程中,是否可以概括你感悟到的上海?
潘:柔和而剛毅;內斂而大氣。
王:你的小說卷,好像都把寫作的對象對準了市民大衆,基本是微觀敘事,貼身寫作,細節生動。是否可以舉例進一步講述你眼中的上海市民生活?
潘:大概與早年的興趣、偏好有關,選擇了小說這一文學樣式;又由於生活空間的關係,是一種貼身寫作。潛伏於小說深處的是人們內心深處對金錢的考量和觀念變化,比如小說《老默》《獻血記》《飢渴者》等都涉及個人與社會利益之間的博弈。經濟考量一定程度左右着上海人的行爲和處事方法,而我小說的主人公往往取義而舍利。
比金錢觀更復雜的是婚姻觀,老底子上海父母經常掛在嘴邊的是要爲子女找“好人家”結婚成家。那麼,好人家到底是什麼樣子,這個好的標準受到時代變化的挑戰。
小說描寫的人性和細節,恐怕在歷史文獻中難以尋覓,是對城市歷史的補充說明。
王:你進入社會後職業轉換多次,每一次轉換有什麼動機和思考?給當代上海年輕人可以提供哪些經驗參考?
潘:我大概換過六七種職業,唯一的願望就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文化,有的主動,有的被動,主動的時候比較多。頻繁的職業變動,產生不同的人生體驗,爲觀察生活提供不同的機會,也爲自己的成長提供了養料。但是40多年一直不變的就是碼字。
1990年代中期,我舉家遷徙距城市中心20公里外的地方居住,每天進城上班,看到地平線上這座城市,想象自己變成了一隻鳥,俯瞰原木的一個橫截面,有外環、中環、內環,似年輪,有許多細密的肌理,多年埋頭寫的就是這座城市發展過程中的肌理,一種隱性的記憶,可以對“大歷史”做出補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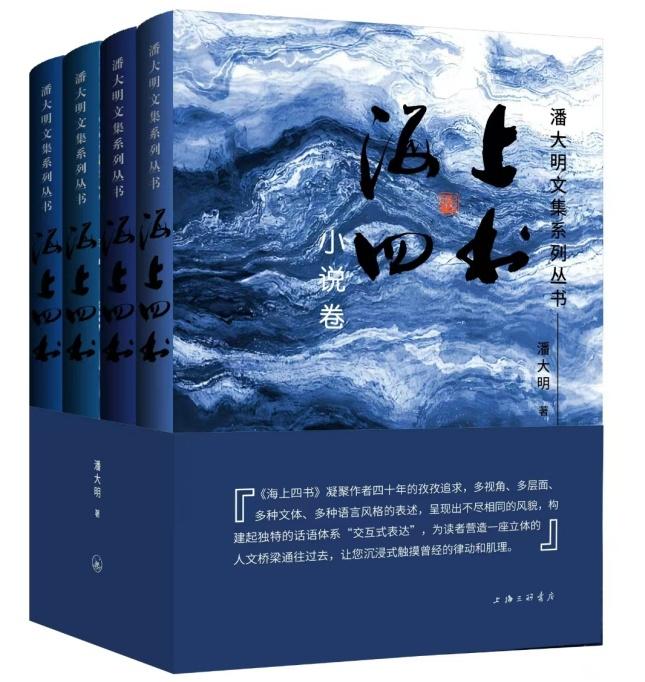
《海上四書》,潘大明 著,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