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曹禺經典中“未竟之生命”,談父女兩代人筆下“最雷雨”的女性|萬方專訪



曹禺先生的話劇作品是20世紀中國文學中當之無愧的愧寶,他以戲劇文學的方式,爲我們留下了一系列精彩絕倫的文學人物。這些文學人物也活躍在戲劇舞臺上,吸引了無數熱愛文學和戲劇藝術的人們。在文藝評論家、上海戲劇學院教授楊揚看來,曹禺筆下的女性人物一直被文學讀者和話劇觀衆視爲是最具有審美魔力的,而《雷雨》中的一號女主角繁漪是這一女性系列形象的代表,她的美讓人一眼難忘,但卻是一種令人窒息的美,是充滿了絕望的美。因此,在曹禺先生誕辰115週年之際,作家、編劇萬方推出長篇小說《繁漪女士》,以“最雷雨”的女性繁漪爲主角,延伸她在舞臺之外的命運軌跡,就顯得格外引人矚目。

這部首發於《收穫·長篇小說2025冬卷》的重磅之作,不僅是對經典的當代回應,亦是對女性情感與生命的再探索。當曹禺的女兒站在當代女性的立場,從跨越時空的視角來重新書寫繁漪的故事,她是否會像麥克白夫人、苔絲特蒙娜等戲劇史上的女性角色一樣,長久地“活”下去?又能爲新世紀熱愛文學和藝術的人們帶來怎樣的新聲與迴響?爲此,本報記者獨家採訪了萬方女士。
在人物與藝術的雙重誘惑下,角色“重生”了
記者:《繁漪女士》選擇從繁漪“求愛而不得”的內心困境出發,續寫她在《雷雨》舞臺上未能展開的生命。您能否分享最初決定爲繁漪單獨書寫一部小說的契機?在您看來,時隔近百年,爲什麼今天的讀者仍需要重新聆聽她的故事?
萬方:其實,很難說清具體的動機,更多的是一種累積多年的感受。我從小最早看戲就是《雷雨》,印象最深的是曾被第三幕的雷聲嚇哭。後來長大一些,父親帶我在後臺看戲,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受當時某種道德觀念的影響,對繁漪帶有批判的眼光,也不理解她。但隨着年齡增長,一次次觀看不同版本的《雷雨》——光是北京人藝就有三版,還有其它劇團的演出——我對繁漪的認識逐漸變化。她對我有一種“危險的魅力”,漸漸引領我走進自己內心那片狂野的地帶。我對她的感情越來越深,從憐愛到共情,越來越複雜:她如此痛苦而又美麗,我同情她,但她足夠強大並不需要的我同情,那我能給她什麼呢?是理解、是愛,是去寫她。

作爲寫作者和編劇,這種情感需要宣泄,而寫作是唯一的方式。這是一個情感逐漸積累、發酵的結果。至於爲什麼今天的讀者還需要聽她的故事,我想,繁漪所代表的那種對愛的極端渴望與絕望,是超越時代的。她的生命雖在《雷雨》中只有不到24小時,卻誘惑着我去看清她、理解她、延伸她。這是一種人物與藝術的雙重誘惑。
父女之間生命的交融
記者:《雷雨》中的人物曾被稱爲“曹禺靈魂的分身”。作爲曹禺的女兒,您在創作中是否感受到與父親跨時代的對話?您如何理解他筆下繁漪“最殘酷的愛與最不忍的恨”,並在《繁漪女士》中延續或重構這種複雜性?
萬方:在我看來,這不是對話,而更是一種父女之間生命的交融。從我出生到他1996年去世,這四十多年裏,父親給予我的不僅是肉體生命的存在,更是一直在延續的精神感染——寫《繁漪女士》的過程,正是這種精神感染、交融的持續發酵。
父親說繁漪身上有“最殘酷的愛和最不忍的恨”,這種極端的性格魅力強烈吸引着我。她對愛的極端渴求與她的絕望,以及她一步步走向毀滅的生命軌跡,對一個寫作者來有着極端的吸引力。在《雷雨》中,她只存在了不到24小時,而我渴望向前向後延伸她的生命,看清她,認清她,理解她,展現她。更關鍵的一點,隨着我越來越成熟,我就能夠越來越深入的感受到爸爸對繁漪的愛,這種愛也促使我向他、也向她靠近,這是我想去寫她的重要因素。

對愛情的追求和渴望是永恆的、不死的
記者:《雷雨》的悲劇源於時代的壓抑,而繁漪的掙扎在今天仍能引發共鳴。您認爲當代女性是否依然存在“繁漪式”的困境?通過她的生命軌跡,有能回應哪些當代女性乃至普通人的生存命題?
萬方:其實在寫繁漪之前很長時間裏,我也有困惑。寫作並不給出答案,任何一個作品都給不出答案,尤其像愛情、女性生存這樣的問題。但困境永遠存在,只是以不同方式呈現。
比如愛情,我今天也會困惑:我們今天在多大程度上還像繁漪那樣需要愛情?也許不會像她那樣至死不渝地追求,因爲我們今天有其他的愉悅,也有更多的壓力。但寫繁漪讓我明白:對愛情的追求和渴望是永恆的,是不死的。
愛情既是痛苦——如果你求而不得;也是愉悅——如果你得到。今天我們可能從很多地方得到愉悅,但愛情給予你的那種生命體驗、對思想情感的影響,仍然是其他方式很難比擬的。
繁漪是一位煢煢孑立的女性,她痛苦而又美麗。我希望通過她,讓人看到那種極端的情感狀態仍然在生命深處迴盪。
重寫與創新,其實是一回事
記者:《繁漪女士》將經典戲劇角色拓展爲長篇小說,這種再創作既是對原著的致敬,也是一種冒險。在您看來,經典文本的“未完成性”是否爲當代寫作者提供了特殊的創作空間?您如何看待文學傳承中“重寫”與“創新”的邊界?
萬方:首先有一個版權問題;我因爲這種特殊的女兒身份,也可能更順暢地想到做這樣的發揮。

經典文本的“未完成性”確實提供了創作空間。繁漪在《雷雨》裏只有片段,她之前之後的生命都是空白,這正是小說可以去延伸的地方。重寫不是重複,是帶着今天的情感去看她、寫她,是一種新的交融。
重寫和創新其實是一回事,必然要有新的東西。如果和原來一樣,就不必再寫。對我來說,創作的核心是發自真情實感。任何創作,不管是對經典角色的重寫,還是寫任何自己想寫的作品,有一點是最珍貴的——那就是用真情實感來創作。
【附錄】萬方:《繁漪女士》後記

爲什麼寫繁漪?
原由很多。首先我是《雷雨》作者的女兒,而繁漪是《雷雨》劇中的女主角,從小到大我一次次走進劇場去看她,對她自然而然有了感情,這份感情隨着年齡的增長在變化,加深。少女時期我被所謂的正經思想洗過腦,對她秉持否定的態度,但同時又有好奇。當我漸漸長成女人,自然而然被她身上危險的魅力所吸引。這引力帶着我去向內心的狂野地帶。我不知道是否人人心裏都有那樣一塊地方,反正我有。我當然懂得她是可憐的,也同情她,但又覺得她不需要我的同情。這個女人煢煢孑立,痛苦而美麗,足夠強大,我給不了她什麼,不,也許有一件事,寫她?
她是妻子,是情人,是母親。在舞臺上這個叫繁漪的角色僅僅擁有一天的生命,在那一天裏她燃燒自己,焚燬世界,無人倖免。《雷雨》是火山噴發的口,地下的岩漿在黑暗中翻湧,躁動,在繁漪的身體裏聚集壓力,最終來到爆發的臨界點,也就是大幕拉開的一刻。那麼她從哪兒來,經歷過什麼,悲劇如何發生的,哪裏是源頭?寫她就要向前,向後,尋找舞臺上二十四個小時之外她的生命軌跡。她活着,求愛而不得,她需要被理解,寫她就要滿足她。我意識到自己非常願意做這件事。
如果從誕生的一九三三年算起,今年繁漪應該是九十二歲了。戲劇舞臺上有一些女人,比如麥克白夫人、苔絲特蒙娜、娜拉,和她們比起來繁漪還很年輕,但是我相信她的壽命會很長,會繼續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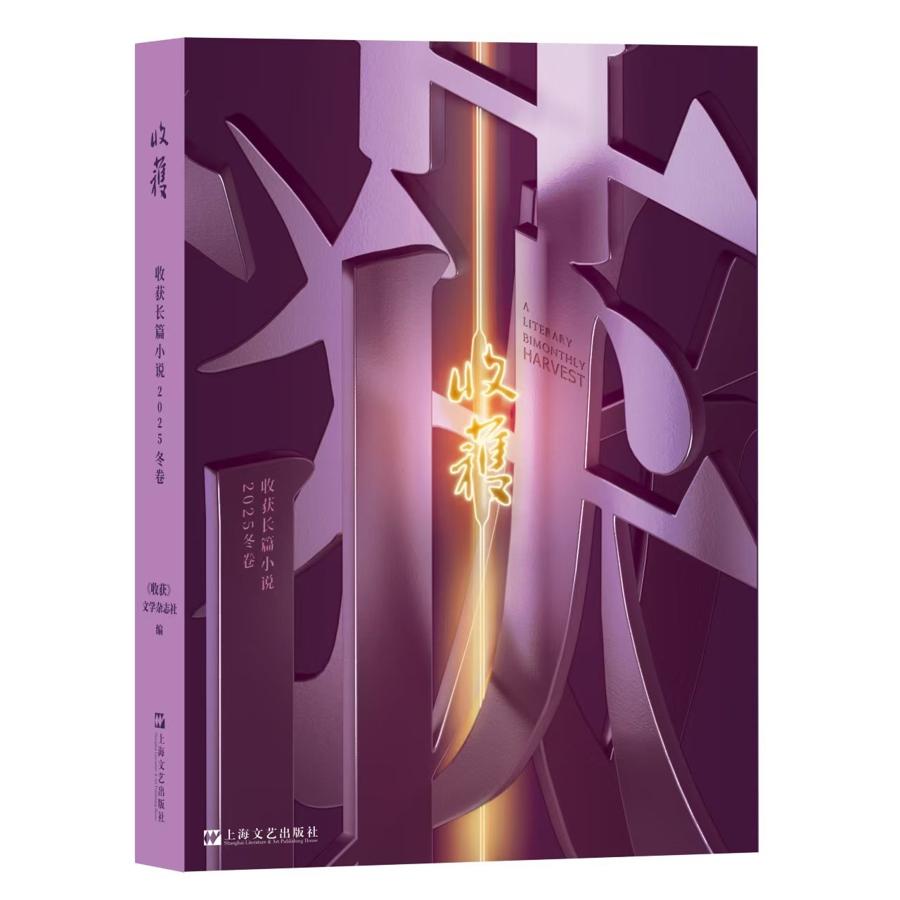
【舊文重讀】曹禺:《雷雨》序 (節選)
在《雷雨》裏的8個人物,我最早想出來的,並且也較覺真切的是周繁漪,其次是周衝。其他如四鳳,如樸園,如魯貴都曾在孕育時給我些苦痛與欣慰,但成了形後反不給我多少滿意。(我這樣說並不說前兩個性格已有成功,我願特別提出來只是因爲這兩種人抓住我的想像。)我喜歡看周繁漪這樣的女人,但我的才力是貧弱的。我知道舞臺上的她與我原來的企圖,做成一種不可相信的參差。不過一個作者總不自主地有些姑息,對於繁漪我彷彿是個很熟的朋友,我慚愧不能畫出她一幅真實的像,近來盼望着遇見一位有靈魂有技能的演員扮她,交付給她血肉。我想她應該能動我的憐憫和尊敬,我會流着淚水哀悼這可憐的女人的。我會原諒她,雖然她做了所謂“罪大惡極”的事情——拋棄了神聖的母親的天責。我算不清我親眼看見多少繁漪(當然她們不是繁漪,她們多半沒有她的勇敢)。她們都在陰溝裏討着生活,卻心偏天樣的高;熱情原是一片燒不息的火,而上帝偏偏罰她們枯乾地生長在砂上。這類的女人許多有着美麗的心靈,然爲着不正常的開展,和環境的窒息,她們變爲乖戾,成爲人所不能瞭解的。受着人的嫉惡,社會的壓制,這樣抑鬱終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氣的女人在我們這個社會里不知有多少吧。在遭遇這樣不幸的女人裏,繁漪自然是值得讚美的。她有火熾的熱情,一顆強悍的心,她敢衝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獸的鬥。雖然依舊落在火坑裏,熱情燒瘋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憐憫與尊敬麼?這總比閹雞似的男子們爲着凡庸的生活怯弱地度着一天一天的日子更值得人佩服吧。
有一個朋友告訴我:他迷上了繁漪,他說她的可愛不在她的“可愛”處,而在她的“不可愛”處。誠然,如若以尋常的尺來衡量她,她實在沒有幾分贏人的地方。不過聚許多所謂“可愛的”的女人在一起,便可以鑑別出她是最富於魅惑性的。這種魅惑不易爲人解悟,正如愛嚼薑片的才道得出辛辣的好處。所以必須有一種明白繁漪的人始能把握着她的魅惑,不然,就只覺得她陰鷙可怖。平心講,這類女人總有她的“魔”,是個“魔”便有它的尖銳性。也許繁漪吸住人的地方是她的尖銳,她是一柄犀利的刀,她愈愛的,她愈要划着深深的創痕。她滿蓄着受着抑壓的“力”,這陰鷙性的“力”怕是造成這個朋友着迷的緣故。愛這樣的女人需有厚的口胃,鐵的手腕,巖似的恆心,而周萍,一個情感和矛盾的奴隸,顯然不是的。不過有人會問爲什麼她會愛這樣一棵弱不禁風的草,這隻好問她的運命,爲什麼她會落在周樸園這樣的家庭中。(1936年1月隨書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