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現代科學的“知”與“行”


早期現代科學史研究的權威學者、康奈爾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彼得·迪爾(Peter Dear)近日推出新著《我們所知的世界:從自然哲學到現代科學》(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25),剖析了17至20世紀重大科學成就的起源,指出科學並非有待“發現”的事物,而是由人類活動、文化觀念與社會制度共同塑造的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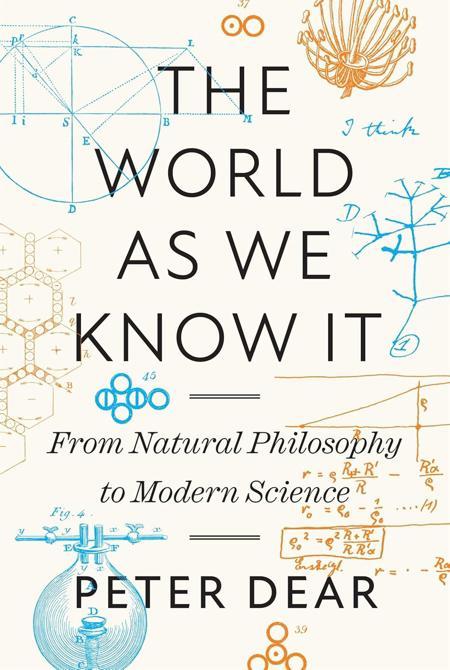
在書中,迪爾揭示了牛頓那本描述運動定律和萬有引力的著作之所以能迅速成功,實因其宗教價值:1687年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在英格蘭出版後不久,英國國教牧師便開始援引其證明“上帝的存在及其對世界的主宰”。同樣,迪爾認爲18世紀林奈建立的生物分類命名體系之所以盛行,不僅因其簡便實用,更因教會和政府都視其爲“上帝創世藍圖”的映照。就連達爾文充滿爭議的進化論能在維多利亞社會獲得接納,也未必是出於其理論價值,而是人類學家可藉此(錯誤地)證明非歐洲民族在進化階梯上遠低於他們在維多利亞治下的同胞。
迪爾繼而探討了熱力學、量子力學及天文學等學科的發展歷程。他提出科學具有雙重屬性:“自然哲學”追求理解宇宙本質,“工具性”則指能改造世界爲人類所用的應用技術與技能。“科學”的創新之處正在於二者的結合。如培根所言:“人類知識與人類力量合而爲一;不明原因則無法創造結果”,這句話常被簡化爲“知識就是力量”。羅素則有更直白的表述:科學具有雙重功能,“其一使我們認識事物,其二使我們有所作爲”。
科學史與科學社會學家旨在揭示科學事實具有社會建構的一面(其中難免存在種種混亂和偶然)。於是這些研究成果在傳播的過程中,就不意起到了削弱科學事實權威性的效果,社會大衆中出現了諸如質疑氣候變化、“疫苗猶豫”等等思潮。似乎今天更需要的,是能捍衛科學的完整性與輝煌成就的研究。因此,如何平衡地闡釋科學“世界圖景”的形成過程,是一項精妙的工作。
《高等教育紀事報》書評提到,過去二十年間,學科本身及其所處的世界已然改變,爲普通讀者撰寫一部兼具社會學與哲學抱負的科學史顯得愈發困難。可是,在人工智能與生物科技的時代,科學在認識論抱負與工具性抱負之間既相互影響又矛盾衝突的特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爲顯著。因此,需要更多新材料,以形成一部清晰而深刻的認識論史,勾畫出早期現代科學如何協調“知”與“行”,以更好地理解我們這個世界的所由來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