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使我們自由,並看到永恆的希望丨文匯讀書週報

《文匯報》第七版讀書
2025.12.5(星期五)

書人茶話

音樂使我們自由,並看到永恆的希望
胡明峯
——2023年1月11日,罹患肺炎的坂本龍一在聽到好友高橋幸宏因肺炎去世的消息後,感慨道:“幸宏,抱歉啊,我會再努力一下。”高橋曾是坂本龍一在YMO樂隊時的隊友,因爲坂本常一本正經地用樂理解釋和聲,高橋便打趣地叫他“教授”,從此成了後者廣被認可的稱號。然而不幸的是,就在同年3月28日,坂本龍一亦因癌症去世,享年71歲。
“用音樂對死亡進行冥想”
——死亡不可對抗,其實坂本龍一對此早有覺悟。早在2014年,他就被確診爲口咽癌,雖經治療得到緩解,但也讓他“開始不得不坦然面對和思考自己的生命終點——死亡”。2020年,他又被診斷出直腸癌,後轉移到肝臟。當被醫生直截了當地告知“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只剩半年的生命”時,他感到備受打擊,陷入消沉,“像是被奪走了所有的希望”。
——他不能忘記貝納爾多·貝託魯奇導演、由他配樂的電影《遮蔽的天空》結尾,小說原作者保羅·鮑爾斯現身的一段唸白:“因爲不知死何時將至,我們仍將生命視爲無窮無盡、取之不竭的源泉。然而,一生所遇之事也許就只發生那麼幾次。曾經左右過我們人生的童年回憶浮現在心頭的時刻,還能有多少次呢?目睹滿月升起的時刻又還能有多少次呢?”當時雖令他印象深刻,但此時才覺感同身受。他曾將這段原聲配上不同語言的朗誦做成一首樂曲《滿月》,收入他的專輯《異步》(2017),而在2023年出版的口述自傳中,他甚至以“我還能看到多少次滿月升起”作爲書名。

圖源:視覺中國
——雖然之前也曾經歷父親、母親及諸好友的死亡,但一直全力以赴工作且生性放達不羈的坂本,只有在面對自己的死亡事實時纔開始認真思考生命的有限。考慮到在漫漫歷史長河中人類的生命一直都很短暫,而藉助科技、醫療手段延長人類壽命,平均活到八九十歲也就是這三四十年纔有的事,他說:“自然地活着和自然地死去,是動物原本的生命方式,只有人類從這種方式中抽離了出來。”一向崇尚自然的他,在2021年的手術後發表聲明:“此後的日子,我將與癌症共生。”
——然而,反覆的病痛和治療使生活變得“更不容易”,同時讓他“學會了辨別對自己而言什麼是重要的和我必須做的事情,並開始爲了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在病情緩解的時間裏,他更加勤奮地工作,依舊滿世界不停地奔波,繼續進行音樂創作。在回應媒體的提問時,他說:“我從2009年左右就意識到我的音樂中與死亡有關的主題。鋼琴鍵盤的起落、(音色的)衰減與生命和死亡有很大關聯。這不是悲傷,我只是在用音樂對死亡進行冥想。”
——英國卡迪夫大學政治哲學和國際關係學教授戴維·布歇與露西·布歇夫婦共同撰寫的《鮑勃·迪倫和萊昂納德·科恩——死亡與登場》一書揭示,面對衰老和病痛,“順從天命、哀傷和即將來臨的苦澀而甜美的死亡”是許多音樂人的創作主題和靈感源泉。迪倫在一個飄雪的冬季被困於偏僻而嚴寒的明尼蘇達農場,由此引發了對自己必死性的不無猶豫的接受,在七年的“停更”之後,重又發表了新專輯《被遺忘的時光》(1997),自稱是“擺脫困境的迴歸之作”。肅穆而沉重的曲詞,讓聽衆以爲他正在了結世俗的事物,與造物主言和。恰在1997年5月,迪倫罹患心包炎,幾乎危及生命,難以忍受的疼痛讓他的音調變得詭異、悲傷、黑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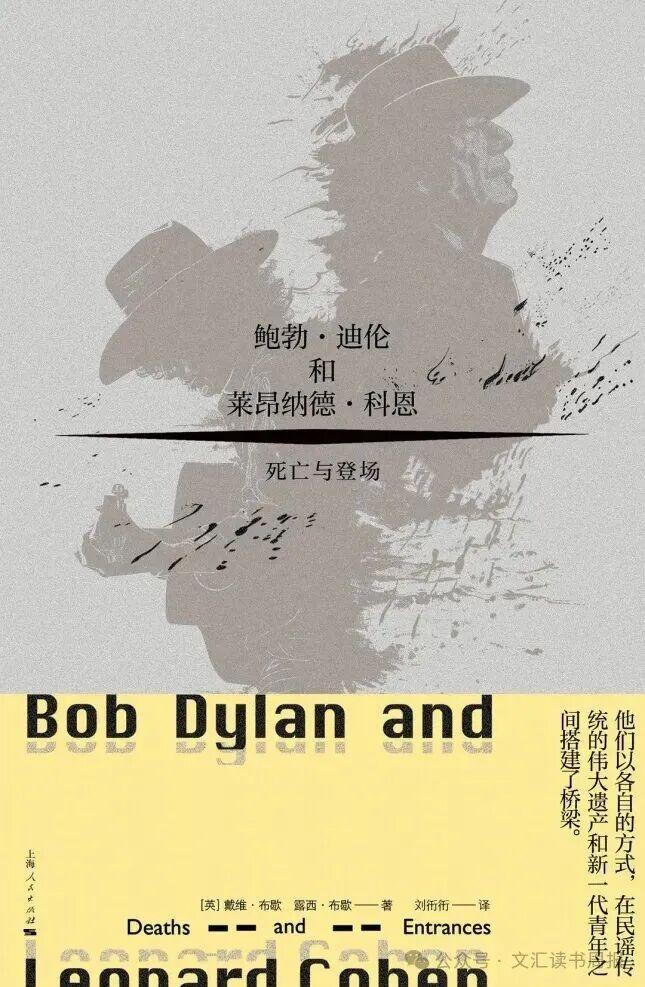
《鮑勃·迪倫和萊昂納德·科恩——死亡與登場》
[英]戴維·布歇、露西·布歇 著
劉衎衎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當被問及是否經常思考死亡時,迪倫回答說他思考的是人類的死亡:“每個人,無論多麼強壯、偉大,面對死亡時都很脆弱。我是以普遍性的方式來思考它,而不是以個人的方式。”從第一張專輯《鮑勃·迪倫》(1962)起,他就對死亡和重生充滿執念,這張專輯也被認爲是“迪倫的遺囑和見證,也是迪倫的新生”。後來他更年長,經歷過多少次生死輪轉,他在歌裏唱道:“記不得我何時出生,也忘記了我何時死去”(《假先知》),而最終“我與生死同牀共眠”(《萬物皆備於我》),均出自專輯《粗礪喧囂之路》(2020)。
追求“事物原本的聲音”
——2017年,坂本龍一與生物學家福岡伸一在NHK教育頻道進行了兩場對談,後被結集爲《音樂與生命》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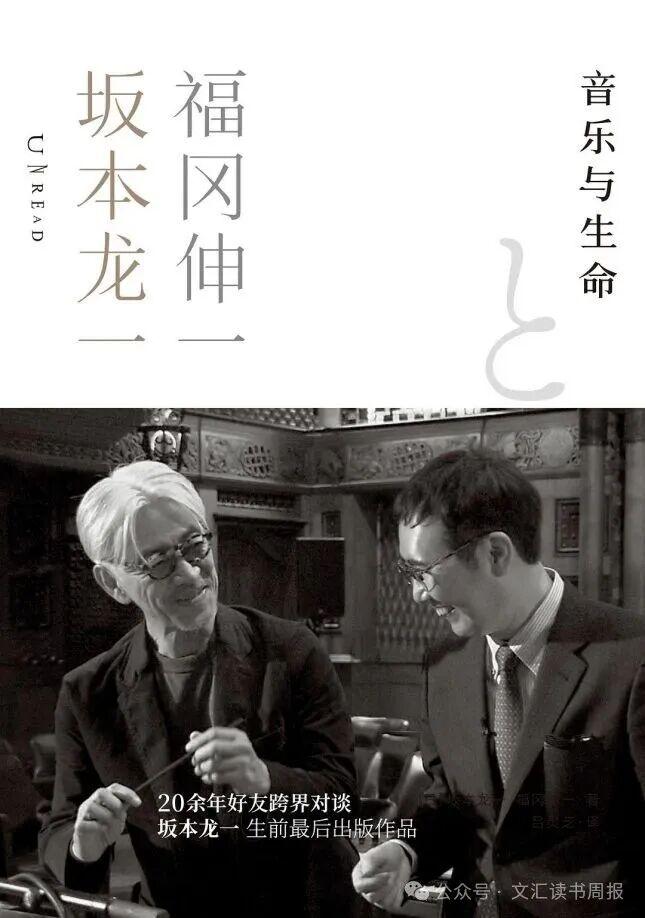
《音樂與生命》
[日]坂本龍一、福岡伸一 著
呂靈芝 譯
花山文藝出版社2025年出版
——作爲一名科學家,福岡認爲,一切的生命體都將迎來壽命終結之時,那是不斷對抗熵增定律的動態平衡最終凌駕於熵增定律之上的瞬間。那不是敗退,而是某種饋贈。一個生命體所佔據的空間、時間、資源等生態位,在其死後將會交到更年輕的生物手上,於是新的生命動態平衡又會建立。生命就是這樣延續了38億年。生命的一次性、有限性,雖然令人感到悲哀和痛苦,但卻是“最大的利他行爲”,“同時也是文化性、藝術性,甚至是學術性活動的動力來源”。每個人都希望在世界上留下自己活過的證據,因此就要有所創造。
——在固定的模式之外創造音樂,在傳統之外創造新潮,這正是坂本龍一一直在做的嘗試。並非刻意破舊立新,並非囿於進步和保守的二分法。“我只是想創作自己想聽的音樂而已”,他隨心所欲,無拘無束,活在當下,希望“每次創作都和上次不太一樣”。既然如今的世界都在追求同步,那麼他就提出“異步”,這既是對現代“時間”概念提出的質疑,也反映了其生死觀的變化。
——坂本龍一的音樂實驗性強,風格多變,“沒有標誌性特徵”——他這樣自我反思道。但他並不認爲這是缺憾,反而頗有標榜之意。在時間上有始有終、有因有果、有邏輯推演過程的線性思維方式,至少不是藝術的創作和表達方式。 “不可以操縱音符”“不要有試圖去控制鋼琴的念頭,只要手指在琴鍵上行雲流水般的移動”,比起憑藉高超的技藝操控音符,這種不操控的自由或許纔是更大的自由,也纔是音樂的本質。在2009年的口述自傳《音樂即自由》中,書名即託喻此意。在《我還能看到多少次滿月升起》中,坂本在病痛的桎梏下更強烈地感受到:“就算身體無法自由行動,在創作和傾聽音樂的瞬間,也能忘卻疼痛和悲哀。這就是Music sets me free啊。”

《我還能看到多少次滿月升起》
[日]坂本龍一 著
白 荷 譯
中信出版社2023年出版
——音樂使我自由。我創造了音樂,而音樂也創造了我——這個領悟恰與鮑勃·迪倫的座右銘不期而遇:“人生不是去尋找自己或尋找任何東西,而是去創造自己。”年輕時的坂本龍一,只顧着在東京街頭流連、玩樂,只望着“高科技”“後現代”那些新鮮玩意兒追趕,卻忽略了關於生命實存和“物”自身的發現。被他一直尊稱爲“李老師”的李禹煥,早在1970年左右就與菅木志雄等人一起以“物派”的名義在美術界嶄露頭角。他們主張拋棄人類狹隘的想象力,正視那些沉甸甸的“物”的存在。
——後來坂本龍一同樣在創作中追求“事物原本的聲音”:石頭互相敲打摩擦的聲音、山中蟬鳴的聲音、海嘯鋼琴的聲音、冰川洞穴裏鍾鈴的聲音、雕塑的聲音、水的聲音、青蛙的鳴叫、雨聲、雪落之聲……他自我反思道:“我在18歲時開始接觸李老師的作品,也許當時就可以走物派音樂之路。然而,年輕時的我因爲迷戀金錢和女性,並沒有選擇這條路……直到過了60歲,經歷了嚴重的疾病,脫離世俗慾望迴歸質樸狀態後,那座我該去攀登的山峯才顯露出身影。也可以說,我兜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了原點。”
——在坂本生前最後一個生日當天發佈的最後一張專輯《12》(2023),封面採用了李禹煥的極簡主義作品,紅綠藍灰間雜的12條不連貫的線段,體現了坂本所理解的時間刻度和復返自然的創作風格。
“更重要的是語言無法表達的那部分”
——2011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福島核泄漏。坂本龍一是一位堅定的環保志士,曾發起“More Trees”森林保育再造計劃。2009年發佈的專輯《出自噪聲》中,記錄了雪融化的聲音、海洋深底的聲音,以及在北極冰川洞穴裏敲打鐘鈴的聲音,“爲表達對大自然的敬畏之情,整張專輯最後呈現出來像是一幅大型山水畫”。但在大地震後,坂本認識到人類根本無法與自然抗衡,面對自然威力的巨大破壞,所有偉大的文明和藝術作品都黯然失色:“我陷入一種即使人類努力創作音樂和進行表達,最終也會喪失意義的無力感……在承認人類難敵自然這個前提下,我也認爲我們有去享受在自然之中加上兩三個聲音的權利吧。”

圖源:視覺中國
——宮城縣名取市一所高中的教學鋼琴毀於地震引發的海嘯,坂本聽說後買下了它。它雖然完全失調,卻發出了一種不同尋常的聲音,這些聲音被收入專輯《異步》。這架鋼琴也在坂本龍一和高谷史郎共同策劃的裝置展覽《生命—流動,不可見,不可聞……》(2010)中作爲展品,與觀衆見面。
——語言是人類思維和認知的前提,是生產和生活的必需,但坂本龍一卻幻想一個沒有語言的未來地球。他認爲,語言爲無形的事物劃定了邊界,名詞命名了事物,但也導致了割裂和僵化。他嘗試去進行不借助名詞的思考:“無論哪種藝術形式,更重要的都是語言無法表達的那部分。”用福岡的話說,那就是“大自然的歌聲”。
——坂本龍一認爲,也許給作品起名字本身就會陷入一種邏各斯的概念化困境,即便是“無題”,也還是一個標題。在最後一張專輯《12》中,他直接使用了錄製時間作爲標題,但這也仍然是命名。在《音樂與生命》序中,坂本說:“但我們依舊無法逃出它的桎梏,不是嗎?即便說‘時間不存在’,時間依舊會朝着單個方向不斷地前進。”
——在《我還能看到多少次滿月升起》最後,坂本龍一引用古希臘哲學家希波克拉底的名言作爲結束:“Ars longa,vita brevis.(藝術千秋,人生朝露。)”當紐約某處庭院裏那架孤零零的鋼琴最終迴歸自然的時候——“這與我們人類應有的老去方式存在某種聯結”,只有音樂讓我們在短暫的瞬間看到永恆的希望。——
END

來源丨文匯讀書週報
編輯丨周怡倩 吳澤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