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葦的地平線與羊羣——評跨文體散文集《亞洲腹地:111個詞》



新疆版圖遼闊,甘肅地形頎長,但在地理和文化上脣齒相依、互爲貫通、彼此莫逆。在詩人沈葦久居新疆的30年(1988—2018)間,我曾經十多次進疆,或是參加由他策劃並組織的文學活動,或是獨自及與他結伴漫遊天山南北,像他所說的那樣,以此向“黃金般的亞洲腹地”致敬。我和沈葦相識於1990年代初,從第一次見面直到今天,我們一直以“小沈”和“小葉”互稱。他是一位寬厚且懇切的詩人,才情飛揚,性情揮灑,與他的每一次相聚,幾乎都是酣暢淋漓,記憶猶新。我們很早以前就約定,這輩子哪怕是到了古稀與耄耋之年,仍然以“小沈”“小葉”相互稱呼,以紀念我們的青春歲月和詩歌生涯。

圖源:視覺中國
久居新疆大地的沈葦,姿態高迥,橫步天山南北。他寫下的關於新疆的詩作大概有上千首之多,可謂是蔚爲大觀,而這些作品業已構成了一塊文章高地,建築了一種獨特的抒唱,風格殊異,嗓音鮮明。在經歷了長久的詩歌寫作,並獲得了魯迅文學獎之後,沈葦忽然斂翅低飛,束身站在了西域大地,漫步,傾聽,細察,並展開了詰問與考證,這就是他與詩歌“同頻共振”的散文寫作。如果說詩歌是他的“羽翼”,那麼散文則是他今日的“根脈”,在他的手中,“詩歌之翅”和“散文之根”相得益彰,乃是一體化的創造與存在,他自己也認爲散文是其詩歌的拓展和延伸。迄今爲止,他先後出版了散文集《新疆詞典》《喀什噶爾》《書齋與曠野》《絲路:行走的植物》等十餘部著作,還有一部在21世紀初,凡進疆的揹包客們幾乎人手一冊的《新疆盛宴——亞洲腹地自助之旅》,這是他曾經漫遊新疆七個多月的產物。《新疆詞典》與《新疆盛宴》,加上詩集《新疆詩章》,被譽爲他的跨文體“新疆三部曲”。
如今,一部歷經20多年,並經過沈葦反覆打磨的重磅之作來了,它就是《亞洲腹地:111個詞》。其前身是由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初版、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年增訂版的《新疆詞典》,此番再次修訂增補,花落蓮出,煥然一新爲全新的精裝本,也不妨稱之爲《新疆詞典》20週年紀念版。的確,一部詞典和111個詞彙,它們形如一隻只羔羊,漫山遍野而來,而沈葦就像一位放牧者,他如數家珍,他耐心肅穆,他仔細經營着這一大家子。我們通常用“十年磨一劍”來讚揚一個人的耐心和定力,而從《新疆詞典》到《亞洲腹地:111個詞》的成長演變來看,沈葦做到了“二十年磨一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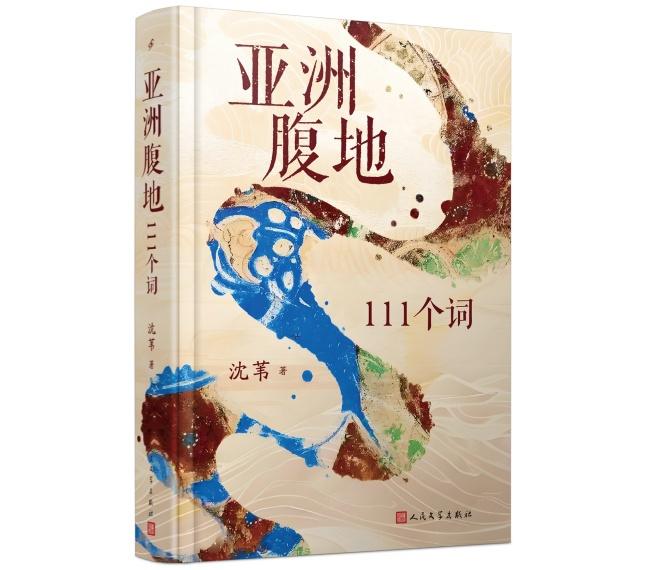
《亞洲腹地:111個詞》,沈 葦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出版
在這部著作中,沈葦用111個詞條,構築起了他所熱愛和理解的“新疆”,它豐盛,它立體,它斑斕,它多元,於字裏行間充滿了啓示性與震撼力。沈葦以詩人的激情、散文作家的博識以及學者的人文精神,着力爲被扁平化和經驗主義寫作所籠蓋的新疆“去蔽”,喚醒了悠遠、沉雄且壯闊的“絲路記憶”,以文字發掘出了亞洲腹地的“精神地理”,其主題涉及西域人文、歷史、地理、人物、風土、動植物等廣泛的領域,並將散文、隨筆、童話、散文詩、寓言、小小說、微敘事、書信、札記、田野調查報告、科考文章等等的文體熔於一爐,鍛造此書。無疑,這是向中國古代“作文”的偉大傳統致敬,同時也呼應了周濤先生於1990年代所倡導的“解放散文”,放大了“散文”這一概念——從“狹義散文”重返“廣義散文”,其形式雜糅、文體交錯、長短參差,呈現出了多重視角下的跨文體寫作特點。
“文體意識”是個好詞,在沈葦的筆下,它升級爲一種“跨文體意識”,也體現出了異常自覺的當代“散文精神”,正如有評論指出的那樣,沈葦將現代知識科學中的“超文本”概念成功引入到文學創作領域,從而有效強化了散文的表現力。我也看到過沈葦在浙江文學館的一個演講,他說,“如果說詩歌是衝刺(尤其短詩,如百米衝刺),長篇小說是馬拉松,散文則是‘文學的散步’;既然是‘散步’,就應該是自由自在、從容逍遙的,可以大步走、小步行,可以走走停停,可以變更路線、偏離方向,甚至可以迷路……”可見,他對散文的理解是十分獨到的。
這本《亞洲腹地:111個詞》,寫出了“現實新疆”與“歷史西域”的交互並置,寫出了邊疆“表面上的荒涼,骨子裏的燦爛”(沈葦語)。雪萊曾說,詩人是這個世界的“立法者”,帶有浪漫主義的宣諭色彩,而海德格爾也說過“詞語缺失處,無物存在”這句話。什麼是詩人?何爲作家?究其實,他們就是一些修辭立誠、尋找“詞”與“物”相愛相殺之關係的人。時至今天,在這個AI時代,“立法者”雖已隱匿,如白駒不可追矣,但詩人仍是這個世界不可或缺的“命名者”。沈葦對新疆大地的諸多“命名”,可謂精準、果斷、一錘定音,他稱新疆是一本“大書”和“奇書”——“以天山爲書脊打開的一冊經典,南疆、北疆是它的頁碼,沙漠、戈壁、綠洲、草原、羣山都是它的文字”。他寫崑崙:“諸神的枕頭,但是諸神缺席。衆山之父,玉英之母。這高處的眩暈、峯巔的虛空……統統遺棄了它:這東方荒涼的奧林匹斯山。”這本書中最短的詞條是“木乃伊”,它只有短短的一句話:“精通死,勝過我們理解生。”最長的詞條爲“塔里木”,乃是沈葦跟隨《中國國家地理》“中國最大沙漠和最長內陸河聯合考察隊”深入考察塔里木盆地後所撰寫的“科考報告”,洋洋灑灑,一氣萬言。

圖源:視覺中國
閱讀《亞洲腹地:111個詞》,使我想起了安比羅斯·比爾斯的《魔鬼辭典》(又名《憤世者詞典》)、米洛拉德·帕維奇的長篇小說《哈扎爾辭典》、福樓拜的遺作《庸見詞典》、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自傳《米沃什詞典》等著作。實際上,在文體探索及精神追求這個層面上,沈葦的“詞典體散文”與上述作品真是一脈相通的,也可以說,《亞洲腹地:111個詞》的寫作,是向那些傑出的“詞典體作家”的一次敬禮。
落日孤懸,大野平疇,在寂寂千年的絲路古道上,亞洲腹地的這“111個詞”,始終跟時間一樣緘默着、沉睡着、期待着。現在,它們因了一位書寫者的闖入,突然間變得面目清晰、詩意勃發、滿血復活了。命運總是雙向的,1988年,沈葦這個江南才子毅然拋別了他所熟悉的南方景緻,一葦橫渡,執念向西,坐了四天三夜的綠皮火車,隻身進入了西北腹地。此後,在天山南北美不勝收的饕餮盛宴中,沈葦紮下了根來,歷30年之光陰,他一直在潛心寫作與歌唱。他的全部文字,既得益於莽莽邊疆及異域文化的澆灌和營養,但又不失南方纔子的那種細膩和柔韌,進而使他的文本熠熠生輝,一時無兩。當然,這本《亞洲腹地:111個詞》同樣如此,它雖然是跨文體散文的樣貌,但詩歌的本心歷歷在目,也可以說,它在本質上是一冊跨界之書、回望之書及重構之書,豐盈且駁雜,猶如一座深秋的糧倉。散文,無疑也是沈葦的另一種詩歌寫作方式,但他的筆似乎更裕如、更廣闊、更加接續了大地之氣,豐沛激越,慷慨高邁,卻又不失理性和客觀。我相信,這是沈葦自信和果決的轉身,也是“書齋與曠野”的雙重書寫,更是他一次次長途奔襲、實地踏勘的結果。
在本書的封底,這位“江南與西域之子”動情地留言:“離開新疆已六年多,現在更多的是回憶和神遊了,但內心深處依然有一種真切的‘不在場的在場感’。新疆是我的人生奇遇和文學再啓蒙,30年後重返江南,它仍是我心中神聖的存在——啓示錄般的亞洲黃金腹地!”我甚至覺得,沈葦的《亞洲腹地:111個詞》是一本可以無限衍生下去的著作,因爲在邊疆遼闊的地平線上,還應當有更多的指認與見證,有太多的風土與晨昏,等着他在回答這個命題:
何以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