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翊雲再一次用講述安頓了自己



故事的講述,往往始於某種不在場,無論是關係的終結還是人的離開。在李翊雲的新作《鵝之書》中,這種不在場表現得格外具體、甚至有些決絕。
小說一開篇,主人公法比耶娜就死了,那是另一主人公阿涅絲的童年摯友,一個如野火般點燃、幾乎焚燒了她整個青春的人。一封來自法國故鄉的家書穿越大西洋,以簡短附言的形式爲阿涅絲捎來了這則死訊。沒有爆發式的眼淚,沒有戲劇性的崩潰,只有巨大的靜默。接着,身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阿涅絲拿起了筆,用筆記本上流淌的墨跡,開始盪滌那些早已被時間沖刷過的漫長記憶。
這樣的開篇冷靜得近乎殘酷,但也因此製造了一種文學獨有的張力,勾起我們的好奇,激活我們的神經。更重要的是,將我們引向一個虛構創作中至關重要的命題,那就是“講故事的權力”。正如拿起筆的阿涅絲的坦白,法比耶娜的死使她擁有了“足夠(的)自由”,去審視、解剖、甚至重塑自己與法比耶娜的關係。於是,她的講述不再是單純的回憶,而是一場權力的交接,她處理的不僅是那段包含了極致依賴、真切深情與隱祕操控的複雜過往,還有不同形式的敘事角力及其蘊含的自我求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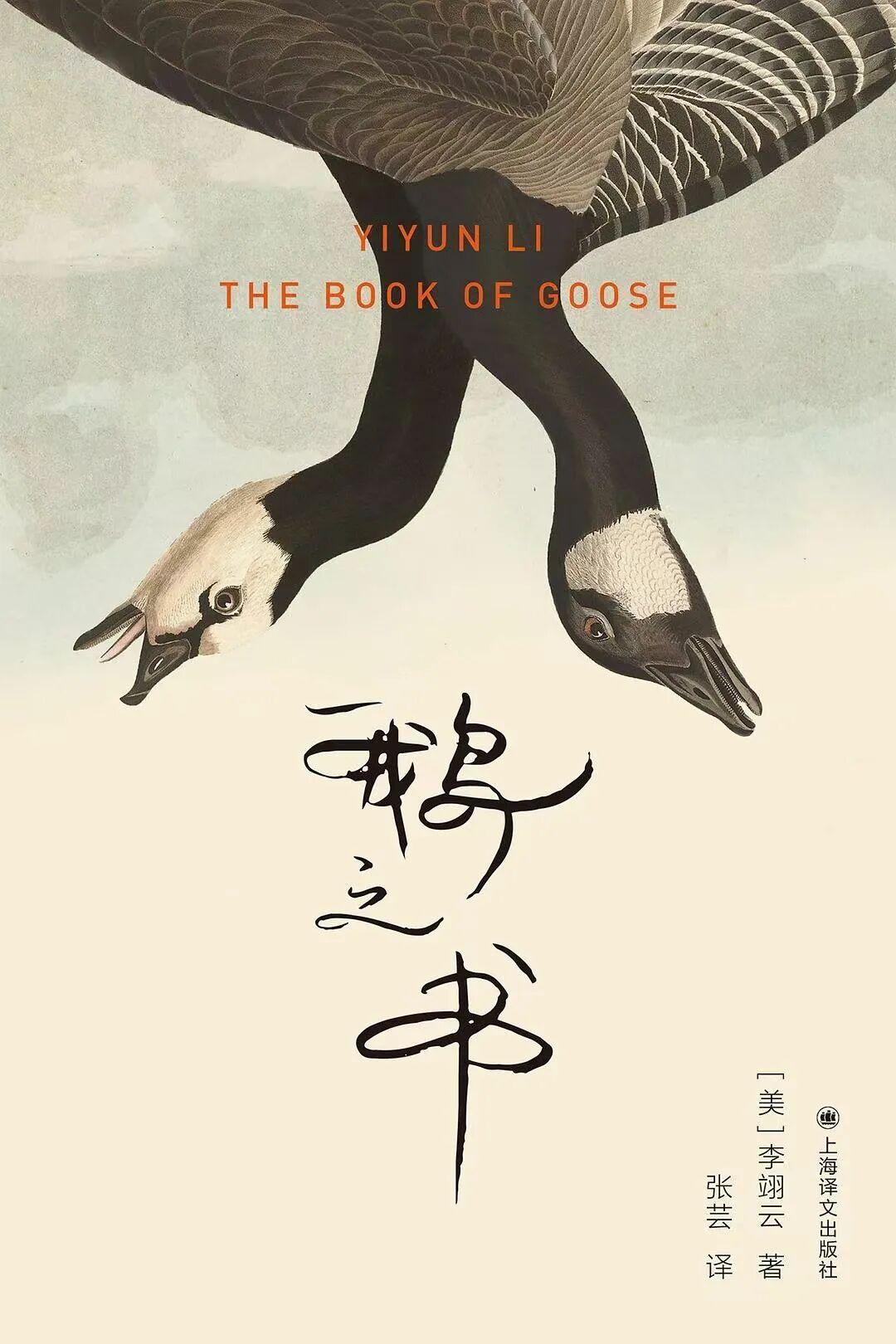
李翊雲將故事的原點設置於二戰後的法國小鎮聖雷米。在那片充滿了泥濘與草地、瘋子與醉漢的荒涼土地上,阿涅絲和法比耶娜是彼此世界的全部。在她們的關係中,有濃烈到近乎窒息的親密,也有強勢的掌控和心甘情願的臣服。
相比於阿涅絲的溫和與順從,法比耶娜聰慧而叛逆,骨子裏散發着野性的她是毋庸置疑的生命力的化身。此外,法比耶娜彷彿天生擁有一顆能夠洞穿世事的“水晶之心”,總能構想出最危險也最迷人的遊戲。其中之一便是她提議和阿涅絲共同創作一本書:法比耶娜負責天馬行空地口述,阿涅絲則負責落筆成文、並在出版時作爲唯一署名人出現在書的封面上。在這場如同小孩過家家一般的寫作遊戲中,法比耶娜的天才創造力不斷奔湧,卻也時常飄忽不定、難以捉摸;而阿涅絲的書寫,則爲這股流動的想象之泉賦予了一種具體、清晰的形式。
這既是一種成全,也是一種馴服。當那些關於“死去的孩子”的哥特式恐怖故事從法比耶娜的口中流淌而出,再經由阿涅絲的筆尖凝固在紙面上時,故事已不再屬於法比耶娜的靈光乍現,而是變成了確定的文本,可以被攜帶、被閱讀、被闡釋、甚至被曲解,這一切都將由阿涅絲全然揹負。當這本書問世後意外走紅,天真的遊戲轉化爲命運的玩笑,她們的身份也隨之迎來了不斷升級的錯位。本是提線木偶的阿涅絲被獨自推到了臺前,聚光燈下的她化身爲“農村神童”,進而成爲巴黎、倫敦文學沙龍和精英圈的座上賓。而法比耶娜這個幕後的真正創造者始終默默無聞,留在她們的故鄉繼續着餵豬趕鵝的鄉野生活,直至27歲死於難產。

然而,正是在這場愈發不可控的“扮演”中,悄然發生着權力的某種轉移。阿涅絲先是與曾經那個完全依賴法比耶娜的自我產生了距離,開始獨立思考、有了自己的祕密。在她痛苦地學習如何應付記者的過程中,她也慢慢學會了如何告訴世界它想聽見的東西。儘管這其中不乏難以啓齒的羞愧,卻帶給了阿涅絲某種意義上的“重生”。她真切感受到“講述”本身也是一種權力,一種可以塑造他人認知、定義自身形象的強大武器。
格外有趣也充滿悖論的是,是這樣一個“虛構”的人生角色讓阿涅絲開始了“真實”的自我構建,是掌握“講述”的權力讓阿涅絲從天才故事的“接生婆”變成了自我故事的“孕育者”。
直到法比耶娜的生命徹底歸於沉寂,“足夠自由”的阿涅絲決定提筆書寫她們的故事, “講故事的權力”在阿涅絲的身上再次具化,也將小說的衝突引向高潮。此時的阿涅絲業已成年,講故事的動機遠非還原真相那麼簡單,正如李翊雲在訪談中的解釋:“寫小說時,我對‘真相’沒那麼感興趣,讓我更感興趣的是‘意義’。”對阿涅絲而言,法比耶娜與其說是一個相伴長大的朋友,不如說是一個改變了她命運的存在,是一種無形的能量、一種神祕的氤氳,籠罩了她整個青春。通過確定而具體的文字,阿涅絲試圖爲這團火焰賦予一個可以被觸達、被觀看的形狀,爲她們含混、曖昧的過往賦予一種可以被言說、被理解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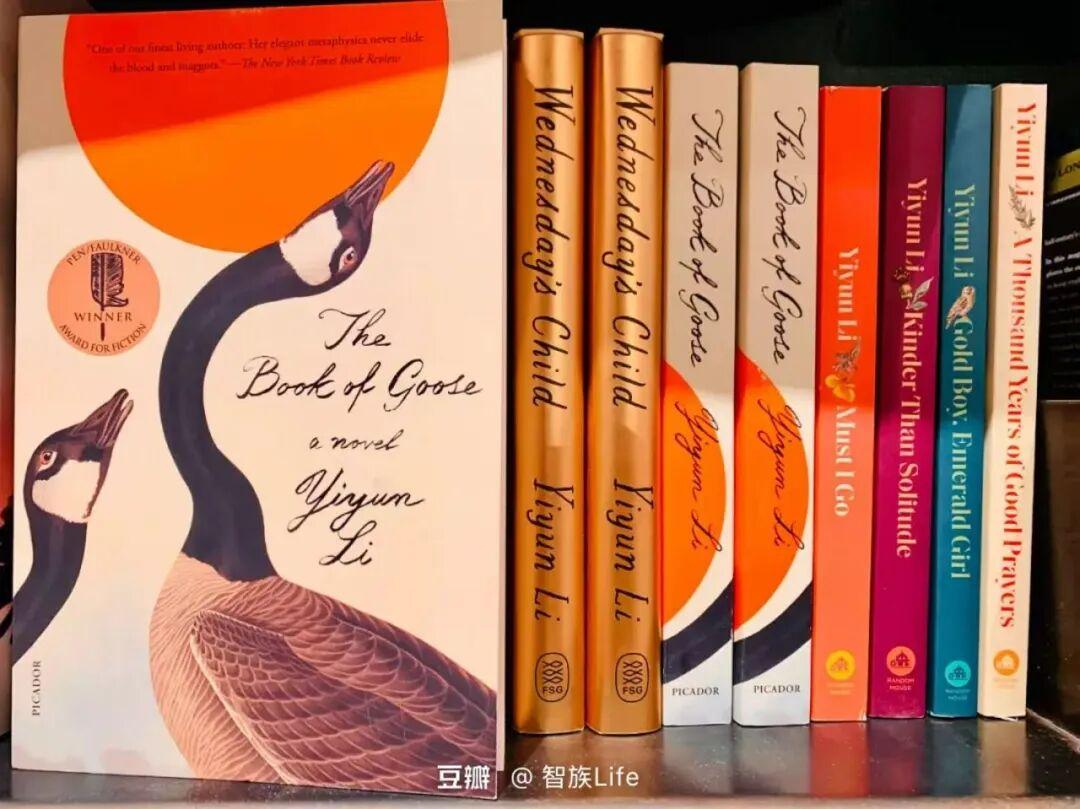
這一次,阿涅絲不再被動地承受法比耶娜帶給她的一切,而是完全掌握了主導權,徹底佔有了她們的故事,憑藉講述的權力重新呈現彼此、重新定義她們的關係。她不再向外求索式地解釋“法比耶娜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而更專注於向內探尋式地追問“法比耶娜對我來說意味着什麼?”在全然由她創造的段落、由她建立的秩序裏,她和法比耶娜之間那些洶湧熾烈卻無從說起的情感,愛和依賴、嫉妒和恐懼,終於得以一一安放。法比耶娜依舊複雜而強大,但阿涅絲通過手中的筆,將她拆解、也將她重塑,使其從一個被仰望的傳奇變爲一個能夠與之對話、甚至對其質詢的書寫對象。
這或許是寫作給予寫作者的最高形式的自由。我們永遠無法改變過去,但我們可以決定如何講述過去,從而定義它對我們產生的意義,改變它對我們曾經施加、甚至至今仍在施加的魔咒。不少評論者稱,《鵝之書》是李翊雲自傳色彩最濃的一部作品。的確,單就同爲一個寫作者而言,阿涅絲的身上或多或少投射着李翊雲的影子。作爲一個用英語寫作、甚至多年來一直拒絕授權將其作品翻譯成中文的華裔作家,李翊雲本人就處在一種“講述”的張力之中。她曾在多個場合表示,用英語寫作是她的一種“個人救贖”,讓她能夠與過去和原生文化建立一個安全的審視距離,從而在最大程度上獲得書寫的自由。這與阿涅絲的人生軌跡有着某種共通之處:同樣是離開故土,同樣是藉助異國的語言,她們才得以真正開始講述屬於自己的故事。於是,自我放逐成爲一種自我尋找,自我講述成爲一種自我確證。
當然,凡事皆有代價,自由尤其如此。寫作在解放阿涅絲的同時,某種程度上也將她囚禁。當她爲自己與法比耶娜的故事畫上最後一個句號,她不僅定格了那個神祕未知、卻鮮活立體的法比耶娜,更通過這唯一的講述掩埋了其它記憶的形態,通過這確定的講述消解了其它解釋的可能。她用一個清晰的文本,框定了一種模糊的關係,封存了一段動態的人生。對阿涅絲來說,這份清晰既是慰藉,也成爲一種無形的禁錮,因爲往後餘生,她都註定要與自己呈現於紙頁方寸間的“法比耶娜”一直相伴。

然而,同很多回憶錄式的寫作一樣,阿涅絲的書寫不僅關乎過去,同樣、甚至更加關乎現在與未來。當生命中一個重要的人永遠離場,當與之交織纏繞的生活被迫終結,留下的人要如何面對,又要如何繼續?顯然,阿涅絲訴諸的是“講述”。她用講述回望,爲了理解那份交織着美好與晦暗的友誼,爲了認清那段從依賴到獨立的成長,爲了宣告這個終於成年的自己。她的講述或許不夠完美,也不一定完全真實,更不可能真正療愈所有的創傷,但足以讓她在故事結束之後,開始一段新的、由她定義的人生。
對於生活的不可知、人的不可知,李翊雲顯得格外清醒而執拗。她曾堅定地表示:“我拒絕和解,但我接受現實。”用她的話說,那是一種“近乎決絕的全然接受,接受事情會永遠這樣下去”。面對生命中遭遇的無常,面對那些遠超她筆下故事的跌宕,李翊雲通過“講述”完成了一次次與宿命的博弈、與現實的權力交接。如果說《鵝之書》是一部關於“講述”的“講述”,那麼李翊雲的講述同阿涅絲的講述一樣,是安頓自己的一種方式。從此,對她們而言,過往或許不再是一把刀,而是一塊琥珀,滄桑卻溫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