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全世界都在教你極簡“斷舍離”,你還可以選擇“不斷不捨不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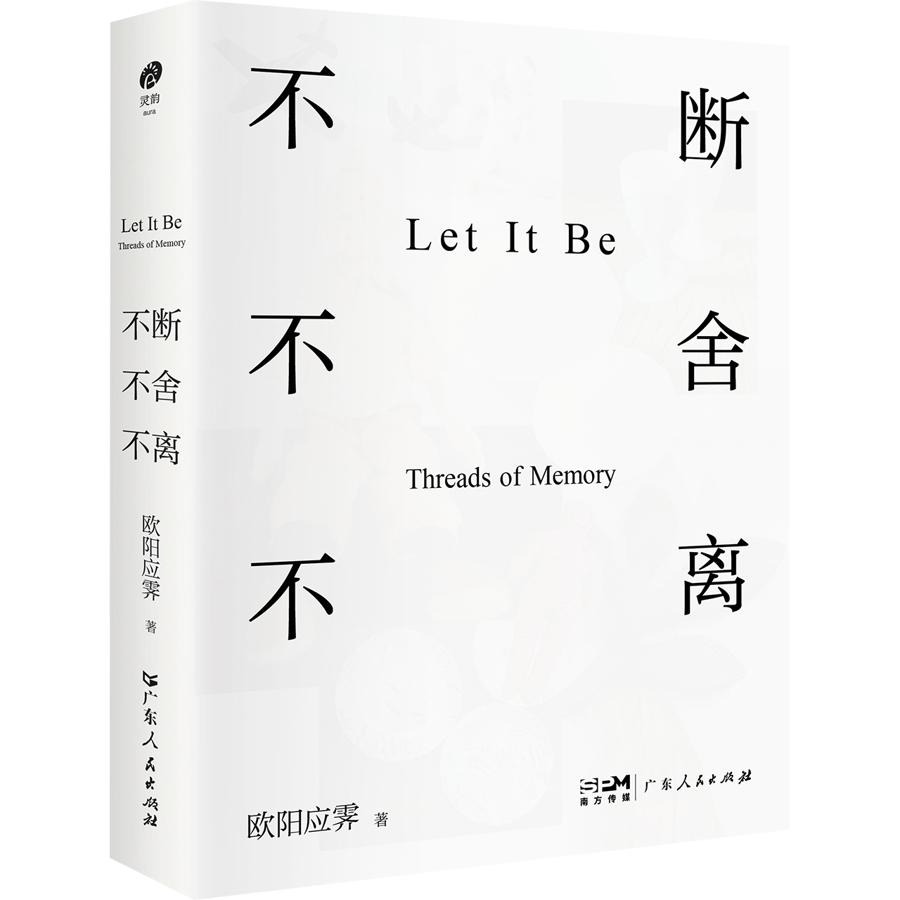
《不斷不捨不離》,歐陽應霽 著,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當“斷舍離”成爲當代人對待生活的流行法則,當身邊的舊物總被貼上“無用”的標籤,《不斷不捨不離》帶我們重新感知日常器物的生命溫度。
書中的66件器物,按生活軌跡鋪展爲“身上衣”“食爲天”“玩痛快”“必有用”,它們是衣櫥裏被反覆磨洗的白T恤,是年復一年盛着煙火氣的搪瓷碗,是角落裏只剩半截的3B鉛筆頭……
這些或許應該被列入清理名單中的物件,在作者歐陽應霽眼中,是他回溯人生時沉默卻重要的見證——“不該讓這些在我們生命中扮演過非常厲害角色的器物,從此離我們而去。”
他以敏銳、細膩的審美觀察,發覺身邊事物不同尋常的美學意義,用充滿溫度且有哲思的文字,徐徐憶起如何與它們偶然相遇、長久共處的親密溫馨時光;娓娓道出一種認真生活的態度,正是身邊平凡的、讓我們“不斷不捨不離”的“心頭好”,成就瞭如今的我們。
>>內文選讀
惜物渡人
有那麼一段日子,我們經常探訪位於灣仔皇后大道東的新品舊物雜貨店flea+cents。在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混亂其實細心安排的店堂裏,我和身邊那位經常會同一時間看中同一件玩意,然後一起等那麼三五分鐘,看誰先忍不住拿起這件新相識去買單。
這回讓兩人相視會心一笑的,是幾個竹編的圓筲箕。看上去用了幾十年的好物仍然結實完整,久經歲月洗禮的竹面都已經轉成棕褐色,間隙塵跡讓竹編的紋理結構更立體分明,其中一個竹筲箕的底面還有用毛筆書寫的“義興祥”三個繁體字。
“這個竹器是香港舊時傳統米鋪店家用來給顧客展示不同的新米品種的,隨着香港米業經營模式轉變以及米鋪式微,這些過去營生的工具瞬間被淘汰,能夠流出市面讓大衆市民睹物拾遺的已是少數。”店主是我們的朋友,也是我的大學師姐,合夥經營這家雜貨店是她與室內設計專業並行的興趣和工作,她正給好奇的我們娓娓道來竹筲箕的前世今生、來龍去脈。

我還正在盤算、想象這幾個竹筲箕如果買回家該怎樣再生再用,身邊那位已經手捧這幾個有年月分量的“長輩”去櫃檯買單了。其實這許多年來,本來打算把它們用作喝茶喫點心的托盤,但又怕經常沾水,加速破損,所以打消念頭,只用在茶几上放些有的沒的零食雜物。更多時候,是眼瞪瞪地望着這一圈又一圈,想象還原它們過去勤勞的忙碌樣子,以及街坊鄰里各家每戶早午晚有粥食粥、有飯食飯的溫飽安心。
這家雜貨店在疫情前後一再搬遷,我們跟店主師姐也疏於來往,失去聯繫,一如身邊的舊物新人聚合離散、來回更替,擁有的、失去的、記掛的、遺忘的,既要上心又得放下。最近有一天早晨,那個寫有書法店名的竹筲箕不知怎的突然出現在餐桌上,我的第一反應是:是時候它要走了嗎?它打算到哪裏去?
我們身邊不少的好物,其實比我們有限的人生經歷還要精彩豐富,也有資格、有能力比我們都活得久。在世界不同角落的雜貨店裏,我們或將會遇上,由不同經營理念的店主跟我們訴說面前不同器物的各自故事。
你我已經沒有機會踏足日本古道具界的傳奇人物坂田和實先生的“古道具坂田”和如聖殿一般的“as it is”美術館,但柳宗裏先生的故居所在的日本民藝館和河井寬次郎紀念館,還在好好地經營運作。小林和人先生位於東京的舊物店Roundabout及Outbound,佈滿他推介的新舊日常設計器物,有他獨到的“永恆如新”的見解處理。深圳的止止藝廊、香港的MIDWAY Shop、京都的Kanka Kari畫廊、神戶的Vague Kobe藝術空間、臺北的Delicate Antique古道具店,還有被行內人視爲神級的比利時古董商阿克塞爾·費爾沃特(Axel Vervoordt)及其後人在其藝廊策劃的一回比一回厲害與震撼的主題個展……
各位古道具經營者不是單懷舊的人,他們都在鍥而不捨地發掘生活應用器物的歷史,探索其當下的意義,延伸其未來的可能。在這些或侘寂幽玄或逼仄擁擠的店堂空間裏,我們與面前的器物和身邊的人一起擺渡到生活的另一個維度,繼續人與事與物的各種糾纏關係。
孤獨的3B鉛筆頭
我的父親是個畫家,生前從事藝術創作。幾十年來,走過的無數地方、經歷過的浮沉人事、用心血畫過的畫,是我作爲至親兒子也無法完全得知甚至想象的。
親和力很強的父親其實是孤獨的,正如所有的藝術家都註定是孤獨的。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包括創作之前和之後的日常生活中,都必須保持一種清醒冷靜的態度去觀察分析周圍人、事,在一種幾乎真空的孤獨狀態中一路反覆拷問自己,才能達至藝術表現的純粹、直接和完整,才能彰顯個人的獨特魅力。
我曾經無數次在香港的街頭巷尾,巧遇藏身路邊一角、蹲坐在隨身摺椅上聚精會神、忘我寫生的父親。身旁是他背了幾十年亦不斷改良進化的自制畫具揹包和畫紙夾,要麼是一個人獨坐,仔細利落地寫生繪畫,一張又一張;要麼是帶着一羣視如子侄的學生,悉心指導如何觀察、如何落筆。我常跟父親開玩笑說,我在街上碰見他的機會比回家探候他的機會還要多,也借意撒嬌說他對學生比對我們幾兄妹更和藹可親。父親“不留情面”地回應說:“我對你們幾兄妹當然更兇,要求當然更嚴格!”
還記得小時候在山野間、在海邊跟着父親寫生畫畫,用什麼紙、用什麼筆、如何觀察、如何造型構圖、如何用色着墨,父親既言傳又身教,靈活放鬆的同時嚴謹認真。我們就是在這日常自然呼吸中被督促鞭策、長大的。
父親在幾年前以91歲高齡,走完了他豐富、精彩、積極創作的一生。有一天,我在他的畫室裏整理他用過的畫筆、畫具,赫然見到一盒還未開封的12支裝的施德樓(STAEDLER)藍杆鉛筆,趕忙拆開一看,都是3B型號,筆袋裏還有一堆用剩的、長短不一的同款3B鉛筆頭。那一刻,我完全怔住了,胸臆翻滾着一股熱氣,直衝腦門,激起的眼淚在眼眶裏不斷打轉。

這熟悉不過的施德樓3B鉛筆,就是我從小被父親指導作畫時專用的那個牌子、那個型號。父親當年其實沒有刻意解釋爲什麼要用這個在1835年創立於德國紐倫堡的鉛筆品牌,爲什麼是3B而不是HB或是4B、5B。以當年父親的收入和生活標準,這個牌子的鉛筆比其他牌子的質量都要好,但也更貴,超出他的日常一般開支負擔。然而,他把這支鉛筆從他的筆盒裏拿出來,交到我的手裏,讓我自己去嘗試去實驗去比較。
這麼多年來,我當然也用過其他不同品牌和不同型號的鉛筆、炭筆,不同的畫幅大小、不同的紙張厚薄質地,需要不同的筆來完成創作表現。但我跟他一樣,習慣了平日在A4、A3紙上打所有圖樣草稿、所有文章手稿,以至於看書時畫寫在書上的所有標記和筆記,都是用這款施德樓3B鉛筆。理所當然,義無反顧,甚至連擦改鉛筆線的橡皮膠也只用同樣牌子的Mars Plastic,始終如一。
更甚的是,我竟然也不自覺地跟父親一樣,這麼多年來一直把用剩的施德樓3B鉛筆頭留在身邊,有的是短到夾在兩指間實在沒法用力而不能再用了,有的是用到大半其實還可以再走幾步的。鉛筆頭停用在某個時間節點,完成了它們在那個創作階段的使命,保持自身的一種孤獨狀態,又跟它們同樣孤獨的弟兄繼續混在一起。能夠“lonely together”,始終是一個漂亮的身段吧!
父愛如山,山中有樹,盤根錯節的參天老樹以一杆鉛筆的孤獨姿態現身日常,成全和延續了創作的衝動與慾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