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席絹封筆引熱議:AI時代何爲文學創作“護城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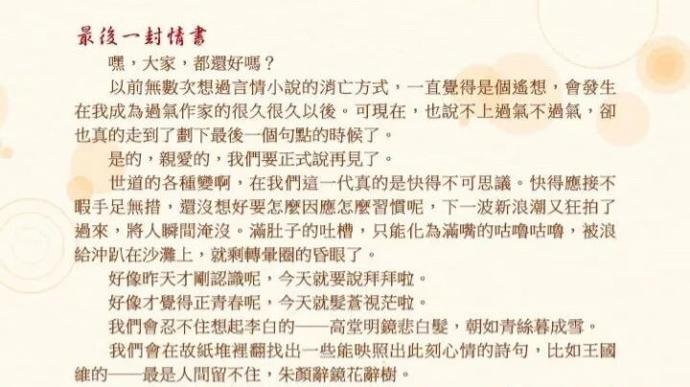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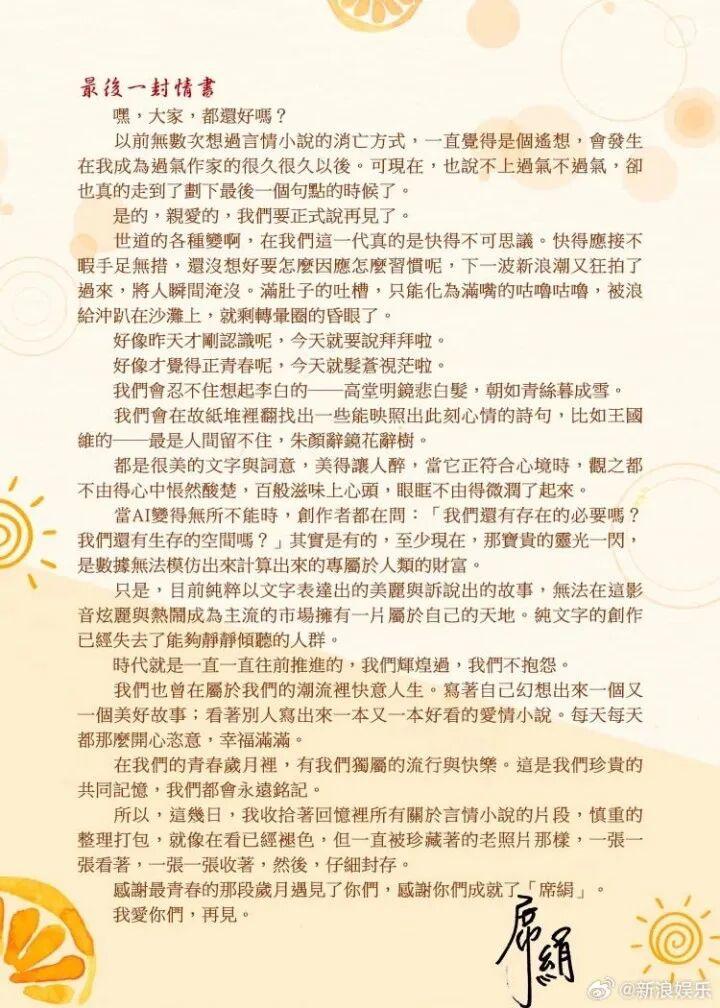
日前,言情小說家席絹通過社交平臺發佈長文《最後一封情書》,宣佈封筆,結束其長達三十餘年的創作生涯,引發業內外廣泛討論。
“當AI變得無所不能時,創作者都在問:‘我們還有存在的必要嗎?我們還有生存的空間嗎?’其實是有的,只是,目前純粹以文字表達出的美麗與訴說出的故事,無法在這影音炫麗與熱鬧成爲主流的市場擁有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她的叩問,是一位作家的退場,也像一封寫給數字時代的告別書——在AI與影音的雙重夾擊下,文字創作者是否已成爲“瀕危物種”?
席絹封筆如鏡子,照見了部分作者的失落尷尬處境:當AI快速遣詞造句,用生命經驗書寫故事還能否擁有不可替代性?讓文學創作具有辨識度的“護城河”究竟在哪?
純文字創作“失去靜靜傾聽的人羣”?
“以前無數次想過言情小說的消亡方式,一直覺得是個遙想,會發生在我成爲過氣作家的很久很久以後。可現在,也說不上過氣不過氣,卻也真的走到了畫下最後一個句點的時候了。”席絹點出她的困惑焦慮,“純文字的創作已經失去了能夠靜靜傾聽的人羣。”
這讓人想起本雅明對“講故事的人”消逝的哀嘆——當注意力成爲稀缺資源,深度閱讀似乎成了奢侈行爲。不過,席絹的告別也並非一味哀嘆控訴:“時代就是一直一直往前推進的,我們輝煌過,我們不抱怨。”
她的這番話在文學圈引起熱議,也從一個側面折射人工智能時代引發的生態格局震盪——比如,AI輕鬆日更萬字,“效率碾壓”一些作者的絞盡腦汁;算法被“投餵”百部作品後,能迅速模仿複製很多不同風格的筆觸;加上平臺根據流量分配推薦,嚴肅文學似乎難敵爽文模板……
“作家沒必要爲未來太過焦慮,AI來了就適應,來了自然會有應對的方式。至少目前我沒有看到一部作品是完全由AI創作,並俘獲人心成爲經典。”在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項靜看來,AI的確對寫作構成挑戰,但也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好處,“就是爲寫作畫了一條線,可能需要作家們先跟機器比賽,要想辦法比它更有競爭力”。
“AI已經確鑿置入了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或者說,它已經具有對於現實重新編碼的能力,但創作者應保有主體性。”評論家來穎燕認爲,文學難能可貴的就是一種永不可窮盡的人性,一種神祕的野性。“寫作法無定法。我們需要接受技術的優勢,同時保有對世界以及人性的神祕性的敬畏。”
換句話說,AI越是無所不能,人類創作的獨特性越顯珍貴。正如席絹筆下那些跨越階層的愛情故事,打動一代讀者的不是情節套路,而是她對人性褶皺的細膩勘探——那可能是算法尚未攻克的情感飛地。
別讓“金屬味”吞噬“活人感”
李敬澤、麥家、範小青等作家近期在多個論壇上都表達了對AI技術的思考。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評論家汪政,用“活人感”“活人味”形容人工智能時代“具身寫作”的重要性,他提倡文學書寫要回到人的情感與肉身。
在李敬澤看來,與其焦慮機器對寫作的威脅,更要擔心創作者自我的工具化。身體的疼痛、記憶的氣味、顫抖的擁抱——這些血肉澆築的細節,是人類敘事的基因密碼。當AI學會編織完美故事,真正稀缺的是承載價值觀的“敘事倫理”。
有聲音認爲,真正的出路或許不是對抗,而是重構創作鏈條。正如攝影術未曾終結繪畫,反而催生印象派——每次技術革命淘汰的是形態,卻解放了本質。在人機協作層面文學界作出探索,科幻作家陳楸帆與AI合寫小說,將機器的冰冷邏輯轉化爲異化隱喻等。
《陶三圓的春夏秋冬》作者麥蘇說,對於網文創作者而言,這個時代“既殘酷也公平”——殘酷在於過去單靠更新速度和套路化敘事就能成功的模式正在失效;公平在於,身處AI時代的高速迭代週期,真正有創意、有深刻情感和卓越敘事能力的故事,其價值正被技術和大潮沖刷得愈發閃亮,“未來贏家將是那些既能駕馭技術又能忠於本心的創作者”。
前不久的2025中國文學盛典·兒童文學獎之夜現場,頒獎嘉賓、科幻作家劉慈欣直言,適應AI時代,就要具備人工智能無法替代的能力,“想象力就是這種能力之一,它可以帶我們抵達遙遠的時空”。
上海網絡作家協會副會長匪迦長期深耕科技工業題材,從《中國,起飛》《北斗星辰》寫到《千帆萬安》,他認爲,人工智能浪潮中,還是需要作者的主體性,“市場是流動的,讀者口味是不斷變遷的,AI是過於絲滑圓潤的,創作者要結合本人特點和所擅長領域,順應潮流,但不隨波逐流”。
“迎合是一種保守的做法,引領纔是更有魅力的呈現。作者要有提高自我創作能力的主觀意識,構建有質感的世界,把故事寫得更加有趣精彩,敢於在寫作上嘗試冒險。”《凡人傳》作者和曉相信,如果越來越多作者推陳出新反套路輸出故事,就無懼AI能穿越更持久的內容週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