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大膽超前的感官實驗:打破禁忌,用身體觀看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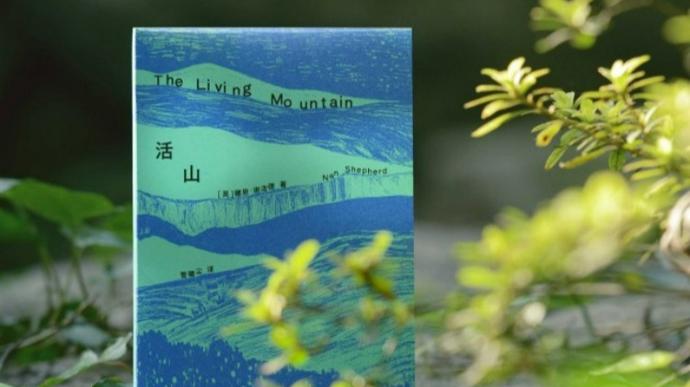


《活山》,[英]娜恩·謝潑德 著,管嘯塵 譯,新經典|文匯出版社出版
娜恩·謝潑德1893年生於蘇格蘭阿伯丁,在1928年出版首作《採石林》後,奠定了她在蘇格蘭現代文學運動的先驅地位;在那個九成女性都會結婚的年代,她終身不婚,隱世而居,不好名利,只爲自己寫作。她一生與山爲伴,當地的山區遍佈了她的腳印,爲了致敬那座漫遊一生的大山,她寫下了人生中唯一一本散文集《活山》。這是她人生的最後一次創作,卻因“不合時宜”被拒絕出版,手稿便放入抽屜長達30年,直到1977年纔出版,首印僅300冊。整整被忽略半個世紀的《活山》,在進入新世紀後卻煥發了嶄新的生命力,它被視爲與《瓦爾登湖》《遊隼》並列的自然文學經典,知名媒體《衛報》將其列爲“關於英國自然風景的最佳作品”。2016年,爲了紀念她,蘇格蘭皇家銀行將其肖像印在了英鎊上。

在山野中,謝潑德完全交付出自己的身體,將每一寸肌膚、每一種感官運用到極致,盡情接收大山給予的饋贈:花粉落在小腿上的柔滑觸感,爬蟲帶來的微微發癢,松樹的幽香穿過鼻腔內的纖毛;同時也不放過身體內部的任何一種細微反應:下巴的肌肉在霜凍中變得僵硬,冰冷的空氣衝進體內後肺部的緊張,觀看雨燕在懸崖飛舞時血液的加速。在肉體欲求被視爲禁忌的年代,她在山間漫遊,享受着身體被世界觸摸的感覺。關於山的一切,在謝潑德筆下變得如此鮮活,湧動着生命、死亡、熱情,乃至微妙的性慾。她大膽地奉獻了一份獨特又性感的自然寫作,以及超前的生命哲學——我們的身體並不止於感受,也可以思考;依靠感官去生活,去認識存在本身,重拾我們早已失去的天真。

娜恩·謝潑德
>>內文選讀:
我已經對我的山做了探索,領略過它的氣候、它的空氣與光芒、它的潺潺溪流、它的幽深山谷、它的山巔冰斗、它的花鳥走獸、它的雪以及它幅員遼闊的土地。年復一年,我對它們的瞭解日益加深。但要我說出有關大山的全部真相,就必須也算上參與其中的我本人。我一直是自己藉以理解周遭事物的工具,而如何管理自己這個工具則需要長久的學習。各項感官都有賴於訓練與規範:如何用眼去看、用耳去聽,如何訓練身體協調移動。我會教給身體許多技能,以此來探索山的性格。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項,便是沉默。
沒體驗過夜宿山中的人,不足以稱其爲真正理解大山。滑入夢鄉的過程中,大腦會趨於平靜,身體漸漸融化,只剩下知覺尚在運轉。思緒、慾望、記憶一律停止,整個人就這麼沉浸在與有形世界的深入接觸之中。
入睡前這些靜默感知的瞬間,是一天中最有價值的時刻之一。卸下所有的執着,我和天地之間再無一物阻隔。仲夏時分,午夜早已消逝,北面的光卻依然閃亮。放眼望去,天光傾瀉在穹頂下默然聳立的羣山,它們的棱角變得更加清晰,直到其中柔軟一些的線條漸漸變得虛幻,彷彿只剩下了光芒本身。在離開地球上所有其他的地方之後,光依然徘徊在這片高原的深夜深處。看着它,大腦也變得明亮而熾熱,直到光芒慢慢收斂,方纔遁入深沉寧靜的睡眠。
日間的睡眠也很不錯。日頭最盛的時候大大方方躺在山間的陽光裏,睡睡醒醒,補上一個清晨早起的回籠覺:這是生活中最愜意的奢侈享受之一。在山上入睡,醒來就能收穫美妙。從睡眠的一片空白裏回過神,在陡崖邊的隘谷裏睜開眼,由於忘了自己身處何方,不禁有些迷茫;在這個時候,你會重新找回平日裏難以品味的原始的驚奇感受。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普遍經驗(跟我平時的睡眠相比自然是不尋常的),但假如是在戶外入睡,也許是因爲比平常的睡眠更深沉,我在醒來時總是處於完全放空的狀態。雖然用不了多久又會重新意識到自己的位置,但在那個受驚的時刻,熟悉的地方會突然煥發出新的容貌,彷彿我此前從未見過一樣。
這樣的睡眠可能只會持續幾分鐘,但即便只有一分鐘,也足以解開記憶的鎖釦。我有一個天馬行空的猜想:也許山裏的某位幽靈或是化身意圖吸走我的意識,好讓我能夠在放下一切的空白狀態下見識到最真實的大山,而這種赤裸裸的恐懼感在其他條件下難以企及。我不會把感覺歸因於大山本身,但我確實沒在其他任何時刻有過如此沉入生命的體驗。這一刻,自我徹底釋放。正因可遇而不可求,這種經歷愈發顯得彌足珍貴。
凌晨四點出發,就能享受好幾個小時這樣的靜謐時光,甚至還能有機會在山頂入睡。身體隨着登山的節奏靈活運轉,在進食後的悠閒裏得到放鬆。你會感到無比寧靜,像石頭一樣,深深地沉入靜止狀態。腳下的土壤不再是大地的一部分。假如睡意在此刻降臨也毫不奇怪,它的到來就和日升日落一般自然。過了一會兒你睜開眼,不再像一塊石頭,不再與大地融爲一體;目光牽引着你感知身邊的一切,直到醒來以前你都是它的一部分。你曾身處其中,而如今這已經過去。
不過,我也曾經在本不會選擇入睡的地方睡着過。當時我們在佈雷裏厄赫山,地平線蒙上了一層薄霧,平淡的景色毫無生機、趣味寡淡。因此我們就在山頂的另一邊趴着,盡最大勇氣靠近邊緣,身體牢牢貼近地面,朝下望向布若翰冰斗。河水滿溢,瀑布的喧譁聲隨處可聞。我們看着飛流直下的瀑布一路傾瀉,砸落在岩石上。在遠低於我們的山谷谷底,鹿羣正在覓食,像是一個個緩慢移動的斑點。我們就這麼看着它們走來走去。隨後太陽露臉,灑下暖洋洋的光,眼前的動作和聲音變得令人昏昏欲睡。再然後,我猛地醒來,突然發現自己正望着一堵深色石牆,而山底遠得令人難以置信。我估計,從山頂到河牀實際上大概有兩千英尺的距離,到山腰那片鹿羣覓食的窪地大概不超過一千英尺;但在睜開眼的那“驚魂一瞥”間,所有的思考和記憶都尚未迴歸,只剩純粹的感覺,於是眼前的陡降便顯得極度突然。我深呼一口氣,說了句:“原來是布若翰!”翻過身,從山邊緩緩後退,然後站了起來。就在剛纔,我曾凝視深淵。
如果說無知無覺是白天睡倒在山間的恩賜,那麼夜空下最美妙的就是輕淺的睡眠。我特別喜歡這種淺淡的狀態,能讓我在迴歸意識表層和再次沉入睡眠之間不斷循環,只靜靜看着,不爲思慮困擾,就這樣體驗着感官的簡單與明澈。早至五月、晚至十月的第一週,我都在野外露宿過。這段時間裏,在我們古怪而錯亂的氣候條件下,通常也會有幾次光芒四射的好天氣。
某個綢緞般溫柔的十月夜,我躺在星空下,看着一輪明月直至凌晨才緩緩升起。在光滑而柔軟的破曉時分,山脈猶如流轉的湖水,連綿起伏。這一夜猶如完全拜巫術所賜,教人爲所有充滿魅力的故事讚歎不已;蘇格蘭如此努力地駁斥巫術的存在,卻從未成功。對此,我毫不訝異。任何一個凌晨四五點還待在戶外的人遇到這樣的一個清晨,都會開始迷糊得犯拼寫錯誤;在被窩裏睡到八點的人才不會想到“仙境”“迷人”或是“魅力”這種詞。找個足夠溫暖的十月嘗試夜宿野外,體驗一次晨曦與月光交織的黎明,你就會明白我說得沒錯。到時候,你也會中拼寫錯誤的迷咒。
我不喜歡魅惑,因爲它在世界這一重現實與自我這一重現實之間插入了某些東西,雖說自我現實早已被許多層虛假幻象和社會習俗掩蓋;但正是這兩種現實的融合,保護着生命免於腐壞。所以,讓我們擺脫這些迷咒吧!
我大部分的野外露宿都發生在簡單的夏日夜晚。我喜歡在這樣的夜晚不斷醒來,因爲彼時的世界實在太美,也因爲野生鳥獸會毫無戒備地靠近睡着的人。不過,如何醒來也是一門藝術。頭腦必須完全清醒,睜開雙眼時身體不能有分毫移動。某個白天我猛地驚醒,發現有一隻習慣從手中啄食的小黑鳥正在腿上走來走去。他擠出一種詭異嘶啞的輕笑聲,想要向我討食,不過聲音實在太過低沉,沒能穿透我的睡眠。還有一次,一隻蒼頭燕雀碰了碰我的胸膛。這兩次我都睡得很淺,立馬感受到了來訪者的動作,並及時醒來,看到了它們匆忙飛走的樣子。要是我沒笨到跳起來就好了!但畢竟我的睡眠被打破了呀。不,必須得是自然而然地醒來:原本閉着的眼睛現在睜開了,僅此而已,再不能有其他動作。離我十碼外的地方,一隻馬鹿正在晨曦中覓食,他無聲地移動着,整個世界完全靜止。我也靜止了。我是靜止了吧?還是說我移動過?他抬起頭,抽了抽鼻子,隨後我們四目相對。我爲什麼會蠢到讓他看見我的眼睛?他跑開了。不過沒走太遠。他一邊跑一邊看,又回頭看了看我。這一次我沒有望他。不一會兒,他低下頭,放下心來繼續覓食了。
有時我會在黎明時分從夢海浮上水面,看到一隻狍子,在他給我的意識留下清晰印象之前,我會再度陷入沉睡。雖然我不能在法庭上爲此宣誓,但這一瞥依然帶來了一陣相當真實的幻覺。那天早晨徹底清醒之後,我什麼都不記得了。直到晚些時候,這個畫面纔開始在我大腦邊緣浮現——不過,那隻狍子是不是我在做夢時夢到的呢?——由於無法確定真相到底是什麼,這個想法困擾了我很久。
在我睡覺的地方下面,木柵裏可能到處都是雀鳥。有一次,我睜開眼數了數,竟然有20只。也可能是山雀,一如既往地邁着有趣的步子跳來跳去。山雀家族裏把這一項做到極致的是其中最罕見的小鳳頭山雀,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它四處炫耀,一會兒蹦到前面,一會兒跳回後面,一會兒又跑到一邊,每個姿勢維持片刻,立馬轉移到高處或低處的樹枝上繼續:活脫脫一個精緻的模特!
有些時候,最先醒來的是耳朵。鷸發出有節奏的啼鳴。我從睡袋裏坐起身,在天空裏尋找它們俯衝而下的可愛身影。有時天還是太黑(即便是在蘇格蘭的盛夏),看不清它們的飛翔軌跡,只有飛速下降的聲音盡在耳中。
我不在睡覺的時候也聽到過牡鹿的咆哮,不過那些夜裏我都不再露宿野外了。黑暗而寒冷的夜晚降臨,咆哮聲從一片靜默的山嶺間傳來,相當駭人。隨後,另一聲咆哮會再次打破寂靜。雪融化之後,瀑布一瀉千里的聲音將整晚在睡夢中迴盪。假如連下了幾天雨,醒來就能聽到河水迸濺,發出比牡鹿更沉悶、更持久的轟鳴聲,亦自有其可怕之處。

















